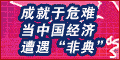| 评论:当非典来临时 谁来关爱我们的民工兄弟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8日00:40 南京现代快报 | ||||
|
非典时刻,当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城市居民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数量庞大、流动性较强的特定人群,民工们同样存在感染非典的危险。 游离于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干的又多是脏累的杂活,住的是破旧简陋的房屋,收入水平低、卫生条件差,极易感染疾病。由于流动性强,一旦感染,势必会给整个疫情的防治带来新的压力。 那么,抗非中,他们的现状究竟如何? 快报记者连续多天在他们中间深入采访——— 他们对非典的认识仅限于口罩 这天是5月12日。民工刘师傅正在锁金村一个普通的小区门口的河对面。 他四十岁的年纪,皮肤黝黑,正忙着砌砖。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安徽人,最近一个月的任务就是给这条长400米的小河两边砌上围栏。 说到非典,刘师傅停下手头的活,拍了拍手上的灰,在裤子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口罩,说:“包工头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口罩,可是什么也没讲。” 当记者再问他关于预防非典的一些基本常识时,他只是呵呵地笑。当记者问他在什么场所应该戴口罩时,他答非所问,说:“工作时,我们也不可能戴啊。” 刘师傅对非典的认识仅限于口罩。 而当天距南京首例非典疑似病例的出现已近半月,南京的非典和非典疑似病例共11例,全国非典和非典疑似病例则达7489例。 有一件事更能说明民工的防非意识。 就在这天上午,20多名民工在南京兴隆通江路上的一处隔离区旁边干活,却无一人按规定戴口罩。南京建邺区兴隆中队执法队员发现后,当即责成民工们戴口罩。不料,当民工负责人拿出一批新口罩时,大家面露难色。原来众民工都不会戴口罩。在执法队员示范下,民工们才掌握了戴口罩这门“技术”。 像这样的民工在南京无处不在。车站、码头、工地、大街小巷……然而,他们中绝少有人采取防护措施。他们对于非典多少也知道一些,但对于非典如何传播、如何防治,则几乎一无所知。面对记者“你们就不怕被传染”的发问,他们往往会拍着胸脯,自信地反问:“你看我们的样子,会得病吗?” 这一切都是在防非气氛一天浓似一天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南京市民疯狂采购口罩、消毒液、中药、体温计等防非物品,各级政府反复强调“防非形势严峻”。 但许许多多的民工依然维持着以前的原生态。对他们而言,干活——拿钱,仍是再直接不过的生活目的,也是他们与雇主间最简单的联系。他们不愿去了解更多有关非典的知识,一方面是文化程度所限和条件所限,另一方面,他们总是觉得非典似乎离自己很远很远。刘师傅的话颇有代表性,“电视很少看,不过报纸还是偶尔看看的。知道南京现在非典挺严重,不过,我们这里应该不会传染非典吧。” 他们的居住环境依旧脏乱 一排两层楼的建筑,一楼是各种经营户的门面房,二楼则居住了很多外地打工者。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十几名工人将其塞得满满的。这是记者昨天下午在后宰门西村看到的一幕。 房间的窗户上,挂着洗好的衣服,脸盆、生活用品散落了一屋。而在楼里,所有的水龙头通通设在走廊里,地上溢着脏水,走廊上晾着鞋子、衣服。记者问他们有没有对房间消过毒。 “消毒?”他们一脸茫然。 而为了便于干活,刘师傅就在小河边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栖息地———一个用帆布和木板搭起的简易工棚,面积不过十几平米,里面一张木板拼凑的床上放着一床已经分不出颜色的被子,地上湿漉漉的,洗好的衣服就挂在宿舍里面,不停地往下滴水。 记者问:“有人给这里消毒吗?”几个正在忙活的师傅抬起头,笑着说:“没有。” 还有一件事。5月1日,南京市疾控中心去福鑫大厦的地下室里消毒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100多名民工竟然拥挤在闷热的地下室,当时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感慨万分:“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得非典也要得其它的传染病了。” 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存在于这一个地方。 几名负责为一家大商场下货的民工告诉记者,他们与商场的关系很简单,为商场劳动,然后拿工钱。对于他们的吃、住,商场也从来不过问。他们通常是居无定所,哪里能住就住哪。 据了解,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紧急通知,严禁施工人员居住在通风不良的环境里,凡居住在地下室的施工人员必须立即搬出,每间房屋居住人员不得超过15人,每人床铺面积不得少于2平方米。工地必须每天对施工人员进行体温测试,并作好记录。每天对居住和饮食环境进行两次以上的消毒措施,对餐具要及时进行消毒。工地配备专职卫生监督员,负责对工地防疫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北京如此,南京呢? 他们在抗非中的流动让人心忧 在采访刘师傅时,记者问:“现在南京非典闹得这么凶,你们没回家啊?”刘师傅的回答很简单:“还没到时候呢?现在离农忙还有一个星期,到时我再回家也不迟。”不过据他说,3天前,他的两个老乡已经回家了。 昨天早上,记者在孝陵卫遇到两位来自安徽淮南的民工,他们当时正背着两蛇皮袋行李在站牌下等36路车,准备去火车站乘车回家。 闲聊时,他们告诉记者,最近一阵子非典闹得凶,加上农忙季节也要到了,他们在马群某工地干完一桩活,和包工头结完账后,就忙着回家了。“要死,也得和家人死在一起。”这是他们挂在嘴边的话。记者问他们,这样随随便便就回了家,也没有人管吗?对于记者的这个提问,他们显然觉得很诧异:“只要拿到了工钱,我们想走到哪也不会有人管,就算想管,也管不了。” 民工的来去自如,对预防非典极其不利。 中国卫生部疫情分析组的专家日前在对全国“非典”疫情的人群分布特点进行分析后指出,要防止民工流动把疫情带到其他地方。而农业部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的跟踪调查表明,去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地方就业人数已超过9400万,这9400多万名农民中,绝大部分为跨省、跨县流动。这些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加上随同外出的2000多万非劳动力,使全国流动农业人口已超过1.2亿。 南京究竟有多少民工?这个数字谁也说不清。从南京市劳动局有关“外来人员就业证”的登记情况来看,2002年一年,共登记了90298名,其中新办证人员就达到76082名。而这个数字还不能反映全市民工的总数,因为不能排除更多的民工在南京市工作,却没有办理“就业证”。 他们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的重要建设者,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然而,他们为南京的各个单位打工,但不是“单位人”;他们居住在南京,却不是“社区人”;他们存在于我们身边,又很容易被忽略。他们始终被笼罩在SARS的阴影下。 他们的心理状态更需关注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注意个人卫生的现象在民工中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疾病袭来时,他们首先想到“逃离”。因为,在这所城市,他们找不到归宿感。或者说,非典更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 一位农民工坐在工地上,神情黯然地告诉记者:“现在我们上了公交车,其他人离我们起码有2米远,有些人还要皱着鼻子,说一句‘脏死了’,脸上的表情很难看———搞得我们像真的得了非典一样,这样一来,我们反而不怕了。反正我们戴不戴口罩,他们都躲我们,我们又何必在意他们呢?”他们内心非常渴望能和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城市真正融合。“有时,就算别人向我们很友好地问路,我们都会很高兴。” 在农村,他们已经算是半个“城里人”,在城市的打工生涯让他们很难再依附于土地而生活;在城市,他们又只能算个“农村人”,缺乏保障、疏于管理,甚至在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 对于农民工现在的生存状态,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周院长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进入了这个城市,可这个城市却从来没有真正接受他们。如果说在平时的生活中受到的排斥还可以忍受,那么在这种整个社会都因为非典危机而变得脆弱的情况下,民工被排斥在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之外,就更容易导致他们心理防线的崩溃。所以他们才会说‘死也要和家里人死在一起’。因为这里不是他们的家。既然没有‘这个城市一分子’的感觉,那他们也没有必要融入整个城市的防非体系中去。其实,即使没有非典,遇到任何一种波动,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危险人群。” 服务与管理,不是控制与限制 抗非中民工们的现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保障问题。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对城市居民的保护更明显一些,而针对民工的部分很多还存在空白。简单说来,民工劳务合同不在劳动保护范围内。民工输出地政府因本乡农民赴外打工,超出管辖范围,想管管不着,民工输入地的政府不了解和掌握民工打工的情况,想管而无力管。然而,在这些民工的印象里,除了签合同的“甲方”,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对他们形成约束的部门。他们自由流动,工资是唯一的牵制。在这场危机中,政府可以通过强行限制来暂时应对,可是对于外地人口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依然是一个空白点,这个空白如果不被补上,依然不会形成外地人口和城市人口共同的社会责任感。 而且这种控制与限制的手段也值得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流动社会,民工的流动性本就是民工存在的一大特点,政府应该借SARS危机提升管理流动人口的能力,这种管理,应该是服务与管理,而不是一味的控制与限制,特别是要在民工的权益保障上有所突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从容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聪明的人应该善于从危机中学到一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典也提醒了我们。”周院长总结说。快报记者郝倩,实习记者杨青春
订短信头条新闻 让您第一时间掌握非典最新疫情!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非典型肺炎防治专题 > 正文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