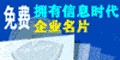| 上海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最后的回眸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24日17:10 外滩画报 | |
|
外滩记者 蒋政文田凌凌(实习)/报道彭辉 以后就住到同里去 刘达临说:“只要人在上海,我几乎每天都在这里。” “这里”是武定路1133号,上海古代性文化博物馆。 冯女士是博物馆的售票员,她告诉记者,博物馆每天上午10点开门,刘教授9:30准时到馆。 在博物馆,刘达临日常处理的事务主要包括:洽谈合作、接待媒体,除此之外经常还会有一些人前来咨询自己性生活上遇到的难题。 刘达临说,他今年71岁,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经营这个博物馆上,他和助手胡宏霞没有一个休息天,博物馆搬到同里以后,我就住到同里去,每周回家一两天。只要一间办公室,一张沙发,有一扇屏风就够了。 刘达临五十多岁开始从事性学研究,一直没有获得过家里的支持。妻子原先是上海儿科医院的医生,由于刘达临搞性学研究写文章出了名,医院同事的调侃让她觉得难为情,后来为了购置博物馆的藏品,又花钱如流水,夫妻间有了矛盾。然而,用刘达临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行我素”,他说,这是他自己的钱,他有权支配。 直到近年,刘达临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包括国际性学最高奖项“赫希菲尔德大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肯定,家庭气氛才逐渐有了缓和。刘达临说,从事性学研究,尤其在中国,注定是寂寞的。 一种无奈的选择 1995年春,为了给自己从事多年的性学理论研究一个实物支撑,刘达临在青浦徐泾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馆,当时,他并没有公开展览的计划。 1999年8月,博物馆和商家合作,从青浦迁至繁华的南京东路,从闭门纳客到公开展示。不过,在南京路上并没有达到预期要求,既没有更多的人来参观,经营上也入不敷出。 一搬进南京路,刘达临就向步行街管理办公室申请挂牌,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道博物馆的存在,可是,相关部门觉得“性”这个字眼不能出现在步行街上,直到2001年4月博物馆搬出,这一愿望都没有实现。 为了博物馆的生存,刘达临绞尽脑汁:“我们想过和大旅行社合作,可是把博物馆纳入旅游计划,就要申请‘旅游定向单位’的铜牌,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先后派了一位科长和一位处长前来视察,每次态度都很好,可是一去再也没有回音。” 博物馆如今所在的武定路,既不是闹市区,也不属于旅游区,博物馆显得孤掌难鸣,客源仍然难以解决。期间东方明珠、豫园,北京、大连的一些单位,乃至美国纽约博物馆都有过合作意向,同豫园商城的合作已经到了最后签约阶段,最终还是在审批环节上卡了壳,刘达临感到无奈和气愤,他说,这次我是赌气离开上海的,权当是我的一种姿态。 她是勇敢的女性 记者看见博物馆里有七八名游客正在参观,冯女士说,最近几天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明显增多,以前每天平均只有十来人,现在基本可以保持50人左右,双休日可以有100人以上。 博物馆总经理胡宏霞正在给几位来自台湾的客人进行讲解,刘达临说她是个“为了理想,为了事业作出重大牺牲的勇敢的女性。” 胡宏霞自称是“刘教授的助手”,作为一名女性,在这个位置上无疑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胡宏霞和刘达临的妻子以前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同事,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精通电脑同时又在一家外企兼职,管理着一家网站,有良好的收入。 可是,她毅然放弃了原有的一切,加入到创建博物馆的工作中来,“在同事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都说她“疯了”,甚至还有一些更难听的风言风语。 胡宏霞就从一名讲解员做起,“起初非常不适应,担心自己的一个不合时宜的笑容会造成误导,现在我已经能很自然地谈及这些话题了。” 这样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然而,当博物馆不得不离开南京路的时候,胡宏霞还是觉得难以承受。 那一天,最后一批来博物馆参观的客人都是刘达临在燕京大学时的老同学,参观就要结束了,刘达临说“我们一起向博物馆最后一批客人致谢。”他和胡宏霞站在大家面前,深深地一鞠躬。 “那一瞬间,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各种各样的压力扑面而来,我觉得整个人几乎崩溃了。”说到这里,胡宏霞流下了眼泪。 3400余件藏品来之不易 除了在博物馆,剩下的时间就是参加各种研讨会,去各地考察。 每次去国外考察,有三个地方刘达临是一定要去的:博物馆、古玩店和红灯区。在他看来,国外的性博物馆商业气味太浓,比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性博物馆利用最先进的声光特效制造了下体隐约可见的玛丽莲·梦露,参观者还会遭到露阴癖“男子”的突然袭击。 刘达临始终强调他一手创办的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的文化品位,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性学专家办的性文化博物馆”。 博物馆共有3400多件藏品,其中有20多件是五六千年前的文物,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搜罗这么多文物,无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钱始终是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博物馆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渠道:刘达临的稿费和版税、部分展品巡展的收入、胡宏霞的钢琴修配厂的收入。尽管这样,钱还是远远不够。 胡宏霞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刘教授在北京古玩市场看中了两件很珍贵的文物,要一万多元,我们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好说歹说,交了几百元定金,嘱咐卖主不要卖出去。后来我又和刘教授去了北京三次,仍然买不起,每次都要去看看文物还在不在,看见刘教授近乎痴迷地摆弄文物,我都会偷偷地掉眼泪。后来刘教授有一笔稿费刚发下来,他当晚就坐了火车去北京把文物买了回来。” 刘达临的另一个诀窍就是和古玩商交朋友。邓伟东就是同刘达临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古玩商中的一个,和刘达临相识已近十年,他前前后后一共向博物馆提供了1000多件藏品,在他的眼中,“刘教授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邓伟东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从一个宁波人手中买来一件文物,由于不懂宁波话,把文物交到刘教授手里的时候,却讲不清文物的来历和用途,刘教授硬是拉着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在市场里把那个宁波人找出来,问了个明白。”邓伟东每次购买文物的时候都会多着意留心,一旦漏掉了什么,就觉得是对不起刘教授了。 博物馆众多藏品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社会各界的捐赠。 石家庄有一位高古(汉代以前)文物收藏家徐老先生,有一次专程找到刘达临,要求捐赠,刘达临一共去了三趟石家庄,拿回来30多件文物,其中有四五件是国宝级的文物。刘达临告诉记者:“我想付一些钱,可是徐老先生一分钱都不要,还说‘你为社会做贡献,我就为你做贡献’。” 性在中国就像一扇半开的门 邓伟东有一次带着他的母亲去参观了博物馆,“我的母亲看了以后很惊讶,感叹上海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回去以后还组织了许多老乡同学来参观。” 许多前来博物馆参观的客人都被那些展品深深震撼,在门口的留言本上留下了各自最真实的感受。 从青浦到南京东路,从南京东路到武定路,从武定路再到明年4月份迁往同里,刘达临和他一手创办的性博物馆一直举步维艰,用一句上海话形容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性学研究起,刘达临就深感阻力重重,“这种阻力来自千百年来对性的偏见——性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刘达临说,中国性文明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好,可是,就像一扇门,打开了一半,另外一半怎么也打不开。 社会学家李银河对记者说:“目前在中国进行性学研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立项、申请资助都比较困难,政府也不会过多参与进来。经济不发展,温饱不解决,谈性是不可能的,这是进行性学研究的基石。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会有很大帮助,类似的博物馆即使在国外也很少见,这次搬迁,某种程度上讲是遇到了一个更好的发展契机。” 声明:《外滩画报》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