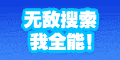| 中国人在汉城:在韩中国劳工现状调查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30日13:01 新华网 | |
|
46岁的金明兰走出那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时,一轮皓月已悬在夜空,这是她离开中国家乡后看到的第八个中秋满月。除了更牵挂在国内的一双女儿,对于每天洗碗12个小时、每月工作30天的她而言,这个节日的最实在意义仅在于用一整天的休息,来缓解已明显肿胀的双臂和双腿的酸痛。 金明兰出门时,屋内的电风扇还在摆头,地中央的矮脚桌上摆着中秋节的晚餐:辣白 包括一间4平方米厨房在内的这套小屋位于汉城市永登浦区的一个中国人聚居区,在平民区中最常见的“多世代住宅”的底层,租下它的花费是每月20万韩元(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0元)。房间内没有卫生间,如果“方便”,要先穿过厨房,登上30厘米高的台阶上到地面,然后还要再跨上另一个30厘米高的泥台。小屋窗外半米处是一堵厚墙,大部分时间里,阳光不会照进来。尽管平常的时候,金明兰住在打工的餐馆中,丈夫住在建筑工地,但有了这间小屋,她和丈夫就算在韩国有了家。 金明兰和丈夫高明持中国护照,签证页的时间显示,他们本应在7年前和3年前归国,那是他们离境的最后期限。过了那个时间,两人的身份都被划入“非法滞留者”,在韩国的劳工部门备案中,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称谓,是“非法劳工”。 据说,在韩国,处境和他们相同的中国人约有20万人。 这个与恐怖记忆相关的中秋节是第14号台风“鸣蝉”登陆韩国南部地区前的最后一个朗日,上午,几万名盛装的汉城市民来到景福宫祭祖。同样的9月11日,对于“非法滞留”在韩国的中国人而言,只是意味着又过了一年。接下来的生活会怎样,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想的,中国人的圈子中,几乎每天都传递着“有人被遣返”的消息,同样,每天也都有新人来到。 非法滞留样本—— 如果不是3年前为非法入境组织做担保,莫名承担了30万元的债务,高明可能依然还在中国北方某市当着他的副局长。如果不是代丈夫偿还债务花掉了5年非法打工的全部积蓄,金明兰可能已经回到国内“享福”。 但现在,他们都是汉城的非法劳工,只要不被遣返,他们会继续留在这里,尽管金明兰已经8年没有见过一双女儿了 金明兰摸出身上的电话卡,打通了在国内读大学四年级的大女儿的电话,每张1万韩元的这种国际电话卡她有很多,每张能用200分钟。小屋的墙上挂着的女儿的照片,已经换过几次,但金明兰仍拿不准女儿的样子,“对母亲而言,女儿的身高和眼睛大小永远不是最重要的信息。”金明兰说。事实上,关于女儿,她也说不出太多,他们见的最后一面远在8年前。 金明兰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总能想到她的一位同乡评价她时用的“刚强”一词。 1995年秋天,金明兰和姐姐金美兰持期限3个月的探亲签证,取道上海虹桥机场来到汉城,几天后,姐姐去了釜山找工作,金明兰则在汉城的驻韩美军基地找到了一份刷盘子的活,每月的收入折合人民币8000元。 “那之前我在财政局做会计,每月的收入不多,拿到第一笔8000元工钱时,我兴奋了好一阵。”度过了最开始的新鲜和惊喜,金明兰的生活很快踏上了忙时劳苦、闲时思乡的简单重复。“一辈子的苦都在几年里受尽了。”那时,她白天刷盘子,晚上就住在餐馆里,每天12个小时的体力劳动,使她常常连吃饭的力气也没了。 几年里,金明兰换过几次工作,在餐馆中刷盘子,为韩国家庭做保姆,或者在类似家政中心的机构等“钟点工”的活,收入最高时每年有人民币10万元。但无论在哪儿,她都战战兢兢,“如果暴露了非法打工的身份,我就会被遣送回国。”所以,即使每个月有一天的休息,她也很少去逛街。和被遣送相比,同样令她担心的还有拖欠工钱,“如果我拿不到工钱,我没有任何办法,要告发老板首先就会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我身边不少朋友就是因此被老板要挟。”金明兰的担心并非多余,来自汉城某民间组织的一项不完全统计:韩国中小企业拖欠中国劳工的薪水、押金、借款的金额总计数百亿韩元,而拖欠薪水的主要行业就集中在餐馆业和建筑业。 生活的艰辛,金明兰不得不接受,这是她做出的选择。但有些困顿的降临是由不得她做主的,诸如疾病。韩国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对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她而言是个惊人的数字。尽管生病时从不去医院,金明兰也有自己的“法宝”:一是“挺着”;二是自己诊治,吃国内寄来的药。这也是一些在韩中国劳工生病后的通行方式。 日子在重复中走到了第五年,金明兰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经历在不经意中来到。那一年,她不止一次想到过死。一切改变来自丈夫高明。 在金明兰赴韩时,已是某地环保局最年轻的副局长的高明留在国内照顾他们的女儿。2000年春天,他应一个朋友的请求为其“代办赴韩签证”的“项目”做经济担保。这个项目的全部内容是:每位想赴韩国打工的中国人交纳人民币8万元,“组织” 负责提供包括邀请函在内的所有的文件,并将他们带入韩国境内。在高明“作保”后,共30人迅速交齐了总计30万元的订金,其中不少人是他的邻居和朋友。未等到赴韩的日子,朋友踪迹全无,受骗的邻居找到高明索要订金,作为保人,这是高明的义务。 得知每月收入1400元的丈夫担下了巨额债务,金明兰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死,尽管她有30万元存款,但那是她在韩国5年的全部积蓄,代价是一个女人的青春。她想到了远离家乡、远离父母、远离丈夫和女儿的生活的每一道艰难的门槛,号啕大哭后,她很想找姐姐说说话,但此时,金美兰已经离开韩国。 作为妻子,最终她选择了为丈夫的“蠢事”还债。 经历这次变局,高明彻底变了。其时47岁的他办理了提前退休,当有不知情的朋友询问他“莫名”退休的原因时,很要脸面的高明唯一的借口是:退休可以涨工资。几个月后,他用家里最后的存款办理了来韩国的手续,出国前,他发了狠誓,“要打工到60岁,还妻子的债。” 2000年的秋天,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正在元气的恢复中,工作不太好找。高明先通过老乡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做木匠的活,这是房子在打好支架后的一个工序。没怎么干过体力活的高明,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因为没有经验,在公认为最赚钱的行业他也只能拿到5万韩元的日薪。整整半年,他每天早7点上工,晚6点收工,每月在工地上29天,最少的一个月也有25天。为了多赚钱,他频繁更换干活的工地,他拿到的日薪最多的一次是13万韩元。 高明说,他现在跟的工头对他不错,最累的活都不会找他做。 2001年,夫妇在大林洞租下了一间小屋,算在韩国有了自己的家,但高明还是常住工地,遇到下雨天停工才会回到这里。令金明兰牵挂的,是高明在工地上的安全。作为韩国最危险的行业之一,建筑工地上时常会发生一些意外,高明就亲眼看到过工友受伤,甚至残疾。2002年2月,意外也落在高明身上,在仁川的一个工地上他不慎被石料砸到了手,手骨骨折不仅让他整整3个月没法上工,还花掉了400多万韩元的医疗费。高明说,“那时我每天都是在小屋过的,没有阳光,心里憋得很。” 和身体上的伤害相比,高明也为自己的身份担心,他曾目睹过熟悉的中国工友被韩国警察带走,其中有人再也没回来过,他知道,他们都被遣送回国了。到韩国3年了,高明戒掉了打麻将,这是他在国内每天必修的“功课”,只是酒喝得更勤,烟也吸得更凶了。 “吃苦遭罪我们都能忍受,最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两个女儿。”支撑金明兰夫妇的最大希望就是“女儿可以上最好的学校”。目前,他们的大女儿正在国内某大学读四年级,小女儿也进了大学,夫妇俩的计划是明年送大女儿出国留学,这笔费用的预算是2000万韩元。 和所有在韩国的非法劳工的亲人一样,他们的女儿对父母在韩国的生活知之甚少。 进入韩国的非法路径—— 合法签证,违法落地滞留,是一种现状,但事实上,在这些签证申请过程中,已有多个环节被证明非法。从“签证交易”到“伪造户籍”,再从“假结婚”到“克隆文件”,许多采用此种方式进入韩国的人可能都背负着一笔沉重的债务。 有一种情形例外,需要付费却不需要造假,那就是偷渡 9月12日,农历八月十六,一场有数万在韩劳工参加的“中国同胞中秋聚会”在汉城汝夷岛举行,尽管大雨如注,韩国KBS电视台还是对此次文艺演出进行了直播。 第二天是韩国中秋长假的最后一天,韩国法务部向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赵舜衡递交了一份国监资料,这份资料认为:截至6月,停留期已满仍未离境的非法滞留者达301747人。据从事维护中国劳工权益的某韩国民间组织估算,在韩非法滞留者的数量不小。如果不把偷渡者计算在内,中国非法滞留者持有短期综合签证(C-3)、产业研修签证(D-3)和短期商务签证(C-2)三种签证入境的约占七成。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获得合法签证时都支付了数万元的高额费用,收取费用的,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 9月14日下午,在汉城九老区加里峰洞打工的陈翰昌和陈其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来这里打工的每个人几乎都背负着债务。”他们分别来自河北和黑龙江。 陈翰昌2002年申请签证的文件大部分都是伪造的,包括韩方邀请函、担保书、公证书,甚至国内在职证明与户籍证明,提供一系列文件的“签证代理人”是在北京某大厦附近找到的。最简单的伪造程序是:从韩国有关书刊中获知当地韩国公司的税务资料,再由韩国籍伪造者伪造邀请函等各种文件。伪造文件的费用是5000元,伪造公证印章200元。全部文件,陈翰昌共支付了6万元。 陈其严说,签证代理人去申请签证时是把伪造文件和正常文件放在一起的。他在顺利拿到签证后,还花了一段时间进行“整容”,“那几天都在洗桑拿浴,为的是让皮肤更好些,出发的那天还特意做了一个韩国式发型。”他这样做是为了在韩国机场降低被遣送的可能。 更严重的造假是“洗户口”,这种非法获得韩国国籍的动向已引起中韩两国警方的密切关注。在此路径中,先由韩方人士找到无主户籍(即户籍存在人不在),然后找到出价合适的中国人,伪造相关证件,“一劳永逸”地解决非法身份问题。不久前,韩国警方破获的一起伪造户籍的案件中,韩国人利用庆尚北道青岛郡无主户籍上登记的名头,为一位中国人伪造了身份信息一致的护照与身份证,并顺利获得了签证,此项交易的好处费为500万韩元。 曾担任韩国一家媒体副社长的金大全先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因为签证管理的严格,通过假结婚方式进入韩国的女性越来越多。”对于她们而言,除了要支付一笔数目不菲的费用,还可能面临着被制裁的命运。就在9月2日,汉城警方破获了一起伪装结婚中介人的案件。汉城警方的说法是,3名女子涉嫌通过伪装结婚非法入境。事实上,远在两年前,涉案的3名韩国籍男子便以“数百万韩元酬金和免费中国旅游”为诱惑,向出租车司机发出协助伪装结婚的“动议”,截至案发,三人已获利1.5亿韩元。 因为“假结婚”手续的便利,一些韩国人参与的组织已经将目光盯上了单身老人和残疾人。他们向汉城、水原和马山等地的露宿者、残疾人和单身老人支付300万——600万韩元好处费,让他们与国外女性结婚,并在韩国户籍上登记以协助她们进入韩国,通过此渠道进入韩国的女性每人要交纳1000万——2000万韩元的费用。韩国汉阳大学金贞花博士告诉记者,“通过这种办法到韩国的他国女性,在2年后可正式取得韩国国籍,与伪装结婚的韩国丈夫离婚后与实际丈夫‘复婚’便可以获得‘合法身份’。” 但有时,假结婚所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汉城家庭法院作出的一次判决理应引起注意:55岁的韩国人金中地通过婚姻中介公司,结识了53岁的中国女子林肖眠,两人交往一周后便在中国进行了婚姻登记。但当林肖眠希望在韩国办理婚姻登记时遭拒,金中地还以“手续复杂”为由拒绝提供邀请,不久更要求退婚。自认受辱的林肖眠在自费赴韩后发现,在与自己登记结婚的一年后,金中地又与另一名中国女子登记结婚。据此,林肖眠向韩国法院提出了损害赔偿诉讼,最后林肖眠获得2000万韩元赔偿。 在韩国的中国非法滞留者究竟有多少?这是个很难确切统计的数据,因为在韩国法务部定期公布的在韩外国人统计中,偷渡客是没法计算在内的。 相对于造假而言,偷渡的代价更大,除了200万——1000万不等的费用外,有时要付出的是性命。知情者说,偷渡的出发地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天然选择”的大连和青岛如今受到了福建等东南沿海的严重“冲击”。 通过非正常路径来到韩国的中国人,面临的选择常是悖论:一旦暴露身份不仅无法进入韩国,还很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刑事后果,但每一位想着去韩国淘金的人都希望有“好运气”,实践中,这样的“好运气”并不是人人都有。2002年,河北某市退休教师张安华,支付给自称能办理赴韩手续的中间人4万元人民币,中间人随后蒸发,张安华其时每月的收入不足800元。 近几个月,通过旅游签证赴韩并非法滞留的事件已有所减少,不仅仅是因为非典时期韩方停止接受了旅行的组团,更是因为一个时期随团旅行落地“蒸发”的中国人过多,韩方加强了管理。9月,韩方更是对中方具备组团资格的旅行社接连发出通告,如果来自国内的旅游团再出现“蒸发”事件,将直接降低旅行社的信用度,并影响其代办签证的结果。 春秋国旅一位接待员在回绝记者“韩国自助游”的申请时说,“不可能,组团的还要跑呢,更别说自助旅游了。”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韩方已经处理多名曾驻北京大使馆及沈阳领事馆的领事,他们均涉嫌在发放签证的过程中从偷渡中介人处受贿,其中一人涉嫌在未确认签证代理人提交的虚假邀请函的情况下,前后共89次给261名中国人发放签证,韩国检察机关调查发现,此人设在香港的秘密账户中有60万美元的存款。韩国媒体对此反应激烈,一家主要媒体更是以“领事馆成为下发非法签证的渠道”为题报道,而韩国朋友在谈及此事件时说,“赴韩签证的审核已经愈发严格了,一旦发现领事有问题就要被‘脱裤子’。” 非法劳工现状—— 在韩国人的求职选择中,Danger(危险)、Dirty(肮脏的)、Difficult(费力)的3D行业很少被考虑。于是,建筑工地的工人,餐馆中的刷盘工、切菜工,韩国家庭中的保姆以及钟点工,成了国外非法滞留者的“天然”选择,中国劳工在其中占了相当高的比重。 相对于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非法劳工而言,中国人收入最高,但同时中国劳工也承受着最高风险,诸如工资拖欠,产业灾害,交通事故 9月15日清晨的汉城九老区加里峰市场,行人寥寥,一派沉寂。除了一家牌匾上写有中文“大果子”字样的餐馆外,数百米长街上密布的餐馆都没有开张,一路数下去,阿里郎饭店、松花江饭店、中国故乡食品……用中文标示的餐厅不下几十家。 这里是在汉城很有名气的“中国人第一街”,以中央市场为中心,居住着超过1万名的中国劳工。 和大林洞不同,这是一个韩国人进出不便的地带,连卖电冰箱、洗衣机的旧货市场的顾客也全是中国人。 “大果子”店是出售油条、豆浆和馄饨的早餐店,虽然规模小到只有3张餐桌,但一直没出现过“空台”。当街区不远处缓缓驶来一辆韩国警车时, 店主6岁的儿子正在忙碌的母亲身边窜来窜去,用韩语和汉语招待客人的是一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坐在邻桌的洪永泰告诉记者,35岁的他准备离开汉城到釜山去了。洪永泰3年前偷渡来到韩国,目前他就职的餐厅拖欠了他700万韩元的工资,因为老板破产,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辛苦钱是否可以拿到。 “合法的中国劳工一般在中小企业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如生产加工、组装元件,劳动强度大,但一旦出现拖欠工资或工伤致残,都会由中介公司进行干预或理赔。我们这种通过其他渠道出来打工的就没有那么好了,基本权益无法保障。”中国非法劳工金爱美的话是所有中国非法劳工的心声。 据韩方估算,像洪永泰、金爱美一样有过被拖欠工钱经历的中国非法劳工约有8万人。 从事维护中国非法劳工合法权益的韩中交流协会会长宋相浩告诉记者,该协会自2000年1月至今,已经无偿受理5676件拖欠中国非法劳工薪水、押金、借款的求助,涉及金额108.45亿韩元,共解决了2227件,为中国劳工讨回应得收入36.89亿韩元。 他介绍,在韩中国非法劳工因为身份问题,无法在银行获得存款账户,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将钱存在打工的老板那里,老板一旦经营不善,就很可能不支付累积下来的巨额存款和工钱。由于中国劳工因“钱势”而动,经常变换工作地点,不少韩国小型企业都要求中国劳工事先交纳300万——500万不等的押金,这笔钱也在拖欠之列。 韩中交流协会编辑局局长李永汉向记者讲述了协会解决的第一个拖欠工资的案例。那是2000年初,一位51岁的中国女性找到协会,她两年前从吉林省到韩国,1999年起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因为男性老板待她很友善,她便将7个月的工钱600万韩元存在了老板处,不久,餐馆因为生意不好而关门,当她想讨要自己的存款时,老板对她说,“钱我不会给你,你再要我就报告给警察署把你抓起来,遣送你回国。”接受求助后,李永汉给那个老板拨了第一个电话,他态度仍然很野蛮,“你们还敢来管我的事,她是非法滞留,你们是不是也是非法滞留?你有本事就去告我吧,要是让我看到你,我一定用斧头砍掉你的腿和胳膊。” 尽管忐忑,李永汉和会长宋相浩还是决定和老板见面。 真的见面了,在得知宋相浩是韩国人,协会提供的是无偿服务后,老板的态度立即软了下来,在被告知协会将起诉他的不义行为时,跋扈的老板当即跪下谢罪,拿出了自己的“失业者登陆证”,希望能够宽限一周的时间。在韩中交流协会的坚持下,第二天,600万韩元便通过协会交到受骗中国劳工手中,这位中国女人拿出了30万韩元酬谢,被婉谢后,便回身融入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并很快更换了住址和电话号码。 不是所有的“讨工钱”都很顺利,一次,一位韩国小企业主以“办新企业”为由向中国劳工借款2000万韩元,随后便更换电话,转移住处,协会先后派人在仁川、汉城,甚至中国的温州寻找他的踪迹,尽管见到了人,钱还是没能要回。 与巨额工资拖欠相伴的,是产业灾害(工伤)和交通事故这类飞来横祸。供职于维护中国劳工权益组织的韩国律师朴真焕对记者说,产业灾害主要发生在建筑业等韩国人很少从事的3D行业,中国劳工一旦发生意外,就有权益受到损害的可能。一次,一位中国劳工在现代集团开发的某工地被砸伤,当朴真焕代为处理时,工头以“他是自己受的伤,工地不知道”为由,让受伤劳工“滚出去”。 据他所知,在事故中丧命的中国劳工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人。而2002年底,韩方公布的在产业灾害中伤亡的中国非法劳工为2760人。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中国非法劳工在韩国遭遇交通事故时,保险公司多以在中国国内的收入水平为标准进行处理。每个有家属在韩国的中国家庭最大的愿望,都是家人能够平安。 其实,在韩国的外国非法劳工中,中国籍一直饱受“嫉妒”,只是因为收入高一些。客观地讲,中国劳工所从事的行业也是最危险和艰苦的,此外,在赴韩成本的比较中,中国人也居于高端。韩国京畿开发研究院以204名外国劳工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外国劳工入境所需费用平均为3930美元,从事制造业占35%,从事建设业占22%,每天平均工作11.1小时,月均工资96万韩元。完成此次调查的金容勋教授介绍,由于国籍不同,所需的费用和办理时间差距也很大。 费用和时间成本最大的来自中国,朝鲜族和汉族也有差异,分别为7500美元和19.8个月,4200美元和11.6个月。而菲律宾人的赴韩成本只是1900美元和9.5个月。 非法务工的风气也影响到在韩国的外国留学生,据有关部分的不完全统计,在韩留学的外国学生中,每7人中就有1人是不顾学业而专门从事非法就业的“问题学生”。这个判断出自出入境管理局的一项调查,共计13.5%的留学生因退学、长期缺席、所在不明被划为可疑。 本刊在调查中了解到,韩国政府为了防止出现留学生为就业而逃离学校的现象,已经实施了“每周20小时、假期不限时”的留学生就业制度,但由于条件过于苛刻,这种“半工半读”的方式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非正常的角色错位—— 他们被称为“非法劳工”,但他们拥有更重要的角色,那是父亲、丈夫、儿子,那是母亲、妻子、女儿……作为背井离乡的“淘金者”,他们承受的辛苦劳作和难言寂寞是难为人道的,因为夫妻长期分离,因为母子不能团聚。 2001年8月13日,是在汉城的143位中国非法劳工的节日,这天上午,载着143个孩子的航班从中国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在接下来的15天时间里,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孩子们将与在韩父母团聚。 “是泪水的海洋。”策划此项活动的李永汉在回忆时说。 每个人都只记得出来时孩子的样子,但他们知道回国探望是不现实的,作为在韩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留有“非法滞留”案底的非法劳工,一旦回去将无法再叩开韩国之门。唯一的选择,是压抑最真实的这部分感情,通过不断寄回服装、玩具和生活费来延续关爱。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整整10年没见过自己的孩子了。 久别的相聚总是充满戏剧性。为了避开不必要的检查和可能的麻烦,急切的家长没有被允许现身机场,他们被安排在汉城阳志宾馆的一个大礼堂内。 当143个孩子由8辆大客车接到宾馆,出现在剧场门口时,哭声立即从礼堂的各个角落爆发出来。但,让每一位父母找到自己的孩子花掉了整整20分钟时间,还有两个孩子始终不肯叫“妈妈”。其中一位叫阳阳的女孩刚满10岁,母亲来韩国时她不足两岁,是她的阿姨带她长大。在亲生母亲面前,阳阳一直在喊,“她不是我妈妈,我不认识她,我不跟她走。” 15天过去了,回国的航班上空出了两个位子——有两个孩子被父母留在了身边,没人知道,还在读小学的孩子在陌生的韩国将度过一段怎样的日子,也没人能说清,他们是否能继续读书。 牡丹江市某朝鲜族中学校长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让他们回来吧,钱就有那么重要吗?”他所在的中学,去年有38名学生退学,他们都是在韩非法劳工的子女。而对于那些依然“坚守”在学校的孩子来说,不少人的生活已经变了,每个月800——1500元不等的零花钱让孩子们过早走向了社会。 在韩国,九成中国劳工的家属都在国内,一些无法忍受寂寞生活的人便结成了露水夫妻。 汉城加里峰洞木槿花幼稚园有40多个孩子,院长尹在芬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她回忆,2002年9月的一天,一位叫吴英花的中国母亲送来自己13个月大孩子,并定期来探望并交纳费用。但在今年3月21日后,吴英花再也没有露过面,按照留下的电话和地址联系,结果是“查无此人”。不久前孩子得了肺炎,治疗的费用是尹在芬自己垫付的,她也曾委托自己的中国朋友找到了吴英花的姐姐,但她也说不清妹妹的去向。孩子可以继续留在木槿花幼稚园,但尹在芬很担心孩子的明天。 韩国法务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在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第二年的1998年,非法滞留者的数量曾经锐减,但随后每年的增幅都很大。 本刊未能被获准进入外国人看护所采访,那里是即将被遣返的中国非法劳工的最后停留地。我们所知道的是,去的已经去了,来的正在路上。(撰稿/李清川)(来源:新民周刊)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2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