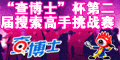| 河南“艾滋村”:过期药品正在“维持”生命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19日10:06 沈阳今报 | |
 艾滋村的一个角落 首席记者张晓宁、陈铁文并摄 河南文楼,一个只有3000多人口的豫南小村。如果不是1996年部分村民集体发病、如果不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的惊人发现、如果不是“中国民间预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的勇揭内幕,或许,这个艾滋病肆意泛滥的国家级贫困县会永远默默无闻,无声无息。如今的文楼,正如当地一位身患艾滋病的村民说的:“我们文楼出名了,因为艾滋病” 三轮车车主:文楼村是个“鬼地方” 隆冬的上蔡,细雨蒙蒙。料峭的寒风挡不住村头田地里的浓浓绿意。 从上蔡县城到文楼村不过两公里的路程,可对于拉脚的三轮车主王大姐来讲,这段路却如同黑夜般漫长。王大姐把她极不情愿拉记者去的原因解释为“那是个鬼地方,出来进去身上会沾上霉气。” 已经有三年拉脚经历的王大姐坦言,赚钱是最重要的。可面对文楼,她的表情很复杂。 自从文楼村的事上了中央电视台,一种阴郁便弥漫了整个上蔡县城。和王大姐一样,所有的三轮车主都有意无意地排斥文楼。谁都不愿坐有艾滋病人坐过的车,尽管大家都知道艾滋病病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播,可就是忌讳。 “文楼的村民也真是可怜。”一路上,王大姐不停地为这个苦命的村子叹息。自从文楼有爱滋病感染者的事实悄然在周边地区传开后,村里养的猪牛羊,生产的粮食蔬菜瓜果便很难卖出去。在多数人眼里,艾滋病无异于一场瘟疫,半点不可沾染。 更让人害怕的是,一个“艾滋病人很野蛮”的说法在县城里广为流传。在去文楼的路上,王大姐不停地善意提醒记者,村里的艾滋病人很野蛮,不但会勒索陌生人钱财,还可能因行为过激而发生一些悔恨终生的事情。 一种莫名的恐惧蔓延在空气中。 村委会主任:近200人已死于艾滋病 文楼村村委员。一个简单整洁的小院。面对记者的突然来访,村委会主任程四国脸上露出了少有的惊喜。“你们真的应该到村子里去看一看!”60余岁的程四国在文楼村村委会工作已经有三个年头了,对于文楼的现状,他感慨万千。 文楼村共有3170人。从1996年村里陆续有人死于“怪病”后,死亡的阴影就开始笼罩着这个贫困小村。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村里死于艾滋病的村民已近200人。更让程四国感到难过的是,这些死亡的艾滋病患者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这正是大好的年龄啊,他们说走就走了。”说这句话的时候,程四国掩饰不住深深的悲伤。 在程四国的眼里,村里那些艾滋病人绝非外界说得那样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尽管有一些担忧,善良的程四国还是决定为记者带路,“为了村民,我豁出去了”,可就是这时,村书记刘同新回来了。程四国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迟疑。对于记者进村采访,刘书记坚决反对。乡里、县里、市里和省里的介绍信,一个也不能少。 进村无门,记者只好按照刘书记的要求,去找芦岗乡政府的有关负责同志。去芦岗乡的路上有些异样,成堆的沙土堆在路旁,许多建筑工人冒雨忙碌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气愤地说,政府正在大修马路,只为了迎接一位近期要到文楼视察的领导。在老人的眼里,一些官员太喜欢搞形式主义了。 在芦岗乡政府,“芦岗乡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几个大字异常醒目。负责接待的赵部长很是热情,在详细地记录了记者此行采访的计划后,便对艾滋病三个字讳莫如深。 和文楼村的刘书记一样,赵部长提出:要进文楼村,需层层请示。还是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悄悄地告诉记者,“上面有指示,不让记者擅自进村采访,谁也不敢担那个责任”。 在上蔡县政府,经过与官员们的一番斗智斗勇,记者终于获准进入了文楼村。 村书记张口:要采访先得拿十万元 文楼村村头的小桥旁,一间上锁的破旧小屋孤独地迎在风中,道路两边是小块的荒地。一位好奇的村民黯然地站在一边,他说,小屋的主人已经因艾滋病死了很久。和他一样,每个路过此地的村民都会有一种无言的悲伤。 对于陌生人,村民们有着别样的警惕和好奇。记者进入村子的短短十分钟时间里,平静的村子很快开始沸腾,村民们奔走相告,很快聚集到村头。“你们是记者吗?我们都是艾滋病人,你们是来听我们讲心里话的吗?” 人群中,一名穿紫色羽绒服的中年女人径直走到记者面前,打量良久,然后指着身旁的一名男子说,“想采访他吗?我们文楼有个规矩,记者要采访,先得拿钱,没钱甭想采访。采访一个病人,两个数儿。” 震惊。气愤。无言。一旁的老人偷偷扯了扯记者的衣角,小声说,两个数就是两千元,她是村子里管计划生育的,每次有记者来,她都撺掇村民要钱。 混乱中,忽然传来阵阵叫骂声。“要采访先拿十万元。”村书记刘同新红着脸摇摇晃晃地走来。 见记者在村卫生所正要对排成长龙的病人进行采访,刘同新气急败坏,冲过来,边喊边用手拉记者的衣服,将记者拖出了卫生所。 对于记者没能按照相关规定进村采访,刘同新显然很生气,把记者的采访定义为给他惹事儿,“谁让你们进村的?谁让你们随便采访的?给我拿钱来,十万元,一分不能少。” 对于刘同新阻拦记者采访并要钱的事儿,村里的艾滋病人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文楼村经媒体曝光,在全国“出名”后,对文楼名誉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作为村里的主要负责人,刘同新不想让这种不良影响继续蔓延下去。而更多的村民则认同另一种解释,就是刘同新很怕记者了解到艾滋病人真实的生活。 这里的多数艾滋病人认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和治疗情况远非外界宣传的那样。 村民的说法:一年25元救济金太少 离文楼村村委会大约两里地,是村里的卫生所,很大,人也多。一种乡村里少见的红火和喧嚣。村民说,建这个卫生所就是文楼作为中国艾滋病重点疫区而享受的特殊待遇。这在上蔡县所辖的几十个自然村里,也是独有的。 村民孟结志说,2001年,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办公室主任殷大奎亲自来到了文楼村,转达了中央领导对艾滋病患者及家属的问候,还亲自为病人检查身体。不久,文楼村就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负责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组及专家组。中央及河南省各级政府划拨专款,在文楼村设立卫生所,对患者进行免费医疗救治。 然而,这些在外界看来非常到位的救治措施并没有完全实现。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免费治疗。和上蔡县其它感染艾滋病人需要凭券购药相比,文楼的艾滋病人在村卫生所领药和治疗是完全免费的。可这种免费却让人不甚满意。 治疗的含义,村民自有一番解释。“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这就是卫生所的现实。至今为止,村民们免费领到的药品中并没有什么特效药,只是一些常用的药品。记者在村民马深义家看到了他刚刚在卫生所领的地塞米松和维生素D2果糖酸钙。 在记者来到文楼的前三天,村北一户人家的老夫妻俩刚刚因无法控制的艾滋病病情而死去。哀伤凝固在文楼的上空,久久不能散去。 和治疗艾滋病相比,生存对于这些染病的村民来讲,则是另一种悲伤。记者从河南省卫生部门了解到,到目前为止,文楼村先后得到各级政府拨出的救治救助资金、物品已超过600万元人民币。 听到这个数字,村民们很惊讶。 上蔡县艾滋病防治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县里和芦岗乡对文楼最为“偏爱”,村里的艾滋病患者情况,政府手里有一本花名册,每个季度发放一次救济金,按照各个家庭的艾滋病患者人数,分别为30、40、50元不等。 然而,许多村民都反映,县里和乡里的救济金并没有如实发放,有的家庭一年才领到25元救济金。 人多地少,是整个河南的现状,文楼也不例外。艾滋病侵蚀了人体的免疫功能,直接造成病人身体状况极差,很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了生活来源,只能靠政府救济。可一年25元的救济金,实在是杯水车薪。 村卫生所里--各种过期的药品太多 对于村里卫生所的药品问题,村民们一直意见颇多。 用村民孔万里的话来讲,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经常发现过期药品。 去年春天,孔万里在一次去卫生所看病时发现,他开的环丙沙星已经过期一年了。 和孔万里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村民老张。去年老张的妻子发病去卫生所治疗,挂了几天点滴,丝毫不见效。后来细心的老张发现,治疗所用的药品已经过期多日。愤怒之余,老张领着妻子去县医院检查,花了几百元才把病情控制住。 愤怒的村民曾就此事找到当时上蔡县主管卫生的副县长。这位官员解释是:这些药品都是各地献爱心捐过来的,没有时间逐一检查生产日期。 上蔡县预防艾滋病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此却令有一番说法:文楼村所有用于艾滋病治疗的药品都是经过政府公开招标的,通过严格把关才发放到村里的,绝不可能出现药品过期的问题。 2003年9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曾在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上坦言,治疗艾滋病的药品在分发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费用,这些都是由地方政府来配套。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病情比较重的地方,病人比较多的地方,在管理上可能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 残酷的现实--最小的患者只有四岁 一个怀抱着熟睡男孩的中年男子,从村卫生所走出来的落寞,定格在记者的记忆里。旁边一位大娘叹着气说,那名男子怀里抱着的,是村子里最小的艾滋病患者,今年只有四岁。 中年男子叫马深义。他的家庭悲剧,是整个文楼村不幸的缩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官办和私办的采血站在河南驻马店泛滥成灾。卖血,做为一种远比田地劳作轻松得多的“职业”,得到了文楼村绝大多数村民的热爱,并成为村民们赚钱的主要方式。而马深义一家就是当年浩浩荡荡“卖血大军”中的勇将。马深义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卖血时只有17岁。新奇、刺激、来钱快,是当时卖血人的感觉。虽然一次卖血换得的50元钱不多,但对于年收入不过千把元的村民来说,还是极具诱惑力的。马深义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种让他感到“很正规、来钱也快”的赚钱方式,会在若干年后给他的人生抹上浓厚的悲剧色彩。 马深义的父母、嫂子、妻子,都已经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给马深义留下的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无尽的恐惧和悲伤。 在马家破旧的房子里,一只昏黄的灯泡有气无力地亮着。马深义无力地摇着头,叹息自己随时可能失去的生命。 除了11岁的大女儿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外,7岁的小女儿和4岁的儿子都染上了可怕的病毒。面对这个随时可能破碎的家庭,马深义说他看不到未来,惟一的希望就是健康的大女儿早日长大,走出这个村子。 7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蹲在地上逗一只小狗玩。清澈无邪的大眼睛,看着让人心疼。马深义说,她们还小,不知道艾滋病的可怕。可他清楚,如果有一天,他走了,给孩子们留下的将是什么。 更深的痛楚--300个孤儿谁来抚养 走出马家,一名同样是艾滋病患者的老人告诉记者,艾滋病给文楼带来的伤害,不止是掠夺人们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村里留下的孤儿有300多个。抚养这些孤儿才是最难的事情。 在文楼村,独自承受家庭重负的绝非马深义一个人。至于不再婚的原因,马深义的言语中尽是无奈。“我有这病,谁敢跟我呀!别说我了,就连村里正常的小伙子,找对象都难呀。”这种说法在程四国那里也得到了证实。在文楼村,姑娘外嫁时要经过层层体检,才可能找到个人家;最难的是那些男青年,根本没有姑娘愿意嫁进来,无论你拿出多少份身体完全健康的证明。 在很多上蔡人眼里,那些在村子里等待政府救助的文楼村民都有好逸恶劳的恶习。对此,一个姓程的文楼村村民深感冤屈,曾在北京打工的失败经历成为他一生的痛。2000年,27岁的他,怀揣着梦想,外出北京打工。没想到一提自己是从河南文楼来的,就换来一张张冰冷的面孔。四处碰壁的他,最终只好回到家乡。 为了避免伤痛,无助的文楼村村民甚至想到把户口改成别处的,在他们看来,这是无奈之举。 为文楼感动--艾滋病患者相互支撑 和自家的贫困相比,文楼人骨子里的善良更是让人感动。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没有一位村民提出要钱和捐助。相反,村干部“勒索钱财”的行为,却让他们深为愤怒。“记者都是为我们好,他们那样做太给村子丢脸了”。 在马深义家,记者曾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看了看自家破旧的家门,沉思片刻说:“你们帮帮戴俊英家吧,她比我更可怜”。 空气中,一种温暖氤氲于心。 35岁的戴俊英,一个被认为文楼村最可怜的女人。丈夫死于艾滋病,留给她一个13岁的儿子。同样患病的她,因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而精神崩溃,毫无劳动能力,每天靠村民们的救济生活。 告别文楼的时候,许多村民自发地为记者送别,站在村头久久不愿回去。黄昏中,他们脸上的期待格外清淅。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