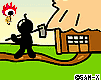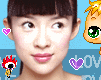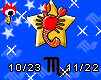| 《南方都市报》社论:给慈善家更宽松的环境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21日10:52 南方都市报 | |||||||||
|
社论 近2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的财富急剧扩张,尤其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涌现了一批拥有相当数量财富的富人。不过,慈善家的人数却似乎并没有同比例增长。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富人本身尚没有发育出比较浓厚的公益精神。中国的富商们刚刚发财致富,还没有从商战的硝烟中走出来,甚至大多数仍拼杀于商战中,这个时候,他们更多地为了商业本身而生存,尚无暇他顾。通常情况下,只有当企业家从一线商场厮杀中退出后,才有余力观照自己的心灵,寻求生命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 另一个原因是,当下的社会环境,似乎让富人们鼓不起精神。某些群体存在着仇富心理,而整个社会对富人们缺乏足够尊重,尽管大家都羡慕他们的财富。这种社会心态,让富人们不愿、也不敢掏钱;而富人们“为富不仁”,又让社会对富人更加鄙视。如此恶性循环,以致近些年的慈善活动似乎以普通民众为主体,富人们反倒没有突出表现。 而就政府而言,没有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政策,为富人们服务社会提供充分的激励。比如,民间基金会的成立、审批设置的门槛太高;缺乏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基金会的活动有诸多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正当其时。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具有公益精神的富人们服务社会的渠道,并使基金会的活动更为规范。 但也许是太强调规范化了,这个条例反而提高了设立基金会的门槛;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基金会的具体运作模式,规定得过于详细,以至于没有给基金会的创造性发展留出足够空间。 事实上,发展民间基金会,不光是为了吸引民间资金,也是为了有效地利用富人们的企业家精神,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士来管理慈善、公益事业,从而为公益事业注入活力。因此,推动基金会发展,需要政府提供更为宽松的政治、法律和政策环境,让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慈善活动家、社会活动家涌现出来。 一谈论起基金会,人们就对美国私人基金会的繁荣羡慕不已。但人们容易忽视,在这些基金会背后,活跃着一批慈善活动家,正是他们,不断地尝试筹资的新渠道,开拓慈善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新领域。根据这样的经验,一个可取的基金会法律、政策,应当鼓励更多具有公益精神的人士参与社会的治理,不仅贡献他们的财富,也贡献他们的智力。 为此,首先需要改变政府本位的社会治理观。以计划体制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政府是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发展经济要靠政府,繁荣文化要靠政府,甚至连近些年来的慈善活动也是靠政府组织的。然而,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可能长期依靠政府的权力自上而下地组织,而必须依靠社会的自我治理,即由民间社会在政府之外提供部分公共服务,比如,对弱势人群提供救助,发展文化、科学、学术、艺术事业。他们既可以补充政府的缺口,也可以与政府竞争,推动政府提高效率。 基金会不过是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治理的一种形式,政府还应该鼓励企业家、富人、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寻求更为多样化的形式。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就一直活跃着大量公益、慈善组织,他们不仅承担起了提供社会救助的责任,甚至供应了社区的大部分公共服务。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自发地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既激励了富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也维护了弱者最基本的尊严。 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提供恰当的制度框架,恢复我们的这一优良传统。这里的法规和管理,可以更为宽松一些。必须的防范措施当然是需要的,但对于愿意涉足公益事业的人士,我们也应当保持足够的信任、尊重,给他们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