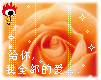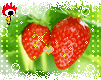| 讲述殡葬工人独特的"地下生活" 烈酒成最好的朋友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05日09:32 新华网 | |||||||||
|
老殡葬工小月致信记者讲述广州市300多名殡葬工人独特的“地下生活” 这是一封让人感慨的来信,细致地记录了一种普罗大众难以想象的生活。昨日是清明节,当广州几十万市民带着鲜花,踏着青草举家祭祀远去的亲人时,一封长达20多页的来信被送到记者案头。它出自一个长年与“死人”打交道的老殡葬工人小月之手,感性而细致的万语千言述说了广州市300多名殡葬工人独特的“地下生活”,掀开了蒙在这个独特职业上的
工作篇 每天都有人死亡,除了大年初一,殡仪馆一年364天都不能休息。每天,殡葬工人都在遗体、棺材、骨灰、花圈、挽联、黑纱、灵堂中打转,看到的是悲痛欲绝的丧主、愁眉紧锁的吊唁人,听到的是催人泪下的哀乐、悼词和呼天抢地的哭泣声,再加上火化炉的轰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为丧主服务的信念,一天的工作是很难挺过去的。———小月 防腐工和冷库工:每天都在打冷战 在殡仪馆工作首先要过恐惧关。小月说,许多去过殡仪馆的人觉得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追悼会上几十人、几百人围着一具遗体,灵堂外阳光灿烂,灵堂内灯火通明,经过精心处理的遗体容貌安详,人们当然不会产生恐惧。但在清洗防腐室里、化装装殓厅里面对十几具乃至几十具遗体时,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小月说,当他们走进地下室,推开冷藏库那扇冰冷沉重的金属大门时,阴暗的灯光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800具惨白的遗体。他们躺在多层铁床上,姿势不一,容貌各异,有的睁大眼睛,有的张开嘴巴,有的作挣扎状,有的作狞笑状,女的披头散发,男的怒发冲冠……阵阵冷风夹着恶臭扑面而来,让人不禁打冷战。 “这时我们最能体会到生命的脆弱、渺小和死神的凶残、无情。”这些情景殡仪馆的防腐工和冷库工每天都要经历,他们常常1个人在里面进行检测、验对、清扫和消毒。 收殓工:烈酒成了最好的朋友 收殓工是殡仪馆接触遗体的第一道关口,他们负责把死因各异的遗体送进殡仪馆,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因为“非典”等疾病去世的死者往往具有传染性,收殓工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全副武装披挂上阵把遗体从太平间“抢”来;有的无名尸体发现时已高度腐变,这种情况要先杀虫消毒;溺水的遗体则肿胀得如吹起的气球,一碰就烂,腐肉要用双手捧进尸袋;在房屋坍塌现场和地方狭小的阁楼,搬运遗体时担架床派不上用场,收殓工只能把遗体驮在背上。 由于收殓工处理这些遗体时,衣服、头发甚至皮肤的毛孔都会吸入尸体的腐臭气味,无论事后如何擦洗,都难以覆盖住这种特殊的气味———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烈酒,因此酒成了收殓工最好的朋友。 化妆师:面对非典遗体化妆 最让广州的殡葬工人们难忘的,是去年2月10日的一幕,殡仪馆接到了广东省中医院的报丧电话,要求派车接运一名吴姓的“非典”死亡遗体。为可能仍具有传染性的遗体穿衣、化妆是最艰巨的任务,要完成任务工作人员必须和遗体亲密接触不可。 此时,自动请缨上阵的“敢死队”来了,他们是年轻的防腐员夏国欣和邱志超。两个小伙子都明白,这时做好个人防护的重要,因此穿防护服、戴帽子时特别小心。他们首先将遗体解冻抹净,然后相互配合协作,小心地为遗体换上衣服,尽量避免大面积地碰触遗体。穿衣入棺后,夏国欣开始为遗体耐心细致地化妆———当时,他和死者的面部相隔不到20厘米。 20分钟过去了,在夏国欣的精心打扮下,死者面容显得安详沉静,仿如生前。死者家属看后都深感满意。夏国欣说,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的必经阶段,我的职责就是不能再让死者家属看到自己死去的亲人憔悴、痛苦的面容。 生活篇 广州殡仪馆是一个绿树成荫、碧草如茵、鸟语花香的地方,这里的工作人员身着笔挺西服,有的出入还开着私家车,让来殡仪馆办事的人羡慕不已。可谁又能真正明白在这些表面风光的背后,我们生活的孤独与苦涩呢?———小月 “厌恶行业”:工资虽高却无人愿做 喜欢爱神厌恶死神是世人的共性,因此殡葬行业在国际上被称为最典型的“厌恶行业”,许多人对这个行业都望而却步。同样,在国外,人们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这项工作,因此这一行的薪酬待遇特别好,以吸引更多的人成为殡葬工人。 “但收入高不代表一切,实际上我们常常潇洒不起来,面对每天的工作我们需要无比的勇气,面对社会我们只能自嘲是孤家寡人。”小月沉重地告诉记者,因为顶不住强大的工作压力,曾经有一个年轻的职工疯了———大学本科毕业的小雨聪明伶俐,好学上进,责任心强,由于长期在压抑的环境下工作,有一天在一个遗体告别仪式上,她忽然和丧主一起嚎啕大哭,然后掏出人民币当作冥币般洒落在地上。 社会歧视:殡葬工婚姻都内部解决 最让小月难受的仍是来自社会的歧视———“来自世俗的偏见让人们总觉得和我们这一群终日与死人打交道的人来往会交上霉运,从此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一群,许多正常的社交活动每每会因为我们的出现而在人们的心头蒙上阴影。” 小月说,自从他入了行,朋友的婚礼、寿宴、满月酒席再看不到他的身影;过年了,他们从不敢登门拜年,老同学生病了,想到医院探望一下也被其家人婉言拒绝。有的人甚至连和他们握手也不愿意。“渐渐地,我们变得自觉而又自卑,工余时间躲在家里看电视成了唯一的娱乐。” 组织家庭,更是殡葬工作人员难言的苦涩。“连普通的交往尚且如此忌讳,能勇敢地丢弃偏见和殡葬工人组成家庭的人就更难找了。”小月说,上世纪70年代,来自农村的20多名退伍军人被安排到殡仪馆工作,当时没有一个女孩愿意嫁给他们,熬不过婚姻家庭这一关,短短几年这些20多岁的小伙子走的走散的散都离开了殡仪馆。 因此,馆里的许多年轻人在恋爱初期,每每恋人问起他们的职业,他们都闪烁其词,心想等感情稳定了再说出谜底,可往往对方一知道真相,很快就和他们“再见”了。“时间长了,我们殡葬工人的婚姻往往都是在职工内部解决。” “死亡游戏”:最心痛是子女受伤害 好不容易有了家庭,可因为职业给子女带来的伤害就像心头的一把刀。小月说,他的女儿曾在上幼儿园时回来对他说,“爸爸,我以后再不上幼儿园了,人家说我玩的是死亡游戏,同学们现在都不理我了。” 什么是“死亡游戏”?原来小月的孩子和其他小孩抬着玩过家家,她抬着“新娘”走了两步,就被家长呵斥她像抬死人,要她赶紧停下来;她替洋娃娃穿衣服,别人说她在穿寿衣;她哄洋娃娃“睡觉”,不经意用小毛巾遮住了娃娃的脸,“盖尸被”的恶言立马向她袭来。“试问,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怎么受得了这种伤害?” “我们的行业虽然特殊,但职业是没有贵贱之分的,面对歧视我们挺住了,可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忍心她再受伤害呢?”满目是小月在字里行间透出的悲凉。(完)(来源:广州日报)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