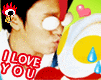| 中国翰林院的明与暗:海外学人论述中国职称改革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20日12:22 中国青年报 | |||||||||
|
本报记者 沙林 任何一种改革在中国都会激起波澜。 黄纪苏等学者在给社科院领导的一封信上说:“最近酝酿出台的本院科研人员津贴改革方案‘传达’下来后一片哗然,说得准确一点,是群情激愤。这个方案在基本思路上是
“大家的不满集中在两处。一是把专业人员根据现有等级体系分作十一等;二是划出百分之十五的硬性比例,实行末位淘汰……” 对这种等级观念极重的改革,记者所接触的所有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国学人都不赞同。他们以自己在西方所浸淫的学术精神,对人文学界的种种改革进行了评说对比。他们认为关键要弄清楚学术是什么?是一个民族从沉沦到腾飞的精神底蕴,还是商业上简单的工具和实用的观点? 等级不是好东西 上世纪80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到法国学习、写作,并获得法国人文学科最高国家荣誉“骑士勋章”的亚丁说:“等级真不是一个好东西。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等级,都跟所有的门槛一样,必然会出歪门邪道,必然会失去本来的初衷而成为一种变味的东西。” 他刚主持了法国电影周的开幕式,因此非常感慨法国艺术的泉涌内力:“现在中国真正要做的是怎么把广大人文学者的心思集中到学术冲动和学术创造上来,而不是让他们去苦思冥想怎么买好、怎么攻关以拿到学术等级。 “国内把学术搞成了等级制,跟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分法是错误的。一个人的知识学问是不能以数字来衡量的,尤其今天人文学科广泛交融,不可比性更多了,怎么能整齐划一呢?我一直认为,学术成就是才能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等级奖励的结果。” 亚丁曾多次在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讲课。他说,法国的讲师和教授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教授只有有席教授(有授课权利和任务的教授)和无席教授之分,报酬也不看你的级别,而是依据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亚丁认为,中国的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稳妥的办法来激发和安抚广大社科学者,如今不得已搞出这么复杂的等级制来,可能是有情可原的。中国人的价值观比较复杂,做任何事都要找一个可以定量的东西来,但这与真正追求学术没有关系。西方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市场(学术市场)和创作的快感和名气上,而我们体现在等级上的位置,这就造成了我们人文学者的不自信,一定要有一个印着等级的名片,内心才稍安…… “学术市场调节也渐在中国兴起,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要公平得多。它摒弃了等级,谁能干什么就拿什么钱。比如我曾被美国斯坦福大学邀去讲学,一个小时5000美元,当时是1992年,我只是作家身份。他们为什么没有邀请名声更大、职务更高的人去讲?因为只有我能讲中法美三国文学的对比。当时东道主开玩笑说,‘我们给你的可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的待遇’。这种系统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加激励人奋进。当然这得有个前提,决定这个事的不是不想干事的某个官员,而是学术委员会、董事会或者是各有成就的评委。” 美国也有职称 “我为什么不同意搞那么多等级,关键是我们很难有公正评价。谁有资格评定学者?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原中国科学院学者、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泰德传媒有限公司总裁张猛说:“这些评选学者级别的应是有资格的、偶然的评委,而不是专职的局长或主任。 “我们的执法过程也大有问题。大家坐在一起,必然有照顾情面、生怕报复等心思。在西方经常是‘偶然的’评委用通讯方式进行投票,这种松散没有一定之规的方式,反而能更大程度地表达评委的真实想法,有些像美国的群众陪审团制。” 张猛说,职称这个东西,西方尤其美国也有,这就是讲师、助教授和终生教授。在美国,当了终生教授后可以后半生衣食无虞,很有点大锅饭的味道。这个制度好处是保护了学术自由,坏处是使大家拼命挤职称这个独木桥———美国学者也为了这个大伤脑筋。助教授到教授这一关极难通过,讲师也不是我们意义上的助教授和教授的中途站,而是那些没有挤过独木桥的人不得已的职业。所以说,美国的等级制度也是残酷的,但基本上是沿着真正学术道路的残酷,不像我们有更多的非学术因素。美国大学的教学水平为什么为全世界所承认,就是因为他们在本科一年级就全是终生教授来教(助教授反而去带研究生)。 鉴于国外经验,张猛认为,总的来说,学术应是民间的,不应是政府的,国家不应动用资源来为学者评什么级别、职称。 社科院是太舒服吗 学者等级、学者报酬之争其实都源于更根本的学术院所的制度。这种专门养学者的像中国古代翰林院式的社科院、研究所、作家协会的存在,已经引起了争议,并直接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的产生。 曾在中国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工作过的张猛说:“西方学者曾对我感叹:你们的社科院太舒服了!确实,我们的社科院这种形式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它模仿的是前苏联的体制,由国家养起一批人,不用教学,不用上班……而西方也有研究院所的称谓,但里面的学者都是有教书任务的。这些院所一般都不是一个国家性质的正规组织。我们把它们翻译成‘社科院’、‘科学院’,好像与我们等量,在我们这个体制上再进行等级划分(评职称),这就把某种弊病推向了极端,我称为‘极端形式的现代化动员机制———一种行政上的号召形式,每个级别都向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不是向学术、向学术道德负责……如此一来,除了任人唯亲外,还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任人唯派(左派、右派)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当然会把学术秩序搞乱,以致现在中国学术道德状况很不理想。” 宽容出大师 在学术和学者待遇方面,几位学人都认为,西方是宽容的。张猛说,在有级别的情况下,西方的动态性(奖励的及时和机动)比咱们灵活多了,但又对学者和教授很宽容。只要你没有学术丑闻和性丑闻,哪怕你在学术上没有建树,你的学术地位和生存都没问题。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家西部大开发干部研修工作办公室的徐轶尊的观点比较尖锐。他认为,现在国内人文学科的改革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这位制度经济学学者的观点,与“社科院太舒服”的观点似乎相左:“改革当然是为了保留有价值的学科和学者,去掉一些没有价值的混混学科和学者。但这种认定很难。比如钱钟书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翻译身份,谁能料到他以后《谈艺录》、《管锥编》一篇篇成为学术上的重鼎?在国外也并非做一个学者就一定要有voice(声音),很多学科由于它的前瞻性而并不被当时的人所认识。所以在学术上我们要向美国学习,宁可错漏一千(养一千个庸人)也不要错杀一个人才。良好的评价体系和学术制度确实重要。但什么是良好,众口不一,所以就干脆宽容吧。” 徐轶尊认为,现在中国在学术上已经到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时期,与17世纪的德国很类似,那时,欧洲其他列强已经过了文艺复兴,而德国才懵懂刚醒,但它后起直追,为人类贡献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师:康德、黑格尔、尼采、歌德、贝多芬……他们没死的时候,他们许多人并不被认为是大师,但德国养护了他们。 中国的学术有待复兴,这需要一个宽松环境。而我们的方法十分简单,就是竞争,所有的学者都为了现在而竞争,没有未来。而学术是什么?是闪着三千年光芒的东西。岂能为房子、职称去扼杀一个民族可能有的大师? 目前中国学术界除了宽容,还缺体系。徐轶尊说:“我们现在的学科体系千疮百孔,经济学刚刚起步,政治学还没有,心理学刚运用……所有学科都是互相支撑的,所以一定要小心养护。” “在对学术的供养体系还没丰富时(中国学术的养护只有官方一个渠道,没有民间的供养)对学术进行改革,弄不好就是摧残。‘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政治理由来扼杀学术的,现在我们不希望以商业理由再扼杀学术了!”徐轶尊呼吁道。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