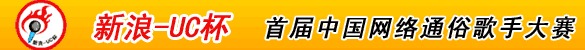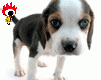| 台湾作家龙应台:白话文需要古典汉语的熏陶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29日16:09 中国《新闻周刊》 | |||||||||
|
本刊记者/方玄昌 几十年的“政治发烧”使中国人失去两件东西,一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掌握,一是对世界的认识。而古典文学,我觉得,是语文最厚实、最肥沃的土壤。白话文如果没有古典汉语的熏陶,是很单薄的
“文字是一粒种子,应该落在广袤的大地里” 新闻周刊:今天的大陆文化圈中,汉语写作有着怎样一种现状?与之相对比,港、台等地又是怎样一种状况? 龙应台:如果一定要“以偏盖全”地来说,香港的汉文水准当然比较低,这和长年的殖民历史有关。殖民对于文化的伤害之一就是,殖民者的优势语言你不容易得其精髓,而自己的语言却又被长期边缘化,结果往往是脚不着地,两边落空。 台湾也有50年日本殖民历史,但是日本统治者对文化采取强势态度要到1937年才真正开始,时间不长。而在此之前,台湾本已有本土的汉文传统,在起点上就和香港不同。国民党来了以后,它的文化“保守”反而带来好处:就是说,中华文化的传统一直受到强调,人文古典的学习一直没断过,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在台湾也等于是一脉相传下来,平均的语文素质相较之下算是还好的。 大陆则因为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文学和语文教育都大受斫伤。文革十年固然是剧烈的文化断层,之前的政治指导文化、渗透文化也使得汉文的自然发展受到影响。 文字可以比做一粒种子,落在广袤的大地里,自由的成长,它可能长成顶天立地的参天老树;把种子放在盆子里要它照着框架长成盆栽,它就会变成扭来扭去的小盆栽。政治,就是文化的盆栽。 但是我同时觉得大陆人才济济,到处都是顶天立地的种子。我们要努力的是设法让种子落在大地里,不是掉进小土盆里。 “就文化而言,‘温和’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新闻周刊:有人认为,今天大陆的汉语写作处于一种没落、断层的状态。如果事实的确如此,这种没落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与“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有何联系? 龙应台:五四的标志之一,是批判的精神。今天,大陆的批判精神在哪里?我是说自我批判,不是说对别人的批判。 再说,在五四对现状的批判里,有激进和温和之分。很多温和者,譬如胡适之,到了台湾,影响了好几代台湾人。激进者,抛头颅洒热血去追求心中的乌托邦。 历史跌跌撞撞走下来,我觉得,就文化而言,在历史“现场”中比较缺少群众魅力的“温和”,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文化本身,需要的是累积、是沉淀、是时间的淘洗和酝酿。而时间,正是“激进”所不屑的。 语文,像珍珠,在蚌壳里要从一粒沙开始酝酿,经不起任何粗暴,不管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古典文学是语文最厚实、最肥沃的土壤” 新闻周刊:我们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重新恢复汉语写作的传统?能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优美的古汉语在今天的语言、社会环境中处于更好的位置? 龙应台:几十年的“政治发烧”使中国人失去两件东西,一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掌握,一是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真正认识使人开放、宽容、理性,这种态度是做学问的基础。而古典文学,我觉得,是语文最厚实、最肥沃的土壤。白话文如果没有古典汉语的熏陶,是很单薄的。 我的意思是说,语文是思想的表达。没有思想的语文,是空的。有思想的语文,要真正的漂亮,要真正使语文成为艺术而不是停留在工具层面,古典的训练是不可缺的。 文革之后,大陆以经济作为优先的国策,但是在文化上要把失去的追回来,花的时间可能更长,要注入的心思可能更深。国民能不能用汉语充分表达思想?作家能不能把汉语的境界带到语言艺术的极致?盆栽是否能回到大树?这恐怕才真是立国之本吧。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