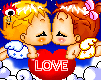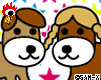| 唯一获准随军采访伊战的华人记者讲述真实故事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04日10:29 解放日报 | |||||||||
|
隗静,北京人,1995年毕业于北京旅游学院英语系,1999年赴美国留学,主修新闻,取得大众传播硕士学位。曾在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部实习。后加盟香港凤凰卫视,任派驻华盛顿记者。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天,她就在第一时间开始连续报道15个小时。此后又报道了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3月和4月期间,随美军报道伊拉克战争,成为这场战争中全球华人记者中唯一获准随军采访的女记者。在《美军中的“凤凰”》一书(同心出版社)中,隗静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随军采访中的所见所闻。
我到伊拉克就受到“骚扰” 5点多起床。天才蒙蒙亮,我们就来到了红新月会的办公楼。因为是去伊拉克,我还穿上了防弹衣,戴着头盔,全副武装。 突然间,我看到有记者在爬一辆救护车,回过头去,又看到几个志愿者正分别登上两辆救护车准备出发,其中的一辆已经被记者包围。我赶忙叫了萧燕就往另一辆车那儿跑,开了后门,里面坐着一个小伙子。我也不管他是不是反对,一边说我们是记者一边往车上爬。几秒钟之内,救护车里已经塞进七八个记者,没有挤上来的就站在车外叹气。 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我还没有定定神,香港就来了电话,问有没有可能进伊拉克?我长出一口气说:“告诉鲁豫(当天的主持人),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经过几番周折,包括半路上被科威特军警赶下救护车、站在零公里边境等着再搭车等等,我和萧燕终于在科威特新闻部的帮助下,分别坐车跨过了科伊边境的联合国非军事区,进入美军把守的伊拉克边境小镇萨扶湾。 这是一个坐落在沙漠中的穷困村落,远远地可以看到一片低矮的土坯房,一片土黄色和灰黑色。此时此地,我已经踏上了一个正在经历战争的国家的领土…… 我希望了解伊拉克人对这场战争、对萨达姆的真实看法。可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懂英语而难于交流。而他们的感想也非常令人困惑:大概一半的人说萨达姆好,另一半说不好;比较一致的是对美国的看法,不希望美国占领伊拉克。 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他对萨达姆政权如此畏惧,以至于只有在,而且不露面的条件下才肯接受采访。我想出让他戴我的防毒面具上镜头的主意。于是,他就戴着黑漆漆的面具说:希望看到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因为萨达姆自己的生活奢侈,却任凭大多数人陷于贫困。 但是另一个也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却大声喊着“萨达姆好”,他宁愿不要美国人进入伊拉克令他们失去民族的骄傲。 在记者们用心观察伊拉克人的同时,他们也在好奇地打量着记者们。在这样的场合,出来看热闹的大多是男人,少有的几个女孩子围着披巾,站得远远地打量着这么多外国人,每每看到照相机镜头就背过身去,不像男孩们那么大方。 可能是女记者不多的缘故,我被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子围住,指着我的手表、照相机和墨镜等等不停地问这问那。虽然语言不通,他们的热烈和新奇的情绪还是很快感染了我,我们一起揽住肩膀照相。他们没完没了地让我重放数码相机中刚刚照过的镜头。附近的一些男孩子们大概也听说这里有新鲜的“玩具”,都纷纷过来加入。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害羞地比划着,问能不能吻我的脸颊,我欣然低下头。哇!他的脸顿时浮现出一个腼腆的、满足的微笑,我因为能让他开心,好像比他还更高兴。 这下可在他的伙伴中造成了轰动,一会儿又来了第二个、第三个……这时我开始摇头拒绝。“爱心大使”做到这一步也算尽力了吧?可是至此我已经被一群男孩子团团围住,有的要我挂在脖子上的圆珠笔,有的拽我的手表,有的想要搂住我的腰……我严肃起来,大声说不许拿我的东西,却在推搡之间走不出包围圈。正在为难的时候,幸好《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及时赶到,把我拉出人群。我长出了一口气,说:“本来还想偷偷留下来,不回科威特去了。看来我想得太简单了。” 晚上,我和一桌中国记者吃饭时,大家纷纷提到我第一次进伊拉克遭到“骚扰”的事。我想,这件事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重新审视原来想要私自越境、租车、独闯伊拉克的打算。“进伊拉克”说起来只是简单的四个字,而为此要做的准备、方方面面的考虑,特别是对一个女记者来说,却远比这几个字要复杂多了。 我目睹大使馆已被劫掠一空 我真的已经到了巴格达! 我不无骄傲地,几乎是在享受眼前的“风景”。旁边一个CNN的主播克兰西问:“你从哪儿来的?日本人吗?” 我大声说:“中国!” 联机的时候,总部有编辑告诉我,听说中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遭到抢劫,问我们能不能去看看。没有地图,没有当地的电话,连大使馆的地址都没有。在有500万人口的巴格达怎么去找中国大使馆呢?我在酒店里的记者和伊拉克翻译之间上上下下打听,终于有一个人知道使馆的大概位置。他凭记忆帮我们画了一张草图。 我们一路找去,经过的街道都十分冷清,所有的商店都关着门。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政府办公楼和街上不时出现的沙袋堆成的掩体提醒我,这里在几天前还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萧燕居然凭着那张草图找到了使馆所在的街区!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区,我们找到了一个有淡黄色围墙的院落,看到狼藉的车库和楼上被砸碎玻璃的窗户。这是不是中国大使馆呢?几乎绕了一圈还没看到任何标志,直到把车开到正门,才看到墙上的铜牌:中国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馆。 “天哪!”我和萧燕马上跳下车。我看到正门旁边被砸得一塌糊涂的签证处失声尖叫。萧燕一边拍摄一边念叨:“怎么连桌子也砸了?这儿有什么好抢的?”我看到写着使馆名字的铜牌被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黄土。我去车里取了矿泉水和纸巾把牌子擦拭干净。 进了使馆一看,更是满目疮痍。院子里到处丢着废纸、文稿;树枝上挂着被抻出来的废胶卷;一个小池塘里也扔着垃圾。使馆办公楼里已经被劫掠一空,没有一个办公室里有一件家具,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碎。在一个房间里,我们看到散落一地的张维秋大使的名片,猜想这间大概是他的办公室。 在一个楼梯口,一面国旗被扔在地上,上面有几个被烧破的小洞,还踩满了鞋印,显示出盗匪的匆忙。“居然敢烧我们国家的国旗!”我不由自主地发火,赶忙把国旗拣起来叠好。 “不行,叠得不整齐,重来!”萧燕一边拍一边说。我们把这一面国旗和后来又拣到的一面保存好,准备以后交给台里,再由台里转交给外交部。 天色渐晚,我们不放心地又看了一眼孤零零的使馆之后不得不离开。临走把大门和后门都关上,希望至少保证它一个晚上的安宁。 晚上看到舒尔茨中校,我问他为什么不派人去保护中国大使馆,还告诉他使馆被劫的惨状。他说,他的上级正好刚刚接到中国政府请美军保护使馆的正式要求。“可是我哪有那么多人啊,小姐!”他一脸的为难,“你住在这儿还不知道吗?那么多使馆我怎么可能保护得过来?” 我说,他应该看在我的面子上对中国的使馆好一点儿。他说,他还是看在中国的面子上对我好一点儿吧。 美国大兵说:我想去看看中国 晚上没事的时候常常有美国士兵过来聊天。今天是一个叫卡尔森的小胖子请我到他值班的通讯室去坐坐。我敲门进去的时候,四个值班的小兵正在百无聊赖地打发时间:两个人在闲聊,一个在边吃零食边翻杂志,卡尔森在看小说《星球大战》。小卡尔森今年才19岁,因为他有八分之一的日本血统,所以对我的一切都很好奇。“我爸爸的爷爷是从日本到夏威夷种菠萝的。”他眨着洋娃娃一样的大眼睛说,圆圆的脸庞一副天真。“告诉我,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什么不同?难道你们不是一个民族吗?”他说,他高中一毕业就当兵了,但是这一次回国以后想去上大学:“因为我不喜欢打仗。”而且还因为胆子小被其他的士兵笑话。“你了解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吗?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他好奇地问。 “你了解吗?”我反问,“你心目中的解放军是什么样子的?” 他摇头说没怎么研究过,看过关于解放军装备的书,但是对士兵没有任何了解。“大家都说他们是红色中国的红色部队。”他几乎带着危言耸听的表情,“他们是我们面临的最强对手吗?” “干吗一定是对手呢?”我给他讲上高中军训时碰到的有意思的教官,说:“他们和你们一样,都做差不多的工作。可能他们还以为你们很厉害,每个人的头盔里都装了计算机。” “只有最精锐的特种部队才有那样的设备吧?”其他几个士兵都摇头。“如果不是这场战争用上了陆军,国会还要减我们的预算呢!和空军海军相比,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看来军种之间的竞争到处都有。”我说,比如西点军校的橄榄球队的口号是“击沉海军”。 卡尔森说我是他接触过的第一个中国人,和他印象里的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色中国’了。”我试图更正他的观念,说现在是“五颜六色”,不,是“万紫千红”。我说中国的变化太大,每一次回国我都可以发现新的东西,受到新的启示。但是现代化也给中国带来像西方一样的问题:青少年的失落、传统文化的削弱、家庭责任观念的淡化……“像你们观念这么传统的人在中国已经很少见了。你肯定很难找到21岁就急着结婚的女孩子。” “我可不会21岁就结婚,”卡尔森说,“我想去看看中国。” 美军排队打我们的“公用电话” 下午在闾丘露薇雇的翻译家吃午饭。有色拉、意大利面、还有翻译亲自研磨的卡布奇诺咖啡,对于一直在吃罐头的我来说实在太丰盛了。告别同事,我们去原来买烤鸡的小店给第二旅的官兵买些烤鸡“打牙祭”。我看他们每天最关心两件事:除了猜测自己什么时候回国就是晚饭会吃什么。 买来烤鸡几乎使我们成为驻地的英雄,官兵的赞誉不绝于耳。我开玩笑说,他们应该给五角大楼联名上书,表扬我们“拥军爱民”的事迹…… 官兵们给了我们太多帮助,我们能够感谢他们的另外一个办法是,允许他们借用我们的卫星电话打电话给家人报平安。这是比烤鸡更受欢迎、更令他们珍惜的回报方式。古诗中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第二旅的士兵大部分自从1月起就没有再和家人联络,经过了一场战争,他们的家人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所以,自从听说我们可以让士兵打电话,我们住的会议室外每天晚上就排起队来,许多人激动得还事先列出谈话的提纲。起初我们没有限制通话时间的长短,但是第一个打电话的周林一下子和他女朋友说了20多分钟。我不得已一再暗示他挂线,可是他每次说完“我必须要挂了”,就又接着说:“宝贝别哭,我很快就回去了。”我和萧燕算了算卫星电话打一分钟是6美元,如果照这样打下去,每人打一次花掉凤凰卫视1000元人民币,我们的会计不把我们吃了才怪!于是我们规定每人不得超过5分钟。大家欣然同意,这样排队的时间也不会那么长。 我找不到最佳的词句描述每一名士兵和家人重新联络上时激动的情景,好像他们的身体内突然被注入了新的生命,每个细胞都重新活跃起来。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尽量离开他们一段距离。可是我又不由自主地想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的家人是什么反应。他们告诉我,妻子或女朋友其实什么都没说,只是一直在哭,激动地哭,高兴地哭。有三个人通过电话听到了新生婴儿的哭声,其中的一个人还是第一次做爸爸…… 但是,也有一名士兵打过电话后脸色反而相当的难看。“出了什么事?”我问。 “我岳父说,我老婆跟别人跑了,”他面如死灰,“而且怀了人家的双胞胎。” 我劝他说,现代社会大家受到的诱惑太多,这样的事也难免出现。他说,如果不是自己先常驻德国又被临时调来伊拉克,应该不会出问题,可是现在,夫妻就快3年没见了。“这次回国后,我一定再也不离开美国了。” 因为明天一早就走,我们今晚和官兵们告别。我们把这些天做的新闻录像放给他们看。虽然没有逐句翻译,但是他们看到熟悉的人时还是会心地笑出来:“那么多中国人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样子吗?” 舒尔茨中校晚上特意来饯行,送给我和萧燕一人一枚第三步兵师的徽章作纪念。我向他挤挤眼说,别忘了给老婆打电话报个平安,他搪塞着说,“有缘就过,没缘分也不要勉强。” 我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很盼望回到美国。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