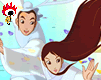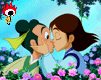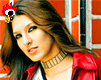| 南方周末:分成两半的广东贵屿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03日11:27 南方周末 | |||||||||
|
有一股比炙烤电路板更难闻的“气味”充斥在贵屿的大街小巷:焦虑、狐疑、仇视。13.5万本地人和数万外地打工者如此生活在一个52平方公里的小镇里。 □本报记者 何海宁
沿着324国道东行,穿过狭长的陈贵公路,载重5吨的大卡车不时蹒跚而过。越过浮草桥,顿时扑面而来一股塑料烧焦的空气,它提醒你:贵屿到了。 在贵屿居住了11年的四川籍三轮摩托车司机“骄傲”地对记者说“欢迎来到著名的垃圾城。” 劳动密集型的电子垃圾拆解业吸引了大批怀着“淘金梦”南下的农民工,他们都有相同的生活哲学:当富裕和健康不能兼得时,健康只能放弃。 在贵屿,有一股比炙烤电路板更难闻的“气味”充斥在大街小巷:焦虑、狐疑、仇视。13.5万本地人和数万外地打工者生活在一个52平方公里的小镇里,却像白天和黑夜一样不能相容。 湖南籍打工者张泊说:“白天外地人不敢惹本地人,晚上本地人不敢惹外地人。” 治安成为贵屿头痛的社会问题,频发的案件让人们变得麻木,甚至涉及性命的恶性刑事案件都很难让这座城镇有所触动。 打工者们来自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地,很多都是不愿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年轻人,贵屿成了他们逃离田埂的跳板。然而,贵屿也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抗拒着他们。 丰作家之死 今年3月4日,20岁的湖南打工者丰作家突然失踪了。 丰作家的舅舅丰兴安和其弟丰作品赶到普宁市南径镇派出所咨询,派出所称下面的治保员没有报案。两天之后,300多名湖南老乡自发组成“搜寻队”,他们开着40多辆三轮车,兵分三路到青洋山村段的练江河堤处寻找。 在河堤处,他们发现了一处现场。带血迹的黑色皮鞋,凌乱的土黄色西裤,烧焦的格子衬衣领子,这些都被确认是丰作家的,此外现场还有一盏煤油灯,十多根血迹斑斑的木棍。 丰作家的家乡在湖南省龙山县贾坝乡。他有个不算奢侈的梦想:赚到钱后,回家办一个卡车执照,跑运输。因为嫌在浙江“赚钱太慢”,他半年前跑到贵屿开始“烧板”(所谓“烧板”属于拆解电子垃圾的工序,就是把电路板搁在煤炉上面炙烤,拔下各种电子元件。贵屿的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此)。 他永远地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与丰作家一起失踪的,还有年龄相仿的同乡谢正友和向永红。而在现场,“搜寻队”发现了一撮带着血淋淋头皮的长头发,谢正友正是留长发的。 这几样血腥的物品勾勒的场景让“搜寻队”触目惊心。他们迅速保护现场,通知当地派出所。 随后公安局警员勘查了现场,将物证取走。 是夜,200多名老乡通宵守候在练江堤边——丰兴安担心尸体沉在河底,被凶手连夜运走。 第二天天亮,800多名老乡主动停工,在附近的山上寻找尸体。后来他们在青洋山村和占陇镇交界的山上发现了3具尸体和两桶盛满汽油的油罐。 法医对尸体解剖后认定,死者头部有致命伤,手上、身上均有棍棒致伤的痕迹,胸部骨折,谢正友面部被烧毁。 丰作家的亲戚发誓要找到杀人凶手。当地传闻这3个“外省仔”是因抢摩托车被打死的。“抢摩托没有死罪。”丰作品说。 丰作品赶过去认尸时,当地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只允许死者亲属进入。 确认死者身份后,警方准备将尸体运走。不料丰兴安他们用三轮车将殡葬车团团围住。他们提出要求:“我们派出代表和南径派出所詹所长谈判,要求尽快立案,告知我们事情真相。” 路边一座寺庙“正德堂”的守庙妇女称“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场面”。 “丰作家从来没有偷过、抢过东西,就算他这次是抢摩托车,也应该把他抓到派出所依法处理啊!”丰作品忧伤地说,“在这里打工一点安全感也没有。” 他的话道出了许多贵屿打工者的顾虑。环境污染没有吓退他们,当地的排外情绪倒让他们忌惮三分。 被吸引,然后被排斥 清晨6点半,贵屿镇北林村综合市场早已人头攒动。猪肉、蔬菜摆在摊位上,等待买主的近百名外地寻工者则站在路边。 不时有本地中年男子骑着摩托车“突突”而至,便有一两名外地人围上去搭腔。 更多的人不愿跟陌生的老板打工,宁可等待打过交道的老板。 这是外地打工者惟一可以和本地人讨价还价的场合。一名骑着黑色“太子”摩托车的男子在他们对面等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一名外地人搭理他。“他太黑,做完后扣工钱,没人愿意跟他干活。”有人私下说。 这无疑是一个典型情景:猜疑,试探,小心翼翼。 本地人和外地人生活在两个迥异的世界里,但是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利益又驱使他们进行不情愿的合作。 在贵屿,当地老板家庭作坊里面必备两样东西:摄像头和看门狗。 这样的场景随街可见:一条邋遢的狗懒洋洋地卧在门口,老板坐在客厅里面边喝工夫茶边监视显示屏上的一举一动。 一个老板解释说,外地人小偷小摸的事情经常发生,没有摄像头和看门狗不行。 贵屿的电子垃圾拆解业分工已经很细。整机拆解后,便有专门的作坊从事“烧板”和电子元件分拣工作。比指甲还小的电子元件很容易随身带走。 但是本地老板对付小偷小摸的外地打工者的办法,让后者回忆起来仍心惊肉跳。 一名30多岁的湖南籍妇女偷了六七个三极管,每个大约4元。被发现后老板把她绑到大街的电线杆上打耳光,并要她赔偿5000元。 从上午10点钟一直到下午4点钟,这名妇女一粒米一口水都没碰,她的丈夫、亲戚远远观望,不敢出面解围。 除了在家庭作坊打工外,很多外地人选择开三轮摩托车载客。 一位三轮摩托车主说,有一次他的车被一辆本地人开的摩托车撞了,对方一下车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打他,最后还要他赔偿。 很多外地三轮摩托车主都碰到过他这样的经历,记者也经历了以下场面。 在贵屿采访时,丰兴安和丰作品开三轮车带记者去察看一处现场,在颠簸的村道上差点和迎面来的一辆自行车相撞。擦肩而过后三轮车熄火。丰兴安回头一看骑车者追了过来,显然是本地人。他粗着嗓子向开车的丰作品大喊:“快!开车!不要停!” 开车后他松了口气:“没有撞到就赶紧跑,停车摆明了就是想挨揍。” 这股抗拒外地人的力量却没有阻止外地打工者的脚步,他们青睐这里的“便利”。 在东莞、深圳打工需要各种证件:身份证、暂住证、未婚证、初中或者高中毕业证,贵屿只需每个月15元的卫生管理费即可,没有办本地老板也不会查。 找工容易也是一大因素。“这里‘烧板’需要很多散工,也不需要很高的技术,每天早上去综合市场一站,就会有人来要工人。”外地打工者说。 尽管如此,许多寄居多年的打工者选择逃离此地。一名30多岁的湖南籍妇女去年冬天去广州了,她表哥为她找了一个小卖铺的生意。她的侄女也准备5月份回家办理各种证件,离开贵屿奔赴深圳。 亲戚老乡们七拼八凑借给她5000多元做生意的本钱。她哥哥说:“我们都替她高兴,这里每个人都在等这样的机会。” 电子垃圾掩藏下的…… 外地打工者把自己称为“过客”,而祖祖辈辈蜗居在此的贵屿人呢? 贵屿镇北林村一名老板并不忌讳谈及环境污染:“这东西或多或少是有点毒,但还不至于马上死人的地步。我们也是讨一碗‘乞丐饭’,谁愿意再回到田里去呢?”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佛山工作,小儿子在广州读大学。他说:“辛辛苦苦把孩子送出去读书就是不要他们回来,要他们回来就不会送他们去读书。” “这行业不是长久之计。”他告诉记者,现在人老了,惟一的指望就是希望在外地的孩子有出息,能把父母接过去养老。 2001年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被国内外媒体曝光之后,贵屿人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楚,又演变为现在的顽固。他们有意回避电子垃圾拆解业可以触摸到的未来,但在内心深处,则对贵屿的家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情绪。 对待家里面的“过客”,贵屿人的感情很微妙。 华美村的一名姓陈的老村民把外地打工者分成三类人:一是老老实实做工的,二是逃避计划生育的,三是人品不好来这里作案的。 “‘烧板’的活儿不好做,没有工作就只能出来偷、抢。”他说,“当然,不可否认大部分的外地人还是勤勤恳恳来找工的。” 贵屿经常发生抢劫三轮摩托车的刑事案件,当地人一般都认为这是由本地人牵头,纠集一帮外地人干的。 治安乱成了贵屿社会一个头痛的话题。一位河南籍出租车司机用手比划了两个方向:“天一黑,有两个路段司机是不会去的,给多少钱都不走。” 今年第一季度贵屿派出所就抓获了60多名犯罪分子。 外来人口管理问题成了村民的一块心病。姓陈的老村民曾经向华美村委会提出一个建议:在荒芜的田地里修建外来工的集体宿舍,用围墙把他们围起来,并规定他们的外出时间,进行集中管理。后来由于资金问题未能进行。 他的话很矛盾:“外来人口搅乱了贵屿社会治安。但是没有外省仔贵屿发展不起来的,歧视外省仔是错的。” 黄文贵去年4月份从湖南老家来到贵屿打工,他觉得“治安乱本地人也有份”。 什么使他们走向另一世界 电子垃圾拆解业落地生根十多年时间,在当地造就了许多一夜暴富的“传说”,本地人津津乐道,周边城镇唏嘘不已。 周边城镇一个村民用夸张的口吻说,他听过最离奇的消息是去年有个贵屿人进了一批20万元的货物,结果拆解后卖了2000万。“什么货,什么渠道,谁也不会告诉你。懂门路的人才能发财。” 暴富的“榜样力量”让贵屿人前赴后继。一位当地知名的文化人感慨:“无论谁当书记,也都没法堵住这条路的。这个行业藏利太丰厚了,没有哪个傻瓜愿意再回去种田。” 贵屿的公路两边密密麻麻挤满了4层或5层高的新楼房,楼房外墙贴满了各式花俏的马赛克。楼房的一层均为3米多高的大仓库,也就是家庭作坊。从事拆解整机、分割电线、分类电子元件之类的一般敞开大门,而对空气产生极大污染的炙烤电路板却是在“黑屋”里进行的。 在四面都没有窗户的仓库里,借着昏暗的灯光,一排人坐在煤炉前“烧板”,设备非常简陋:一把钳子,一些人多了一双手套、一杯饮用水,极少看到有戴口罩的。惟一的通风设备只有一台风扇,夏天煤炉的热浪和炙烤电路板散发出的刺鼻味道足可让人窒息。 外面的路过者只能看到路边一堵墙上的一排风扇,也许还有门边的烧板工抬手擦汗那一瞬间的憔悴。 打工者流传着这样的一条经验:还没有生育的女孩不能“烧板”,否则会影响到孩子。 贵屿的上班时间是早晨7点半到晚上5点半,中午休息1小时,一天工作9个钟头,“烧板”工钱是每天25到28元不等。 有媒体称,贵屿人是在使用19世纪的方法处理21世纪的产品,野蛮的家庭作坊拆解方式为媒体屡次诟病。它不仅给环境造成了“二次污染”,而且给贵屿社会造成了看不见的创伤。 “‘烧板’这样又脏又沉重的劳动当地人是不愿意干的,何况还对身体有害。”一个当地人说,“这在无形之中就把外地打工的看成是低贱的了。” 一个宗族社会的规则 湖南老乡亲切地称他“龚师傅”,本地人不客气地喊他“老头”。 龚师傅教出来的“烧板”徒弟有70多个。老乡要是找不着工了,便跑来找龚师傅:“龚师傅,你帮我留心一下。”本地老板缺人手了,也找上他:“老头,帮我找个工。” 龚师傅1997年来到贵屿,现在北林村开三轮摩托车。他有个“毛病”:喜欢管“闲事”。 一名做工两年的老乡偷了4两价值450元的单电容和38元钱的“镀金维型”,被老板抓住绑在六月天的太阳下,浑身汗“哗哗”地往下流。他的亲戚把龚师傅找来说好话。最后由龚师傅担保,要他在一个星期内筹到5000元作为罚款。 从1998年第一次为老乡求情以来,龚师傅一直在管这些“闲事”。他俨然成为本地老板和外地打工者之间摩擦的调解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热心人”而已。 摆在龚师傅们面前的,是一个由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 贵屿镇共辖28个村(居),自然村里一般均为同姓聚居。一个自然村落就是一排排建得整整齐齐的潮汕民居“下山虎”,宗族关系就像村道一样联系着村与村。 村际械斗是政府头痛的事情。两年前农历二月份北林村和南安村由于“拜老爷”双方争抢道路,大打出手,一名北林人开枪打死了一名南安人,导致近两年来政府出面禁止了这两个村每年的祭拜活动。 贵屿大姓宗族的理事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很广,它负责解决民间事务。“村里同姓之间、不同宗族的人之间有矛盾一般找理事会,很少找政府解决的。出现命案了政府才出面。”华美村大宗理事会陈镇雄会长说,“有一些民事纠纷政府没法解决的,也交给我们办。” 宗族理事会还有另外一个牌子:福利会。它兼顾了社会福利事业。 这样一个习惯了传统宗族关系的社会中,却忽然闯进来一群陌生的外地人。贵屿人无法套用熟悉的宗族规则来解决他们两者的关系,只能束手无策地抗拒着,或者用最原始的办法来处理。 令龚师傅欣慰的是,在贵屿7年来,他总算有了一个当地的“朋友”,那是1997年认识的一位老板,对外地人比较友善。今年年初,由于撞车要赔钱,龚师傅开口向他借500元。 “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现在我还有200没有还呢。”龚师傅微微一笑,显得很有成就感。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