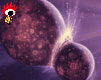| 红色档案———地下党在天津之三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2日23:54 城市快报 | |||||||||
|
“我和老伴儿 都是‘抗联’成员” 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不信世有三生缘,只因道同才并肩。回首风雨来时路,甘苦已过五十年。”望着这首十年前写的《金婚志感》,楚云、辛冬这两位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革命夫妻心潮起伏。当年只是20岁出头的天津“抗联”成员,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当两位老人回忆起天津“抗联”战斗的历程时,青春的活力再次从心底迸发。 接受新思想 发起救国会 “我是‘青救会’发起人之一” “我原名叫李家辉,参加革命后化名为楚云,其间还用过李建平、何戈书等化名。解放后,因为知道‘楚云’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就一直沿用下来。我的老伴儿辛冬,原名叫陈子政,辛冬也是她参加革命时用的化名。” 在革命老人楚云的家中,老人开门见山,首先将两人的“秘密”和盘托出。“抗战初期,我在天津美国教会办的究真中学上初中,同王洋、康力是同班同学,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思想使我们彼此接近,常在一起看些进步书刊,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和柳湜主编的《读书生活》、《生活杂志》,翻译的《哲学大纲》等。王洋、康力、高飞和我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平凡读书会’,互相传阅一些进步书刊,经常在一起讨论抗日形势。” “那时,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姓赵的,是晋察冀边区曲阳县人,曾担任过区‘青救会’主任,后因个人婚姻问题,离开老家到天津读书,常向我们谈及根据地的情况,教我们唱革命歌曲,使我们产生向往解放区、根据地的思想。到1941年,我们已感到搞读书会、光看书发议论是不够的,要革命必须有党的领导,有进步的行动。于是,我提出回老家———河北省束鹿县找党组织(属冀中根据地六分区)。” “我在家乡曾向专区检查文教工作的王雅波同志提出,天津有几位同学要到根据地的要求,但没有得到解决,仅我个人被留在老家当了半年多小学教员。敌人‘五一大扫荡’后,我与地区党组织失去联系,1942年7月,我设法回到天津。回到天津我才知道,由于很久没有得到我的消息,康力、王洋等7个人在1942年春天与冀中八分区敌工科的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分3批去到了八分区。在4月份回到天津,‘五一大扫荡’后,康力等回津的几个人也与根据地失去了联系。就在这个时候我从老家回到了天津。当时,康力、王洋和我便决定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名称就根据我在冀中知道的‘青救会’起名,叫‘天津抗日青年救国会’。我们是发起人,也是负责人。最早的成员有苏更、辛冬、何凤淑、张继兰、李新开、田英等人。” 积极寻找党 暗地蓄力量 “我们在高中秘密发展会员” 1942年暑假后,楚云、康力和王洋三人又分别考入木斋中学和广东中学的高中。他们一边积极寻找与党联络的线索,一边暗地积蓄力量,广交朋友。 “我们青救会员在同学、同事、朋友、邻居中物色培养对象,进行宣传教育,够条件者便吸收为会员。田英首先被吸收入会,接着王洋发展郎维华入会。以后田英介绍张继兰(女,张佩兰)为会员。张继兰又介绍其妹朱琪(张佩英)入会。郎维华当时是广东中学学生,同时在维斯理堂夜校兼任校长。郎维华被发展为青救会会员后,工作很活跃,以维斯理堂夜校为阵地组织了几个秘密读书会,并从中发展刘诚、张中育、胡平(马燕歧)为青救会员,建立了第一个青救会小组。”到1943年5月,苏更(女,张奎雯)、李兴凯、何鸿书、辛冬、石中(女,钱秀如)等又相继入会。青救会会员有十五六人,分两个小组,并有若干单线联系会员。 1943年4月间,康力到私立特一中学学生宿舍看望一个老同学,无意中在一张床位的被褥下发现了几本抗战前出版的进步书刊。他问:“这是谁的床位?”老同学回答是高三同学郭韦(现名雷文)的,还说郭韦和好几个同学经常看这类书刊,还嘀嘀咕咕地谈论些什么。楚老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康力记在心里,回来与我、王洋研究,在5月,向郭韦寄发题为《‘五四’纪念日告天津全体青年书》的传单。以后又和郭韦直接建立了联系。通过郭韦了解到这里有七八个青年组成的秘密读书会。6月间,康力介绍郭韦入会,接着郭韦又将读书会成员杨畅言(杨昌炎)、冯森(吕塘)、左建(李培昌)、邓迈、林青(张先捷)等6人发展为会员,建立了另一个青救会小组。” 据楚云老人回忆,青救会期间,共印发抗日传单两次:1942年10月,《给伪军组织同胞的一封信》和《胜利在望,同胞们团结向前!》两种,共印150份;1943年5月4日,《“五四”纪念日告天津全体青年书》,印500份。传单是由青救会负责人起草,组织会员在夜间刻印的。印刷时带上手套,以防留下指纹。署名“八路军冀中军区”或不署名。通过伪装邮寄、夜间张贴或塞门缝等形式向外散发。当时会员们认为,印发抗日传单是革命的实际行动,既宣传了群众,又打击了敌人,也考验锻炼了自己。 联络解放区 改组“青救会” “我们都成为‘抗联’成员了” 由于长期与解放区失掉联系,得不到党的领导,年轻的“青救会”成员们始终无法系统开展活动。1942年冬,快过春节时,楚云和康力、王洋、田英4人在张继兰家一起研究,最后决定由田英回解放区去与领导取得联系。 苍天不负有心人,1943年初,田英在根据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解放区的一些小册子、传单由田英送到天津,“青救会”油印后再散发。“青救会”与抗日根据地党组织恢复联系后,从根据地带来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的著作和其他时事政策文件,“青救会”便有计划地组织全体会员认真学习了这些著作和文件。楚云曾以何戈夫为笔名,写了一本介绍冀中抗日根据地民主生活和军民关系小册子———《另一个国土》,作为学习参考材料,在会员中秘密传阅。因为只有一份手抄本,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同年夏秋,在十分区司令部驻扎的苇塘里,地委书记兼十分区政委旷伏兆同志接见了康力,康力汇报了“青救会”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听了汇报,旷伏兆同志便决定让康力和田英写一份报告,由地委转到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城工部回复:确有这些人被派到天津,指示暂由十分区领导,待情况好转后再接康、田二人去晋察冀边区。旷伏兆同志决定把“青救会”改为“天津市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其出发点就是不限于青年,要扩大活动范围。 “抗联”散发传单比较活跃(1944年下半年这种做法不提倡了)。大家想出了不少办法:邮寄、塞门缝、从商场顶上往下散。在列车上散发传单,震动比较大。另一次是在日伪举办的华北运动会上散发传单。 “当时有4个同志(左建、邓迈、冯文慈、刘铁锌)化装成运动员,混入运动员住的国民饭店,在走廊过道里,挨户叫门,门一开就给一份,封皮上印的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宪兵队给某省运动员’,里面是八路军传单。当他们拆看时,我们的人早已不见了。第二天,运动会停止,宪兵队包围了饭店,运动员挨个受审。后来这种刺激敌人的做法受到刘仁同志的批评。”楚云告诉记者,“那时热情很高,就是斗争的方式方法还不能准确把握。” 渴望加入党 长途夜行军 “我们每夜行军80里” 楚云说:“到1944年,‘抗联’成员已发展到30多人,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红色团体。‘抗联’的成员团结了周围的群众,在组织分布上,已突破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圈子,由学校发展到工厂。但我们只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还没有一个人入党,因此,我们对于早日入党的渴望更加迫切。” “这年夏天,担任联络工作的田英奉命回津,带我和康力、刘克、辛冬等4人到十分区。出发时,我们化装成普通学生,从天津坐火车到静海,从静海步行到王口镇。我们四人装做互不认识,一路拉开距离向前行进。过了王口岗楼,前方就是游击区,就比较安全了。打头阵的我和康力在岗楼前的路上买了几个甜瓜,一边吃一边大摇大摆地走过岗楼,把守的伪军也没盘问,顺利地穿镇而过。到了文安洼水边,田英雇了一条小船在那等着,等四个人到齐后,撑船离岸。到达分区司令部后,中央分局来电让派有经验的同志护送我们到阜平,另有任务。十分区司令部派特务连的陈排长护送我们,当时环境很残酷,不能直接走,在白洋淀转了个弓背,最后过铁路到了晋察冀城工部所在地。在部队的夜行军中,每天夜里要走80多里路,把我们这些没有行军经历的新人累得够戗。在阜平,我们向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同志汇报了‘抗联’的工作之后,便留在城工部进行学习,除了党的一般文件刊物外,还学习了‘党的城市工作方针’。这时,佘涤清介绍我与康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辛冬与刘克也先后入党。” 刘仁、佘涤清研究以后指示:成立“抗联”党总支,由楚云担任总支书记,康力担任“抗联”主任;今后的活动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必须要贯彻城市工作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刘仁还特意指示停止散发传单等暴露自己的做法。 巾帼不让须眉——— “高中时我就打入纱厂” “打入工厂、企业,大力做好工人的工作是回津前党交给的任务,在发展党员之外,我们就开始研究打入工厂的计划。由于当时工厂待遇差,很少有人愿意在工厂上班,所以我很容易就和另一位女同学考入了双喜纱厂(解放后为棉纺五厂)。” 当年的辛冬还是木斋中学的学生。“由于家人已知我从事了地下工作,也就默许了我向学校请病假,我化名陈小兰在9月下旬到双喜细纱车间做试验工。同时去的还有朱琪,她当时是工商大学(工商学院的前身)的学生,父亲是位工程师,这样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公开去工厂做工根本是不可能的。为打入工厂,她以反对家庭给介绍对象为名不辞而别,秘密地住到我家,化名张露华,装作不识字到双喜布厂做了织布工。我和朱琪同住在工厂的工房里,由于我俩原来的社会身份和打入工厂后的工人装束,只能每周一趁天不亮溜出家门,周末等天黑后溜回来,以免引起邻居的疑问。” “当时工厂是两班制,每个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进出厂还要搜身,挨打受骂、女工受凌辱的事经常发生。但一个月的工资除发30斤带着糠的玉米面或山芋干外,只发给几元钱,年终才加发几斤面粉和一点布,一个工人全月收入满足不了自身的温饱。这些情况也是我到了工厂后才知道的,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也很难体会到工人的艰辛。” 辛冬回忆说:“1945年3月,天津抗联党总支根据中央分局城工部长刘仁同志的指示‘不要把打入工厂工作搞得太勉强,学校工作、敌伪工作都很重要’的精神,决定我和朱琪撤离双喜纱厂,仍到学校去做学生工作。厂方规定不许工人辞工,因此要走只能偷偷走,不能公开拿走自己的铺盖。我俩要离厂铺盖怎么拿走呢?孙少华的父亲装作拿自己的铺盖去典当,孙大嫂拿着我们的一些零碎用具,对外人说是送我回娘家,终于帮助我俩混过了门卫,安全地撤出工厂。” 相关专题: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