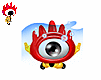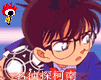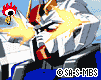| 追问郎咸平 你要为民企指明什么道路(2)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2日10:14 瞭望东方周刊 | |||||||||
|
小时候,郎咸平念书不用功,但打拳却极用功 1949年,国民党第26军的一名上尉军官,带着自己的妻子、一箱青岛啤酒及身上仅
7年之后的1956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活不过12岁。不祥预言的阴影,时时笼罩在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的头顶──扁桃体发炎、一周三次的抗生素注射、吃各种药片,便是郎咸平对幼时的主要记忆。 2004年夏末,盛年郎咸平回忆起童年经历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那时候反正各个方面都不正常,还尿床,一直尿到12岁。”接着他又用非常快活的语调说,“但是等到过了12岁,一切开始变得正常了,再也不尿床了。” “满分100分,我只考了5分” 迈过了12岁这个坎,郎咸平的少年时代开始了。 我们在水的这一边,以回望的姿态看郎咸平的少年时光,才蓦然发现,在水的那一边,成长的经历竟然如此熟悉,原来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啊:父母忙着工作,年长的哥哥姐姐有他们自己的快乐,孤独的少年守着自己重重的心事。 “我爸爸经常在部队里,他脾气极坏, 我和他很难相处。妈妈很疼我,但她在补习班教书非常忙,没有时间陪我。我跟姐姐处得也很糟糕:我晚上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姐姐一回来,一定会把电视抢过去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只要我有意见,她一定会和我大打一架。我哥跟我关系不错,他常帮我,他说我这人小时候怪里怪气的,我想从小孤独应该是主因。” 成名后的郎咸平多次谈到,自己不是一个精英,从小就不是。当以一个成年人身份特别是有所建树的学者的身份提起少年求学往事的时候,郎咸平的语气是轻快的,甚至略带戏谑。你丝毫不会感到一个10多岁的少年作为一名差等生的无助心境。 “我在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差,而且似乎什么都不如人家,包括体育、艺术、学习成绩等。我对自己完全不认可,由于属于坏学生的缘故,我心中充满了自卑感,而且对未来也不敢有什么想法。” 郎咸平回忆的语调里,有一丝惆怅。 郎咸平迄今还记得爸爸在他小学5年级时,拿了一份算术模拟考试的试卷给他做练习,满分是100分,郎咸平辛苦做完后,只得了5分。 幸运的是,那一年台湾开始实行小学直升初中,不用考试。郎咸平成为台湾第一届小学直升初中的学生,进入大同中学。 但身为差等生的痛苦随之延续到中学。初三分班的时候,郎咸平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班,是给那些没有出息的差生开的班,学生基本上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份子,很多人家里很穷。放牛班很可怕,有很多流氓和“太保”。因此郎咸平说自己从小就对台湾的太保、流氓和黑道非常熟悉,而且在学校几乎是天天打架。 “我基本上都是被打。念到初三的时候我感觉非常不愉快,很讨厌上学。那时真不想念书,想去念陆军官校。”郎咸平回忆说。初中毕业后郎咸平也去考过陆军官校预备班(陆军幼校),想出来当军人,但由于近视缘故,体检没通过。 向左转木工,向右转学术 郎咸平开始学木工始于放牛班。“当时的理想就是准备出来先做木工学徒,再开个木工厂。”郎咸平说。 今天看来,在成长为一名经济学家的路上,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一直在牵引着郎咸平。而在那个时候,他的脚正踏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里树着一块路标:左转是木工,右转是经济学家。而那个路标他并不能看到。 现实的问题是,郎咸平当时的成绩实在是太差了。升高中考试前3个月举行模拟考,在1000多名考生中,他的成绩排在800多名。这种成绩就算考军校恐怕也不行。虽然做好了当木工的准备,但是在潜意识深处,郎咸平还是想升学的。 郎咸平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母亲,“妈妈学的是化工,所以在学校教化学。她在台湾是化学界的名师,所以忙着到各地补习班教书。一个星期最多教到76个小时的课,为了养家,非常辛苦。对我妈妈支撑这个家,我们兄弟姊妹都非常感激”,“妈妈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我妈妈哭过”。 听郎咸平回忆母亲,有理由相信,正是母亲的德行潜移默化影响了少年的郎咸平,老师的孩子爱读书,是熏陶,也是宿命。 就这样,考前3个月,郎咸平感到了压力,就想念书了。但是念课本肯定来不及,就只好念“考前30分”,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临时抱佛脚”用的一种复习资料。考前两个月的第二次模拟考,郎咸平考了500多名,考前1个月的第三次模拟考,居然考到了300多名。等他参加中考时,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愿成功中学。他们整个学校考上高中的总共不到300人,而郎咸平能够在1000多人中考上这个学校已经很不容易了。 回忆起那次决定命运的考试,郎咸平认为是自己买的那种版本的“考前30分”帮了大忙。 “这真是造化捉弄人。我想如果当时买别的版本‘考前30分’,那不就完了吗,那真的只有当木工了。”郎咸平笑着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西门町之虎” 由于妈妈在建国中学教书,因此根据学校规定,郎咸平可以“跳”到建国中学──那也是郎咸平报考的第一志愿──借读。但是他的成绩并没有随之跳起来。 “在初中时,我个子小,常常被同学修理,因此一上高中就赶紧学打拳──螳螂拳,准备和同学打架用。我们老师卫笑堂是山东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功夫极高。” 郎咸平念书不用功,但打拳却极用功。他自诩当时功夫很高,班上的混混都不敢惹他。那可能是少年时代郎咸平最为得意的一段记忆了。 “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时,我和另一位同门师兄弟王国光到台北闹市区西门町逛街。当地几个地头蛇看我们不顺眼,上来找麻烦。我们就和他们打了起来,结果一下子冲出来好一批他们的弟兄。当时真可以说是一场血战。” 郎咸平说,“我的螳螂拳这时发挥了威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有上百人围观,我好不得意。但我的左手腕也被打成重伤,养了两个月才好。同学们也从不同管道得知了这个消息,最后大家干脆开玩笑叫我‘西门町之虎’。” 中学毕业后,郎咸平顺利考入了台中的东海大学读经济。 改变人生的作弊 郎咸平走上钻研学问的道路,和大学时的一段境遇有关。 据郎咸平回忆,当时东海大学经济系的微积分课程要求很严。该门课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 而且一学期得考4次月考。郎咸平第一次只考了60分,第二次月考时就想走快捷方式,作弊抄一抄同学的试卷,结果被老师抓到了,得了零分。 “第一次60分,第二次零分,平均起来是30分。这样的话,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会被淘汰。当时,我都想干脆放弃算了,因为像我这样的水平怎么能考100分呢?”郎咸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然而纵览郎咸平成长的道路,人们发现,就是在这时,他的心路历程开始转变。 郎咸平继续回忆:“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忽然有一种想法,决定好好地念。我每天很用功地念到半夜二三点,当时就感觉好像哪根筋不对劲,我就不信考不过。结果一个月下来,忽然发现,我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忽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很多解不开的题一旦解开了很有成就感。” 第三次和第四次两次月考考下来,平均分竟达99分。郎咸平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笨,这是他这平生第一次有这种“聪明的感觉”。结果一通百通,其他科目例如经济学也考得很好,都是90分以上。 “从那时起,我慢慢开始对做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以后我在学问方面的涉猎极广,博览群书,可以说国内外名著样样涉猎,尤其是历史、政治学、军事学和哲学四大科目是我有系统学习的主体。我似乎从书海中寻回了我的灵魂。” 郎咸平说,他每次回台中,都要看望王文清老师,感谢他抓作弊抓得好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求职未遂,回锅当记者 如今的郎咸平已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据他身边的人说,朗教授是很乐于跟记者打交道的。 聆听郎咸平的经历,你也会发现,早在读硕士期间,他便与媒体结下了渊缘。 大学毕业后,郎咸平顺利地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那是台湾最好的经济学家摇篮,台湾财经界人物大部分来自那里。直到那时候,我爸爸才深深以我为荣,到处吹嘘我的台大学历。我爸爸在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生的。我这个爸爸的反应也稍微慢了一点,10年以后才搞清楚儿子初中在干什么。”郎咸平说。 研究所第二年,郎咸平的同学郑家钟在《工商时报》做记者,他把郎咸平也介绍到了报社当金融记者。 “当记者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年轻的记者,才23岁,接触到的都是部长级以上的人物。我是金融记者,很早就看到官场上的是是非非。很有意思,研究所出来后,因为找不到事的缘故,我又回锅当记者去了,整天跑新闻。” 郎咸平说,在台湾和大陆类似,记者不被年轻人当成一个终身的职业,通常做个两三年就会转业。他前前后后做了两年记者。 之后,郎咸平开始考虑跳槽转业,但是台湾职场似乎跟他较上了劲,他始终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我只有考虑出国留学了。”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跑新闻实在太忙,也没时间念托福和GRE,最后郎咸平的托福考了550分,GRE考了1640分,是两个相当差的分数。他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作了回应,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郎咸平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得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 这所惟一接受郎咸平的学校,竟然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不知道是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沃顿──“烂校”──去还是不去?还有两万美金的学费。如果说初中毕业时弃木工而选择升学,是潜意识中受母亲影响的话,此次郎咸平最终成行,完全是母亲的决定。 “我的母亲对儿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妈妈把它卖了两万美金,准备给我出国交学费用。” 两年半攻读博士学位 郎咸平在沃顿申请了商业经济系。在东海和台大念书时,他总觉得自己的水平不错,但进入真正的学术殿堂后,郎咸平才发现课程太难,根本听不懂。 特别是跟经济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郎咸平现在回忆起来,还直感叹:“那就别提有多难了。”至于第一次接触博弈论,“我简直一点概念也没有”。 两门课考下来,郎咸平的成绩都是C。到最后,因为他的操行很好,上课从来不迟到、不早退,助教帮了个大忙,才帮着把C改了个B-,这才得以继续留下来。 那次考试之后,一切似乎变得光明起来,最后,郎咸平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考核,一直到了这个时候,郎咸平才认为自己念书开窍了。 回忆那段狼狈的日子,郎咸平说:“那时我就不敢交学费,学费一直拖到最后才交。我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干脆拿钱回台湾去算了,也不用浪费学费了。所以我从9月份拖到12月份才交学费。” 1985年,郎咸平在沃顿开始写博士论文。起初,因为没有胆量做公司财务的课题,他只想做投资学方面的论文。在他看来,自己是不可能适合做那种软科学的,也不可能打进那个小圈圈。 当时沃顿的一位大牌教授艾尔温·弗伦德需要一个勤劳的打杂工,碰巧郎咸平曾义务帮他搜集过一些资料,因此弗伦德很希望郎咸平继续帮忙,就收下了他,并要求他做公司财务的实证研究。这便是郎咸平在公司治理研究方面迈出的第一步。 谈到自己的博士学位,郎咸平既得意,又不失谦虚:“我总共花了两年半时间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这个速度在沃顿创校100余年的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了。虽然我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但我对这个领域还是相当的陌生。” “我情愿往国内走” 博士毕业后,郎咸平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执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其间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然而,异国平静的学术生涯,在郎咸平看来又有一丝沉闷。在谈到那段日子的时候,他说:“你到了快40岁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什么成就感了,因为在那边太专业。你发现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有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看到播出中国,心里面就觉得有点酸酸的,所以一有机会的话就会想到回这里。” 1994年,郎咸平抵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从此,郎咸平由一名亚洲与中国经济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2000年底,郎咸平在香港立法局与众投资银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演绎了一场“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的壮举,至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依稀有少年时代“西门町之虎”的风采。 2001年底,郎咸平进入内地证券市场。他提出:“应当审慎地提出一个‘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东的规则。” 之后,郎咸平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在媒体间掀起一场“郎旋风”。褒之曰:体现了一位经济学家的深厚学术功底和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侠义胸襟。贬之曰:不谙中国国情的“民企杀手”,只为出风头的狂人。 郎咸平说:“我情愿往国内走,我不愿往美国走,因为在这边你会受到重视,你的意见受到重视,你能够为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做一些事情,虽然我只做了个开头,提出了一些观念,但是还是很重要。” “追求卓越是我留在中国的最大动机,真是的,这个‘追求卓越’真的是让我非常感慨,真的非常感慨!”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一年,2004年,郎咸平48岁,身份是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长江商学院合聘教授。《瞭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范无盐/北京报道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