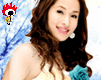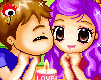| 法学专家激辩“国资流失”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16日19:31 南方周末 | |||||||||
|
罗培新 整理 编者按:近日,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郎咸平,接连向包括海尔、TCL、格林柯尔等国内知名企业发难,指责其在“国退民进”的企业改制中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并称企业家“就在想怎样圈国家的钱”,因而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此番言论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郎教授的观点是否有道理?是否正如他所言,要遏制国资流失,就必须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在保护国资方面,法律制度究竟存在什么缺陷?我们需要怎样的制度安排,以遏制国资流失?针对这些问题,本报约请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研究中心牵头,由其组织6位法学专家,进行一番研讨与对话。 对话参与人: 顾功耘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副会长 胡鸿高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市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吴弘华 东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会长 任荣明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市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干事 韩长印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理事 罗培新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 郎咸平的发难是否妥当 顾功耘:我很敬佩郎先生的批评勇气,也很敬佩他对维护国资的热情和责任感。但是,郎先生提出的有关观点,我却不敢苟同。 一说:企业家“就在想怎样圈国家的钱”。这种说法很不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从计划经济体制直至今日体制转轨,大多数企业家无论是工资奖金,还是福利待遇,虽有逐渐增长和改善,但与他们的贡献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正因为如此,国企的激励机制成为长期以来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说:看重产权改革是一个错误。这种说法是对国企改革实践的无知。我们的改革,经历了25个年头。总的说是,什么时候离开了产权谈改革,我们就寸步难行;什么时候捡起了产权谈改革,我们就有所进步。大家想,国企从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到两权分离,再到法人财产权,国资从全面覆盖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哪一点进步不与产权相关?! 我认为,产权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我们今天提“法人财产权”,其实还没有真正确立企业法人的独立地位。法人有财产权,为什么不提有所有权?这里面,仍然是在强调国家对企业投资有绝对支配的权力。公司法第4条的内容就是明证。所以,看重产权改革,并不是错误。 任荣明:我认为,郎咸平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发表个人见解,只要这种见解不是无中生有、凭空臆造,就无可非议。郎咸平的言语有些过激或尖锐,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前,我国许多重大事情包括国企改革,尚处在探索之中。让少数官员、少数学者决定我国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容易造成失误。学术需要民主,学术需要活跃。我们对不同的声音,不应苛求它表达的方式以及措词是否严谨。 郎咸平确实不客气地指责了某些国企、上市公司。但国企与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公众企业,公众企业理应受到社会的关注。如果不同意郎先生的观点,可以反驳。社会公众也很希望听到这些老总们的见解。 罗培新:的确,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上市公司的小股东保护一直很成问题,即使是透明度要求较高的上市公司,其信息披露也往往报喜不报忧,或者是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一般投资者根本无法看透的“报表重组”等手法粉饰太平。郎教授对一些公司的财务数据层层剥笋,化繁为简,使这些公司的真实面目显露出来。“郎监管”至少增大了真实信息的供应量,而这正是社会所需要的。 但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了,与郎教授严谨的财务分析方法极不相称的是,他的推论逻辑极不严密,对法律更是缺乏必要的了解。刚才任荣明教授讲到,我们不应苛求郎教授的表述方式及措词是否严谨。恰恰相反,我认为,对于已经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并且以学术操守自重的郎教授而言,坚持严谨的学术标准,是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否则将误导民众,严重的还会破坏政府决策。 很可惜,郎教授这位公众知识分子,在应对媒体时有问必答,他的知识似乎没有边界,狂放到了极点,什么企业家“就在想怎样圈国家的钱”、高管的信托责任“是道义上的,不是制度上的,因为制度没有办法规范”、由于我国“缺少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国企的保姆反而成为了主人”……且不说国资流失这么个大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靠强化高管的信托责任来解决,至少郎教授不应当忽略我国公司法还是有相当多的法条要求高管必须忠实于企业的,这种责任也绝不是什么道义责任,而是法律义务。 吴弘:郎咸平与张维迎等的争论,涉及如何看待国有资产流失与国企改革的关系问题。撇开一些具体个案中的是非,大家都承认改制中存在国资流失的客观现象。但一方指责一些企业家在“国退民进”中席卷国家财富,从而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国企产权改革;而另一方却认为拖延国企改革,结果只会使国资缩水越来越大,强调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只有分给私人经营者,才能有积极性。双方有些观点都过于情绪化、绝对化。 遏制国资流失,必须叫停产权改革? 顾功耘:我想,郎先生所指认的国资流失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现象应当引起全社会尤其是监管部门的重视。国资是公共财产,不能因为我们过去忽略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今天就可以忽略对公共财产的保护。 国企改革很复杂。在卖国企问题上还存在着另一种现象,或许是郎咸平不够清楚的。这种现象可称为“惜售现象”。有的人总想使国企卖个好价钱,这个动机不错,但是他们不了解国企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是有区别的,单项实物的价值与企业整体的价值也是有区别的,他们更不了解国企评估价与市场价仍然是不能等同的。一个国企,尽管它有数亿、数千万元的实物资产,但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产品没有市场,你要卖出好价钱是不现实的。如果考虑企业冗员、缺乏技术、做账不实等因素,要卖好价钱几近荒唐。如果国企都像郎先生想象的那样好,那样值钱,我们的改革早就该完成了。 任荣明:郎咸平所说的值得深思。作为国企的老总,为何一人可以持有企业5%—10%以上的股份,为何管理人员可以持有企业25%以上的股份,为何国企资产增值的大头归管理层,为何只要国企一上市,这些老总们就可以一夜暴富,甚至再经过几次改革可以达到巨富?这种管理者收购的股权分配比例是由谁来决定的?有没有法律依据?国企资产为国家所有,同时这些国企获取上市溢价发行这一稀缺资源也是国家给予的。这些国企老总实际掌握了这些稀缺资源就可以暴富与巨富,这种暴富与巨富是否合情、合理、合法?这种暴富与巨富的财产中有没有国有资产或“职务资产”的成分?本人在此借用专利制度中的“职务发明”概念。这些问题很值得大家探讨。 胡鸿高:我不赞成郎氏关于“国企比民企好,不需要再改革和改制”的观点,因为中国及国际上国有化浪潮的失败与终结,已经作出了很好的注脚。但是,我认为郎氏提出的“在国资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过程中,国家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国资、国企买卖中,卖的是谁的资产?谁能代表国家出卖这些资产?价格应该怎么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法制建设还有很大的缺失。 如果制度建设不到位,必然使中国国有资产在一片“防止国资流失”的口号声中流失殆尽。郎氏提出的问题不从制度上解决,那么,就有可能沿着这一条可怕的道路走下去:什么时候国资折腾完了,什么时候国企改革也就结束了。 罗培新:我注意到郎教授之所以主张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其中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国企的所有者是国家,所有者并没有缺位,关键的问题是选不好“管家”。我觉得,如果在产权不变的前提下,能够选好、监督好管家,倒也不错。但现在的问题是,让国企高管为毫不相干的“全民”服务,显然缺乏道德上的吸引力,而且事实表明,再没有比切切实实的所有者而不是虚幻的全民所有的监督更有效的约束了。所以,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停止产权改革,而关键是要作出一套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明确高管、职工等主体在产权变革中应分得多少利益。 哪些原因造成国资流失 任荣明: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解决好国企管理层的激励机制问题,国企老总干好的与干坏的收入差距不大。这种机制不解决,国企肯定搞不好。国企老总的贡献与国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利益机制如何制衡?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学术界,认识上都比较模糊。因此,不可能制定出一套合理有效的制度来规范。在此情况下,国企老总们必然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为何国企在制定改制方案时,大多采取MBO(注:管理层收购)方式,并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将企业包装上市的根源所在。 韩长印:另外,我国的财务法律制度也很成问题。一些实施MBO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调剂或隐藏利润的办法扩大账面亏损,然后利用账面亏损获得较低的收购价格,甚至逼迫地方政府低价转让股份给管理层控股的公司,如果地方政府不接受,则继续操纵利润,扩大账面亏损,直至上市公司被ST、PT后,再以更低的价格收购。 国内首家提出通过转让国有股实现管理层收购的“宇通客车”,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起因就是公司虚报资产和负债。处罚书指出,“宇通客车”在编制1999年年报时,采用编造虚假记账凭证等手法,共计虚减资产、负债各13500万元。在此次虚减资产的一年后实施管理层收购,其用心不言而喻。 罗培新:国资流失,还与我国目前薄弱的司法体系密切相关。现在大批地方国企搞破产逃债,形成银行呆坏账,而当地法院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这是因为“破”掉的是国有银行的资产,而地方企业则可以逃掉银行债务,这显然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人、财、物都由地方供给的法院,司法的“地方本位”自然难以避免。同样地,在国企高管侵吞国资而酿成诉讼时,司法往往被地方上的人情或者利益所俘获,独立性很难得到保障。 防范国资流失的法律处方 顾功耘:如何做到既能防止国资流失,又能不“惜售”,我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要选择合适的国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在进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依靠监管机构的监管,保障改革的顺利展开。 现在应从三个层面加紧立法,一是国有资产监管法,二是国有资本运营法,三是国有企业改革法。监管法解决体制、职责问题,运营法解决国有资产转为国有资本经营运作问题,改革法解决国企的内部体制和治理问题。我希望高层领导把注意力尽快转移到相关的法制建设中来,以法律引导、规范和促进改革。 吴弘:在改革不断市场化、规范化的今天,国企与国资改革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完善相应的法制才是惟一出路。应该看到,由于立法相对滞后、执法监管不严,总有一些预想不到的侵害国资的行为发生,这需要法制及时应对。 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信息的公开。信息公开是现代市场的基本要求,也是医治市场痼疾的一剂良药。国企与国资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透明度不够。国资的转移或是暗箱操作,或是故布迷云。国资改革万众瞩目,不应该也不必要秘密进行。 任荣明:我认为,在目前我们尚未找到一套有效的国企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先不必急于否定MBO的做法。不管怎么说,MBO也是一种激励方式。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找到有效的方法去修正弊端,或寻找一种更好的激励机制来替代目前国企MBO的做法。国企的资产为全民所有,但必须授权或者信托一部分人经营。任何偏离兼顾经营者、企业、国家三者利益的改革都无法取得成功,更不会为社会所认可。 此外,我国应当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对国企老总的能力与贡献形成科学的市场评价体系,将国企老总的收益与其贡献挂钩,而不是与所谓的资本运作挂钩。 胡鸿高:我国的大部分法律,大都是从“消防”考虑,急就而成的,往往带有“救火性”和局限性,因而也就有片面性。郎氏的“炮轰”,迫使我们去考虑“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国企”,以及如何造就平等机会、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等问题。另外,信托、租赁等西方行之有效的国企运营办法,在中国大环境未改变的情况下引进,并希望其发挥作用,恐怕不能太乐观。因为一是中国自古以来“解构”能力很强,二是租赁承包已被历史证明收效甚微,三是我国制度文明建设尚未取得足可依赖的成就。 韩长印:我认为,针对目前问题最多的MBO,应当强制性地引入信息披露规定,要求转让方将公告及其他相关信息,委托产权交易机构刊登于相关的报刊和网站上,并广泛征集受让方。“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很多问题,都会在阳光下的竞争中消失。 罗培新:我们常说,经济体制需要转轨,公道良心却不能脱轨,在这方面,法律的作用必不可少。但常识告诉我们,不能对转轨时期的法律期望过高。法律的确定性或者说刚性,往往是和社会变革时期对规则的弹性需求相矛盾的。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曾说过,如果在社会转轨时期,一切规则都用法律的形式来固定,那必然会增大改革的成本。在国资这一块,拟议中的《国有资产法》历经十年风雨仍难以出台,就是这个原因。 2003年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对许多问题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尽管如此,这部暂行条例也还面临着市场的重重质疑。但我认为,将国资流失一味归咎于国资部门失察,或者一味归咎于法律的粗疏,都有失公允。国资流失,在目前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下,很难完全避免,这里面有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分权问题,如地方国企和国有银行的利益博弈,有司法地方化的问题,也有市场化改革后国资隐性流失显性化的问题,许多问题法律无能为力。 目前法律能够做却做得不好的地方是,如何将地下交易推到阳光之下,比如说目前产权交易的信息披露和拍卖竞价规则很不完善。另外,在设计规则时要多注意避免产生道德风险。譬如说,东欧国家在搞MBO的时候,规定企业要连续三年盈利,企业的高管才能将它买入。换句话说,就是要卖企业,也要卖给有能力把它搞好的人。而不像在中国,许多国企的高管故意把企业搞烂,然后MBO,压价将其买入,产权变更后,马上乌鸡变凤凰。设计法律规则时,要对人性做最坏的设计,才能避免道德风险,并取得最好的效果。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