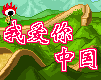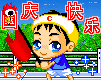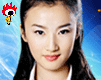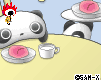2003年05月19日:SARS中国初愈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2日20:53 中国《新闻周刊》 |
|
5月是关键的一月。 忐忑着度过了“缩水”的五一假期,北京人的心情随着疫情曲线的一路走低而渐渐走高:每日新增病例数自5月2日跌下100大关后,至5月9日更跌下50关口。而官方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谨慎的乐观:疫情正呈波动式下降趋势。 北京人开始试探着从SARS的阴影下走进初夏明媚的阳光,街上行人开始增多,一度空旷的大街上汽车重新排上队,后海边的酒吧里又有了喧闹,饭馆准备重新开业,多数人摘下了口罩——这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指标,表明这座城市已走出了恐慌。 北京的向好也带动了全国疫情“波动式下降”,至5月13日,仍有6个省区保持着“金刚不坏之身”,而福建、湖南、山东、广西等地均有10天以上未新增确诊病例。而一度令人担忧的上海,在严密的防范下并未失守,更是鼓舞了全国的士气。 与此同时,好消息还不断从周边传来:越南成为第一个完全控制住SARS的国家,多伦多也宣称“完全控制”,新加坡和香港的状况也一路走好,并且有望促成WHO取消旅游警告。 数据和专家的预测显示:5月可能是一个转折期。可能是北京的转折、中国的转折,进而是全球的转折。 既然是转折,我们希望向好,但也要提防反弹。有了先前的惨痛的教训,政府十分担心过早乐观和松懈的情绪,一再告诫各级官员和各地人民:疫情尚未完全控制,仍有进一步蔓延的危险,稍有不慎,可能功亏一篑。 虽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自由的呼吸,但现在,还没有到把口罩扔到一边的时候。 每个中国人都需要反思 SARS危机让我们重新考虑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个人 文/许纪霖 2003年的春天,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突如其来的非典病毒威胁着我们的生存。虽然这是一场公共卫生的危机,但在其背后,潜伏着我们这个社会多少年来积淀下来的某种危机和缺失。民族国家认同、社会自组织运作和个人精神信念这三大要素的匮乏,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国家 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不是人类世界的敌人,而是微生物世界的病毒。但就像对付日本鬼子一样,如果民族不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受到它的统治和奴役,甚至毁灭我们整个民族!不过,中外历史表明:民族危机的时刻,也是建立民族国家认同的最好契机。在这次危机中,特别是在中央高层处理了两位渎职的政府高官之后,全国民众表现出了对民族国家共同体强烈的认同感。在这以前,除了在女排夺冠、足球出线、申奥成功这样的时刻,我们很难看到这种向心力的表现。 但是人们发现,中国的公众却苦于没有合适的表达自己爱国情感的方式。过去人们都是被动员式地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一旦有了自觉表达的需求,却丧失了表达情感的空间、方式和仪式。比如,国旗作为现代国家的图腾,是一个很好的象征物。在9·11事件以后,在美国可以看到各地的民众在家里、汽车里纷纷挂起星条旗,以此表达对国家的支持和认同。但在我们国家,国旗很少是公众表达情感的载体。 不久前的一天,一辆出租车上挂起一面小国旗,这很让人惊喜,第二天,当看到每辆出租车上都飘扬着五星红旗时,才明白原来是按照上级统一的布置,欢庆五一! 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对国旗的自由使用,表达我们对国家的真实情感?为什么国旗只能是国家意志的象征,而与我们公众的真实情感无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们不仅丧失了表达爱国的渠道,还丧失了表达爱国的语言。在电视上,看到不少医务人员、军人、小孩在表达与国家同心同德,不怕牺牲,抗击非典时,语言贫乏,真是急死人。我们相信他们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他们的语言听上去是那样的空洞、无力。中国人真的已经丧失了真实情感的表达能力吗?是被我们的媒体强制过滤了?还是做老师的责任,让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只会使用统一的标准答案?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北京是灾难最严重的城市,不管其最初原因是什么,作为中国的首都和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理应获得全中国的同情和声援。但在这次非典危机中,人们听到和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北京的歧视和指责。虽然大家知道,各地对北京的实质支持是不少的,比如在北京需要口罩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批示要求上海全力支援,虽然这时上海也缺口罩。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挖断国道、对北京人围追堵截的场景。北京虽然缺医疗用品、缺医务人员,但最缺的是其他地区道义的支持和精神的关爱! 在这一时刻,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又是十分传统的。缺乏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意识,比较9·11以后美国人的众志成城,真是让人们感慨万分。 中国人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情感还很肤浅,我们不是没有这种情感,但一旦与我们的另外一些认同价值,比如家庭、家族或地方利益发生冲突,通常会把那些价值看得比国家的价值更高。中国社会,就像费孝通先生所指出,是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差序格局”,自我利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家族、村庄、地方的利益,最后才有可能是国家的利益。从晚清到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是否真正建立起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呢? 社会 这次抗击非典的战役,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采取了传统的行政动员、发动群众的人民战争方式。虽然很有效,但也暴露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各种自组织系统,在这次战役中,基本无用武之地。一个社会,假如在危机来临时,只能被动地依赖行政的垂直动员和控制,而无法启动自身的自组织系统,这本身就潜伏着一种危机。 有一些网友们在网络上激烈地批评政府,认为这次危机政府必须承担责任,甚至说,假使他个人得非典的话,要通过法律追究政府的责任。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但在这些貌似激烈的反抗言论背后,隐藏着某种全能主义社会的臣民心态。所谓臣民心态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和个人所有的问题都是应该由政府负责的,既然这个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政府的问题,那么我就有权利追究政府的责任。臣民心态可以是以正面的“顺民”形象出现,也可以以反面的“逆臣”方式形态表现出来,但二者背后的逻辑和预设是一致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灾难面前,个人和社会应该担负什么责任,除了批评和监督政府之外,作为独立的公民和社会成员,还能够做什么? 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假如它的民众缺乏公民和社群意识,同样会出现不堪忍受的混乱。海峡对岸的台湾非典也很严重,形势一度失控。台北和平医院被大面积感染,被隔离之后,有些医务人员借口人权,竟然违背隔离令,带头逃跑。而新竹市市长为了所谓当地选民的利益,也去堵截运送患者的车辆。一个现代的社会不仅要讲个人的权利,同时也要有公民的责任感,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在加拿大,亚洲回去的加拿大公民不用政府强制,都是自觉地在家里隔离两周,这是成熟的公民社会中的自觉。 我们今天对自由民主社会了解太肤浅,似乎只要有了权利意识,有了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我们没有看到,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社群。西方的人际关系中,除了市场和法律的权利关系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情感联系,因而特别具有人情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是没有人情味,但只是发生在熟人之间,在陌生人当中,不要说人情,连起码的交易信用都可以不遵守!这样的传统社会一到现代都市生活,人际关系就表现得特别冷漠。 现代的城市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空间,现代都市生活剪断了与以前传统社群的联系,把你抛到一个完全陌生和非人格化的空间之中,如果都市中缺乏社群生活的话,这个社会是经不起灾难打击的。北京这次的悲剧就在这里。北京的人口流动性非常高,许多北京人都对北京缺乏认同感,更别说这么多外来人口了,这次逃离北京的大多是学生和民工。北京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赚钱和拿文凭的城市,他们和北京的关系是很脆弱的,社会上也没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亚社群让他们留恋。人之所以感到恐惧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让他感到孤独,无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剩下一条路,只有逃离。纷纷逃到自己的老家,因为在老家,还有他们所依赖的社群:家庭、家族、邻里等等。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各种各样的亚社群了,即使有,也缺乏体制化的保障,中国的大学现在普遍禁止成立同乡会,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反思。 个人 在这次非典危机中,很多人患了非典恐怖综合症。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症状。比非典病毒更难应付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性的病毒。 如何使自己在灾难时刻获得对生命和生活的信念,成为一个勇敢的公民,如何在世俗社会中获得神圣性,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在网上北大一个留守在校园的新生写帖子,讲到他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慌之后,省悟到“北大精神并不仅仅是面对成功与喜悦的激情昂扬,也应该有面对危机灾难时候的冷静、沉着、不盲从——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并且能够上前线——治疗、护理非典病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平静的心态,不恐慌,不盲从,并且不把任何不健康的情绪传染给别人;尽可能多地给他人以关怀。”有网友在跟帖中称赞说:这也是一种英雄!世俗时代的英雄不必刻意轰轰烈烈去做什么事,只要保持平常心,做平常事,也意味着战胜了荒谬。 这是一个灾难的时刻,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对许多人来说或许一生只有一次。能否在这样的时刻实现对自我的升华,在于每个人的自我选择。人们希望,危机过后,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和每一个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阴暗的回忆。 (作者是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
北京暂舒一口气
北京人可以暂时舒一口气了。乐观的人说,北京已经渡过最危险的时期,除了疫情,还有心理。但SARS向周边扩散的趋势,并未被完全遏制,在这个时刻,我们仍需要小心 本刊记者/孙亚菲 在北京市西城区防治非典办公室里,任爱国正在忙着核对刚报上来的数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防非办”每天都要收到来自区疾控中心、卫生局医政处以及街道办事处等多家送来的新增非典病例数据。作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派驻西城区“防非办”的专家,任教授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数据进行核实,并据此对疫情做出分析,然后提供给领导做决策参照。 “这几天压力小多了,因为我们一连好几天的报告病例,都在10例以下。”任爱国一边翻看他做笔记的小本,一边回忆说,在他到“抗非”一线来的十多天里,西城区报告病例最高的一天曾达45例,而自从5月4日开始,新增病例便降到个位数以下。“昨天5月11日新增7例,5例确诊,2例疑似;而今天又有下降,4例确诊,2例疑似,虽然没完全杜绝,但形势确实在好转。” 与任爱国同样感到欣慰的,还有他的同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曹卫华教授,他从4月17日就进入北京市朝阳区疾病控制中心,见证了SARS在这个“北京的第二大疫区”从爆发到逐渐得以控制的全过程。 “那时侯,一天最高有70多例疑似和确诊患者,疾控中心的同志整天疲于奔命。而到现在较长一段时间,每天只有十几二十个新增病例,而且确诊的只有四五例,这是很好的现象。我估计,再有7到10天时间,朝阳区的新增病例很快就能降到一位数。”曹卫华乐观地表示。 另一个消息也鼓舞人心:全北京市5月12日新增诊断病例48例,其中有39例为疑似转临床,而新增的疑似也为48例,比前一日少了3例,没有出现回升势头。 街上的“口罩族”减少,行人车辆增多,商场开始恢复以前的热闹景象,种种迹象都表明,北京正在努力走出高发疫区的阴影,重新回到阳光下。 北京渡过难关? 5月是关键的一月,前10天是检验政府新措施的关键时段,控制得力与否,全可由此见端倪——4月底,记者采访不少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时,他们不约而同做出如此预测。 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除了5月的头三天,北京仍以平均110例的确诊数让公众很是紧张了一阵外,之后基本一路走低,没再越过三位数的界限,在90上下徘徊了三四天之后,5月9日成为新的突破:低于50例。直到截至5月12日的最新数据,北京在过去的四天时间里,新增临床病例平均不超过50例,而且绝大部分是由疑似转为临床。也就是说,北京控制非典的防护网,基本上做到了把问题发现在早期,控制在萌芽状态,漏网之鱼越来越少。 “现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举措很坚决、很有效……我不认为有多么的可怕,我觉得可能会控制得比较好。”早在5月4日,广州呼吸道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很乐观地下了一个定论:北京基本上渡过了艰难的高峰阶段。他的理由是,根据流行病的规律以及广东、香港的经验,SARS的传染期在两到四个月之间,而高峰期约为15至20天,即使没有采取措施,疾病本身也会自然回落,何况外界进行了非常得力的干预。从北京爆发的时间推算,应该过了高峰期。 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岩教授也赞同钟南山的说法。她介绍说,传染病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是更大面积的爆发,另一种是全社会获取免疫性屏障,疾病慢慢衰退。 “而北京,从时间和过程来看,两种情况都经历了。”郭岩把北京的SARS疫情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她意味深长地用了一个英文单词“undertable”来形容。“这个阶段应是在新市长到任以前,其特点首先是疫情的严重性没有向公众说明,导致从官员到社会群众都没有警戒意识。另外,有关部门措施不得力,比如用首诊负责制来对付SARS。这种错误决策带来的后果是,很多不具备接诊条件的医院医护人员出现大面积感染,医院成了最大的传染源。” 认识和措施都不到位,为4月中下旬SARS的全面爆发埋下恶因。郭岩举了个政府对SARS认识偏颇的例子:“当时曾有命令,要求北京市各个区都不许出现一个SARS病例。那怎么可能!这样的命令是非常不符合科学规律,很官僚的东西。” 4月24日,被郭岩看作是北京抗击非典的“里程碑”,同时也是第二阶段的开始。“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止,为SARS爆发的高峰期,一天152例诊断病例的最高纪录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创下的。”郭岩分析说,由于前段时间控制干预不力,经过近半个月潜伏期,刚好集中在此时段爆发。但也是在这关键时刻,新市长上任,防治措施做了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譬如设立小汤山等三家定点医院,隔离措施更加果断严格,疫情公开透明化,政府行为受到监督。 “其效果在第三个阶段显现。5月9日是一个标志性时间,那天,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较高峰期)下降了一半,之后几天一直保持平稳,事态发展朝向好的方面。”她说,这也证明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与郭岩教授分析相吻合的是,5月9日,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局副局长、流行病学专家梁万年宣布,北京市持续了十几天的SARS上升平台期,已经下降到一个低水平的平台。他还用“有效控制”和“出现了下降的迹象和趋势”这样的语言来答复记者,这是在张文康、孟学农被免后,官方第一次以如此肯定的口吻来评价当前的SARS形势。 5月11日,北京市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通报说,北京23464个被隔离者中,已有13274人安全解除隔离,重新回归社会。随着一系列“利好”消息,是社会恐慌心理的减轻和社会活动的重新恢复。 北京市防治非典咨询热线一位姓郑的接线小姐告诉记者,现在打热线电话的人比以前少得多。“前段时间我在这儿当班,热线几乎没断过。而现在基本上每小时接十来个电话,而且他们的情绪比以前也平和多了。” 这表明北京人已渡过了心理危机。记者还在北京数家商场看到,那种排队购买大量米面油甚至方便面的情况不复出现,超市的购物者较以前增多,大家井然有序购置所需物品。越来越少的病例和人们开始放松的神经,都在昭示着,北京似乎渡过了SARS爆发以来最危难的时期。 关于“高峰期”的争议 然而,WHO的专家官员们和世界一些国家,尚没有中国人那么乐观。WHO总干事布兰特兰日前就表示,虽然北京的疫情得以缓解,但“最坏的情况还没到来”。北京要摘去疫区帽子,为时尚早。 记者曾看到由北京大学数学系模拟的未来疫情走势图,图上显示,在5月中下旬,北京疫情逐次下滑,但到了6月12日左右,一个新的高峰骤然出现。那么就是说,疫情在未来有反复的可能。当然这只是一个数学模型,一切尚有待检验。 然而,研究流行病和公共卫生的专家却坚持认为,只要目前实施的各项措施可以持续下去,这样的高峰就不会再出现。 郭岩教授认为,SARS虽然在全国蔓延,但很多地方都是输入性病例,由此可见,关键是能及早发现,发现后组织力量,把传染途径切断。 “应该说,目前国家采取的防范措施已经比较到位了,没有什么明显疏漏的地方。因此,除非有不可抗的因素,譬如‘漏网之鱼’在人口密集的小区、学校造成突然性的集中爆发,那么,北京的疫情应会很平稳地维持在较低水平一段时间。” 郭岩表示,被一个突发偶然事件改变走向的情况不是没有,但可能性不大。她估计,只要措施得当,再有20天到一个月时间,北京疫情可以降到广州、香港目前的水平,每天在五例上下波动。 “我们在一线看得非常清楚,北京的SARS高峰期确实已经过去了。”任爱国教授认为,北京的疫情重心已经下移,目前进入了一个“低位平台期”,而且这个曲线还会往下走。但对于这个平台期持续多久才往下走,他表示难以估计。 “市里面领导很早就问我们,大家能不能判断一下,这个病到什么时候能够下去,能够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这涉及到市里面决策,要动用多少的资源的问题。当时大家伙都非常谨慎,表示没有足够的资料让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表。毕竟对于SARS,我们的认知太少了,还有很多无法确定的因素,影响到未来的流行趋势。” 在他看来,SARS在潜伏期有没有传染性,是影响未来走势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国CDC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曾做出“SARS在潜伏期没有传染性”的结论,但任爱国等不少在一线进行研究的专家却对此表示怀疑。依据是,疾控中心人员曾对多位疑似和确诊病人进行调查,问他与谁接触过,尤其是否曾和病人接触过,但好多人都表示没有这样的历史。 “染病原因查不出来,这就使我们怀疑,SARS在潜伏期是不是就有传染性了?但这个问题谁也不能回答:有,还是没有。如果没有传染性,那么这些人的病是从何而来?如果有,那么现在的局势还是不可预期的,等一段时间,才看得出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他说。 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SARS疫情得到控制,民工返回城市务工,学生回校上课,很有可能把病毒重新带回北京,造成第二轮新的流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教授,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这种担心,但他认为,在目前布控的防御网络下,即便是有外地的带毒患者到北京,还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关键是整个监控网络不能散,人的警惕性不能因情况好转而放松。他反复强调:“千万不能麻痹大意,一点小的疏漏,造成的危害难以估量。这也是对我们防治队伍的严峻考验。” 全国往何处去? “形势依然严峻。”5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山西太原考察时,不无忧虑地指出,目前防治“非典”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并有“继续蔓延扩散的危险”。 两天后,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四川省富顺县,考察农村防治“非典”工作。胡锦涛说,当前,“非典”疫情扩散的危险还没有消除,防治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十分艰巨。 温家宝山西之行的背景,是整个华北疫情严重:以北京为中心向周边省区扩散,先是山西、内蒙古,而后波及到河北、天津,华北地区的增长速度在全国位居前列,其中以山西省最为严重,除了吕梁地区还没有报告病例外,其他20个县市区,从城市到农村,几无完卵。 尽管全国疫情的走势与北京相类,随着北京的减少也有走低趋势,譬如5月12日新增疑似病例创了新低,仅为95例,较之10天前的最高峰322例减少了三分之二,新增确诊病例自5月10日始就低于三位数。但不少专家认为,全国防非典的工作还没有进入最关键的时期。 姜庆五教授把SARS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02年的11月到今年的2月,以广州和临近地区为中心向外扩散。第二个时期为三四月份,朝南扩散到香港,朝北侵袭到了北京。究其原因,香港是临近地区,与广州交往频繁;而北京是政治中心,与外地交往频密。而第三个阶段,是北京朝四周和全国扩散的时期,而且发展很迅速,华北地区首先遭殃,其他25个发现非典病例的省市,绝大部分是由北京输入的。 “而且,这种趋势还没有停止。从卫生部每天的疫情报告可以看出,新增临床诊断病例还占一半以上,这说明第三个时期尚未结束,不但如此,还可以看出它仍处于传播的旺盛期。” 姜庆五有些忧虑地表示,呼吸道疾病往往和气候有关,冬春季节为高发期,如果控制不力,有朝气温更低的北方地区蔓延的可能性。5月12日的疫情报告似乎做了佐证:在8个报告有临床诊断病例的省份中,除了广东和华北五省市区外,就是东北三省的辽宁和吉林。 “实际上,SARS一直在蔓延,我还看不出短期内它有停止的迹象。”北京大学的郭岩教授说,从全国的趋势看来,这几天报告疫情数降低,主要是由于北京得到了一定程度控制而减少,但并不表明全国的情况在好转。“5月11日内蒙古报告的新增临床诊断为0,但我很担心,它一下子从高发到0,不知是否会反复?” 任爱国说,他个人“比较武断”地判断,全国SARS疫情“还没有到高峰”。他的理由是,全国各地控制SARS力度肯定比不上北京,财力、人力、物力资源都与北京有相当大差距,所以发病的趋势可能会往后推,时间会延长。 他举例说,比如对病人的管理上,北京有定点的医院,有非常好的转诊系统,对有发烧症状的人,只需要在家通过电话向医务人员请求帮助即可,医务人员会亲自上门来诊断有没有可能是SARS患者;如果是,则有专门的接诊车送去定点医院,避免了外出诊治过程中的传播问题。另外,在对密切接触者隔离的管理上,饮食免费,工资照发,若没有相应的人力物力,做起来非常难。 “影响疾病流行的因素多种多样,不仅仅是单纯的病理原因,社会因素尤为关键。现在各地都有了相当高的警惕,也采取了应对之策,但还存在管理措施不到位,物资条件跟不上的问题,控制起来不可能像北京那么快。” “在失去警惕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曹卫华教授说,目前抗击SARS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决不能掉以轻心,以免造成恶果。但他最为担心的,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忧虑目前的应急体系究竟能维持多久。 “现在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把日常卫生系统变成应急系统,这个非专业化的队伍能支撑多久?在全国范围内能起多大的作用?都是问题。”曹卫华认为,必须迅速建立起一支专业化的应急队伍严阵以待,随时听命,应对危急事件。
北京拉网
为了斩断SARS传播途径,流行病调查队要在第一时间里从茫茫人海中找到SARS患者接触过的人群。这是一项关键却艰难的工作,虽然北京的2500名流调人员做出巨大努力,但仍有一半的患者没能找到传染源。它意味着,危险仍随时在我们身边潜伏 本刊记者 文/孙展 李楠 摄/郑萍萍 “姓名?”、“年龄?”、“职业?”、“居住地址?”、”工作单位?”、“户口所在地?”、“发病时间?”……当周世凯问到第七个问题的时候,距离他面前不到两米的这名病人出现了明显烦燥情绪,态度也变得不太友好。但这只是一份名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例个案调查表”中的开头几个问题而已,要把这份调查表中的43个问题全部问完,显然还为时尚早。 40多分钟后,周世凯脱下了厚厚的多层防护服,汗水很快从额头流了下来。“每天都要这样重复多次,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5点。”周说。这位不满25岁的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流行病调查大队(简称“流调队”)队员,和他的80多名同事,已经夜以继日的工作了50多天,而此时,北京市共有2500多名这样的流调人员。 没有人告诉他们在什么时候才结束这项工作。 流疾难控 每当医院接收到了非典(包括疑似非典)病例时,医院必须在第一时间通知疾控中心,流调队员们便火速出动赶到医院为病人做面对面的调查,“刨根问底”地找出病人的传染源何在,近期内和什么人有过亲密接触。然后将得到的信息进行处理,通知相关单位,将非典病人的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 5月9日,在接到望京医院的通知后,周世凯和他的搭档——刚从医科学校毕业的梁艳蓉就出发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调查一名刚刚被确诊的“非典”患者的情况。最核心的问题是要知道他“最近一段时间的交往情况”。 车一到望京医院,周和梁就迅速地套上了防护服,显然,这是多天累积而来的熟练。 发热门诊在一个简陋的院落里。几名戴着口罩的病人正在这里静静地坐在凳子上输液。如果不是看到遮护严密的医护人员,没人能够想到这里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周和梁要调查的对象也在输液。这是一名44岁的男子,在首都机场货运部门工作,发病前和其母亲居住在一起,其母也于前几天出现了发热症状,但“她在村卫生所看了病之后已经好了”。这名李姓患者说。显然,这个情况要尽快得到查实,否则无人能够判断这其中还潜藏着什么样的隐患,而和李共事过的同事,也将成为隔离观察的对象。 “这种情况算是比较简单的”,周世凯说,“很多未曾留下姓名或没有得到很好隔离的患者的流行病史,追查起来有如大海捞针。” “流调队只能尽最大的努力追查流行病史,但疫情如要真正得到控制,预防才是最关键的,事后的亡羊补牢总是事倍功半。”于德利满脸焦急地说。 预防难为 北京有机化工厂在5月7日前后发现一名民工出现发热症状,于是将其送往医院。而这名病人未经“流调”已被转送小汤山医院。 朝阳区疾控中心的吴大夫在5月9日下午3点接到指示前往有机化工厂进行“流调”。到达化工厂的时候,一群民工正围着一张桌子测体温,几乎没有人戴口罩,在见到身穿防护服的流调人员之后,有些人才面露惊讶之色,慢慢地将口罩戴上。 桌子上只有两支体温计,却有200多名民工在排队等候测温。有些人显然是等候不及,象征性地将体温计往酒精中沾了一下,又在腋下夹一夹就取了出来。即便是这样,还是有几名工人被测出体温过高。 “这样的措施太危险!已经发生了疫情,却还有这么多人群聚在一起,很容易导致大面积的传播。”吴大夫对记者说。可是,当吴大夫走到病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时,才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一幢陈旧的二层小楼,200多个民工就住在这里数十个房间中,楼内昏暗潮湿,空气污浊。而曾经与病人同住一室的三名工友被锁在自己的房门之中。房门最上一层隔档被卸下安装了十字形铁条。“送饭取药就由这个小洞递进去,”一名工人指着房门说。如此隔离措施,显然已让一部分工人放心了,“只要他们不出来乱跑就行。”看护他们的工人对记者说,接着他伸手拿了由屋内被隔离人员递出的钥匙开了门。记者注意到,此时他既没有戴手套,也没有穿任何防护装。 被隔离的是三名湖北籍农民工,流调人员到达的时候,他们正在看电视。这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屋内显得有些凌乱,地上很潮,似乎是刚刚喷洒完消毒液。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能到楼前打一会儿篮球。”一名工人怯怯地对吴大夫说。当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把头低下不再说话。在他侧面摆着一个鱼缸,缸里的鱼正在自由快活地游动着。 “流调”人生 和朝阳区流调大队队员一样,从3月15日北京市西城区第一例“非典”病例报告开始,40名西城区疾控中心的流调队员们已经奋斗了50多个日夜,做了600多次的调查。 流调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西城区疾控中心党支书商雷堂告诉记者,他们在早期的调查中发现,非典病例的最大传播途径是医院,很多人都是在医院感染的,他们据此向区里汇报,在得到北京市有关部门同意后,果断地关闭了人民医院和北大医院。这是近日来西城区非典发病数明显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流调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搜集信息就需要接触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因为队员们必须进入隔离病房直接接触病人,所以,其本人也属于危险人群,在工作期间都不能回家,吃住都在办公室。队员李丽的爱人在疫情开始前不久刚刚去世,她忍着悲痛投入到了工作中。由于过度悲伤和劳累过度,李丽的消化系统功能出现紊乱,呕吐不止。但是她仍然坚持工作,她说:“我虽然不能参加流调了,但我还能接电话。” 疫情高峰期间,疾控中心的5部热线电话每天响起800多次,大部分是咨询电话。有的咨询者情绪激动,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甚至张口责骂。负责输录表格的王楠,创下了连续30个小时不休息的纪录。 商雷堂说,他含着眼泪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些细节。 由于分工不同,队员们在跟医院的合作中也会遇到困难。每次,出了隔离病房,所有随身物品都要销毁,包括隔离服和记录使用的笔。调查表也是近距离接触病人的物品,一般医院都不允许带出来,队员们只好说服医院,并包裹上若干层,回来消毒后再打开进行数据统计。实在不行时,只好一个队员进入隔离病房进行调查,另一个在病房外用对讲机联系进行记录。 除了可预见的困难,队员们还得面对许多想不到的麻烦。队员李民告诉记者,一些非典病人对调查工作很不配合,不愿意说出曾经接触过谁,这时,队员们就必须想方设法套出他们的话。孙木曾对感染了非典的一位文艺界知名人士进行过调查。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知名人士始终不说他和谁有过接触,孙木于是便和他聊起了家常,问他近期有没有给学生上过课?对方回答“有”。孙木接着问,是不是有车接送?他也说有。就这样,孙木才一点一点搞清楚了和他有过接触的人群。 在谈到工作甘苦的同时,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们也对现行的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有些抱怨。商雷堂说,为应对非典疫情,中心的花费已经大大超出了预算,每个队员每执行一次任务,平均就要用掉100多块钱。而上级的补充拨款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过,这些问题也许在这次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能得到解决。 救命药还要等多久?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