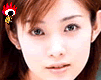作者:闵良臣
不怕挨小说作者的骂,我是不大看现在一些人写的小说的,缘故之一,就是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的小说仿佛只关注“小资”,只关注新生的“中产阶级”。就好像我们的社会真的是已经全面实现了小康似的。请原谅,我是个只相信事实、只相信自己眼睛、只相信自己的感受的人。媒体也好,“文件”也罢,说真的,都只能“仅供我参考”。
从媒体最新消息得知,南京有作家以南京的市骂作小说标题发表后引来轩然大波,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有人说是揭露丑恶,有人说是对城市丑化;有人说南京应该反省,有人说作者是哗众取宠。不一而足。
这一切,我都不关心。哪有一篇小小说就能把一个不是丑陋的城市弄成丑陋了的。一个城市真是脆弱到如此地步,我看比描写的那些丑陋还要更加影响这个城市的发展。再说,总是一个城市有了丑陋人们才去写,而难以想象因什么人的说和写会把一个美丽的城市就变得丑陋了。一个城市丑不丑陋,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是完全能感受得到的。至于说到一个城市在某一点上是丑是美,这要看事实。即如11月7日《娱乐信报》的报道中所说,一位“南京人”一家报社派驻以色列的记者,去年回国向记者直言:“去年回来以后自己也觉得南京话确实很难听。雅兰(那篇小小说的作者)的小说标题虽然粗俗了一点,但毕竟反映了事实。我发现南京的年轻人尤其喜欢说脏话,几乎每句话都带着脏字。我曾经陪着外国朋友去五台山看球赛,几万人一起喊‘南京呆B’,我听了都脸红。南京整个城市的文化素养确实不高。”这说明南京城市中至少有不少青年人喜欢“出口成脏”是事实。当然,我们永远要记住:不能遇见一个坏人,就把所有的人都作坏人看(鲁迅语,大意)。更要记住一位伟人所言:除了沙漠地带,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肆意丑化一个地区,肆意丑化一个城市都是要不得的。
回过头来说,我更关心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家都在写什么,因为写什么也就意味着他们关心什么,他们关心什么,也才会写什么。前不久,我批评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因为有了“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因此我们似乎就应该有《英雄》《天地英雄》这类的影视剧供这个阶层享受。我们确实有了一个可以称得上“中产阶层”的人群,也确实应该有让他们去“享受”的文艺作品。但古今中外证明,这种作品不一定就是像《英雄》和《天地英雄》之类的东西。尤其是对一个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度的作家而言,就算你已经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你依然不能只去关注中产阶级——即使中产阶级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了——因为全国更多的却是才刚刚温饱不久的人群。这里且不去统计现在我国大小城市中的绝对贫困人口数(想来不会是一个小数字),单按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后答记者问时说的话,即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人口约3000万(从后面的文字中可以认定这仅是指农村而言),这仅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标准计算的,如果把标准增加200元至825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一个人一年只有825元呀,恐怕还不及有些人请客时的一顿“便饭”。
对此,《娱乐信报》的报道中一位大学教授有清醒的认识,他说:现在很多作品其实是一种哗众取宠,只是写了城市的影子,像大商场、酒吧之类,对社会底层却不曾关注。这实际上是在一种想象中写作,而且还不是一种健康的想象。如果想通过这些作品去了解城市,是误入歧途。
说至此,不能不令我又想到了鲁迅。几年前有“庄周”在《书屋》上连载《齐人物论》,其中“百年新文学余话”中有一小章,题为《百年“树人”的鲁迅》,对鲁迅的“定论”是这样下的:
鲁迅先生世纪中国文学第一人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我的理由很简单,只有鲁迅先生以自己的如椽巨笔向国人奉献出的下层民众形象,才使得我们可以像俄罗斯人提到乞乞柯夫、拉斯科利尼柯夫、美国人提到亚哈船长、桑地亚哥老头、法国人提到纽沁根、“局外人”那样,提到我们自己的祥林嫂、阿Q和孔乙己,并坚信他们的确存在过。这是真正属于中华大地的民众形象,他们的屈辱和蒙昧,高贵和卑贱,性格和情感,都具有无可置换的中国特色,这三个在小说里最终都悲惨死去的中国百姓,恰恰具备甫一现身便进入不朽的文学伟力。鲁迅先生以自己看上去更像业余爱好者的产量而能奠定在中国世纪文学的崇高地位,的确只能反衬出其他同行的卑微渺小。(2000年第12期,第44页)
我还想到了学者朱学勤先生在《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中所言:“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能)想像(得出)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又说,“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们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均见鄢烈山选编《2003中国杂文年选》第470、471页,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我不知我们有哪一位作家也会像朱学勤先生这样,因认为自己的“苟活幸存”而产生对自己的“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