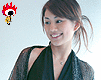(特别报道)还滇池一潭碧水(组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24日07:01 荆楚网-湖北日报 | ||||||||||||
湖北日报记者陈熹 通讯员余平凡
滇池,这个被誉为“高原明珠”的湖泊,由于蓝藻水华泛滥,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从2000年起,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刘永定带领一支队伍,住进滇池之畔野外小屋,向蓝藻水华发起挑战——— 世界难题 11月的一个早晨,昆明滇池上空缆车里,一位北京游客俯视湖水后啧啧地说道:真脏啊!一点可见度都没有了,浮着这么多的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啊? 这位游客说的绿色浮游物,便是蓝藻水华,俗称“绿油”。蓝藻水华死亡后还会释放出毒素,不仅毒害了水中的其他生物,而且腥臭难闻。滇池,这枚“高原明珠”正是因为它而失去了往日的丰采。 滇池是我国第六大淡水湖,面积297.9平方公里,是世界上过富营养化最严重的三个湖泊之一,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藻类水华暴发。 20世纪60年代,滇池水清澈见底,水生植物丰富,是许多鱼和鸟类的良好栖息地,水质达到地表水II级标准。70年代以来,随着昆明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盲目地大规模围湖造田,使水生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丧失,滇池水质迅速恶化。 近20年来,滇池水体理化环境随着水体污染的发展而不断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进而影响到整个水生生态系统的平衡,改变原来水生生态系统的形态和特征。 滇池低纬度、高海拔,气温恒定,换水周期长,治理滇池蓝藻水华,成为世界性难题。 临危受命 云南省环保局数据,截至2000年,国家前后共计投入资金40.78亿元,其中直接用于滇池污染治理的达到29.4亿元。 水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而蓝藻水华污染控制是其中的关键之一。2000年,国家科技部首次以公开招标的形式,选择单位承担课题。 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为能拿到该课题,召回了刚去法国做访问学者的刘永定。 刘永定是著名的藻类学家,他带领的团队在竞标中胜出,被确定为该项目的牵头单位,和中科院南京湖泊与地理研究所、云南大学、昆明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等12个单位共同承担,另外还有几位科技工作者以个人名义参加课题。 拿下这个“首次”招标的项目,虽然展示了水生所的实力,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各方都看着呢。”刘永定笑着说。 课题组面临的局面是,滇池流域的水污染、水资源短缺和蓝藻水华污染同时发生。课题组在滇池边建了一个野外工作站,当地农民几间卖韭菜的平房,就是他们的实验室和宿舍。 4年间,一共有130多人在这里工作过,日常固定的研究人员约14名,来自日本、法国、韩国、美国等1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或企业技术人员在这里合作试验过。“国外不可能像我们这样长期派驻一个队伍蹲在湖边搞科研,这些东西在实验室是搞不出来的”,刘永定说,“我们的蓝藻水华理论不比别人落后!而且有的比他们做得更好”。 挑战尖端 蓝藻水华污染控制技术是一套以水华蓝藻环境生物学和富营养型湖泊稳态转换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技术。从2000年起到该项目验收,经过了三个阶段。 2000年,课题实验区建立,这个以湖泊污染治理为目标的实验湖沼学实验研究区位于滇池东北部,面积6.01平方公里,用非封闭的高强度抗风浪柔性围栏将试验区与外湖分隔开来。 2001年至2003年,试验区内的水质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课题组在实验区开展了生物控藻、机械除藻、湖岸生态修复、蓝藻检测和脱毒、湖泊生态系统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创新成果,并建立了多项示范工程,使得试验区内自身发生的蓝藻得到了有效控制。 实验人员介绍,生物控制蓝藻水华,就是利用不能自然繁殖的鲢鳙来吞吃蓝藻,达到有效控制蓝藻繁殖、再生的目的,并大量种植多种水草,养殖螺、蚌等低栖动物,恢复实验区内的原生态。与此同时,结合机械除藻,将打捞上来的藻类提取藻蓝蛋白、藻多糖、做饲料、肥料等。 2003年至2004年,课题组逐渐扩大试验区,并将水文、气象、生物、化学、社会变化等综合考虑,使实验区的研究更接近自然的真实性。 说起来简简单单的三个过程,其困难却难以想象。刘永定和他的课题组,经过4年的艰辛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课题通过验收时,专家组一致认为该课题在蓝藻水华污染控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国家环保总局领导解振华、汪纪戎,时任科技部副部长的邓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等,曾亲临滇池试验基地,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专门发来贺信。 蓝藻水华污染控制技术研究课题完成了,但离在大湖中取得实际效果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治理滇池污染任重道远。 国内外湖泊治理专家介绍,一般湖泊治理至少需要10-20年,才能取得明显成效,日本对其琵琶湖的治理,费时25年,耗资185亿美元,水质才接近三类标准。湖泊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 滇池有6条“病根”,一是流域内水资源严重短缺;二是生态环境脆弱;三是污染源控制难度大;四是生态修复具有复杂性和局限性;五是投资巨大;六是管理难度大。 课题组紧接着承担了“滇池入湖河流水环境治理技术与工程示范项目”,该项目计划投入9000万,刘永定依然被聘为首席科学家。 这一次,采取专家组负责制。“听说没完成预定的目标,我们要承担责任,这又是第一次。”刘永定透露出的是自信和踌躇满志。 固守站点为水清 湖北日报记者陈熹 通讯员余平凡
几间破旧的平房,几台电脑,床,书桌……这是云南滇池边的小河嘴村里一个普通的院落,在周围农民的楼房映衬下,显得有些寒酸。 如果不是那些试验设施,以及每个房间里面都有的网线,没人会想到这是一个承担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工作站。 这是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滇池蓝藻水华污染控制技术研究”课题组在这里建立的一个野外工作站。首席科学家刘永定和课题组成员在这里已经过了4年,另有130人在这里工作过,长期固守的固定研究人员约14名。说起这几间平房,站长沈银武说,这个院子很便宜,以前是一个卖韭菜的市场,只有外墙和屋顶。租下来以后,隔成了几间房间,分别作为宿舍和实验室。“条件不错,有热水,有人做饭,可以上网,没有人抱怨。”刘永定说。 院子里,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是一年国庆,课题组坚守在滇池边,为庆祝节日,他们买了一面五星红旗。此后,升国旗成了课题组经常举行的仪式。 节假日不休息,通宵工作,这对于课题组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刘永定的每个春节都是在工作站度过的,“初二、初三给年轻人放假,让他们进城玩玩,的确太辛苦了,我就留守。”而沈银武一年有300多天都在这里,几乎没有时间回去陪家人。在刘永定和沈银武的感召下,课题组成员全身心地投入到滇池治理的攻关研究中。有一次,陈旭东肚子疼得无法忍受,也不愿意放下手头的研究,带病坚持工作。后来被强行送到医院后,经诊断是盲肠穿孔,立即手术。 68岁的陈英鸿研究员则把生命献给了滇池,作为专家接受课题组的聘请后,陈英鸿先后5次来到滇池边,进行“鲢鳙鱼控藻功能机理研究”。为了弄清底泥能否种水草,需要取一些底泥作研究。第一拨取泥的人回来说太硬,不能种。陈英鸿说,插深点再试试看。取泥的人说,还行。为了彻底弄清楚,陈英鸿决定自己下水查看,他带着工人跑到试验区,由于体力不支,没能游上岸。被救上来送到医院时,医生作出了“溺水死亡”的结论。 艰苦和牺牲没有动摇课题组成员的信念,尽管滇池蓝藻水华污染控制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工作,尽管年轻的博士、硕士刚来时不会有很直观的成果,但大家还是坚持了下来。4年过去了,当初的辛苦和犹疑变成了热爱。一位年轻的博士说,我最怕的就是这个野外站撤了,我想在这里多干几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研究有很大帮助。 有一年的春节,课题组的成员在湖边小屋的门上贴了这样一副对联:直面灾变消藻害天道酬勤不酬怨;固守站点为水清人间有苦亦有甜。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