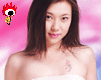“老克勒”最后的据点(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1日15:33 北京青年报 | ||||||||||
住在这里的徐元章,没有权、没有势,十分随和,是一个喜欢听西方音乐的著名水彩画家。 面对这一切,有时候你会感到有些疑惑,这里的一切,总那么与众不同,总那么出乎你的预料,这里面,到底蕴藏着什么呢? 因为这祖传的私家花园和徐元章的老上海系列水彩画,无数国内外媒体络绎不绝慕名前来宝庆路3号。而徐元章本人则笃悠悠地守着他的大花园,任凭外面的世界多么热闹,他的生活似乎仍然停留在了过往的时光里。 每个周日的下午,宝庆路3号的客厅就会热闹起来。华尔兹、吉特巴、恰恰,舞曲响了起来,再看身手敏捷的舞者,却都是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们风度翩翩、舞姿优美,举手投足间隐现昔日大家闺秀、富家公子的风采。看着屋内轻柔舞动的人们,望向窗外的草坪,那一刻,时光竟真的倒流了,旧上海的浮华逼真呈现。 这大概是上海滩上“老克勒”们(洋泾浜英语,取意class,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旧上海称资本家的儿子为“小开”,“老克勒”以前就是小开)的最后一个据点了。也就是这个固定的舞会,引来不少中外美眉,她们在向老绅士们讨教舞艺的同时,得以一窥昔日上海大户人家的光景。难怪有人还把徐元章和他的大宅比作老上海的“活化石”。 “到我这里来的,都是些老朋友了,比如住在朱家花园的‘面粉大王’后代朱小开(又叫十七),‘钢铁大王’的女儿朱文琪,还有‘席家花园’主人的后代,英美烟草公司总代理的后代,还有程乃珊、陈丹燕等也是常客。”随手拿起一本关于上海老洋房的书,徐元章指着里面的房子,说着这些房子原来的主人是谁,他们的后代谁谁前两天还在这里玩。 朱小开则对记者说:“我每周日来,因为都是老朋友啊。周五我不来的。”听说本报是《第一财经日报》,朱先生说:“哦,你们是做财经的啊,我也是做财经的啊,前些年我还在香港管事呢。”徐元章告诉记者,朱小开因为在香港的事业比较成功,是“老克勒”里情况不错的,不久可能就要移居到国外去和子女团聚了。还有一些人的生活就过得一般了,肯定不可能有年轻时候好了,但是这不能阻止他们内心当中固有的喜好。 “我的膝关节最近总有点疼,但是一跳舞就好了。不跳舞,就变成‘跷脚’了。”朱小开说。他和这个圈子里的其他“老克勒”一样,年纪不轻了,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心态却都很年轻。 “我们不在乎别人叫我们‘老克勒’,在我看来,‘老克勒’就是有层次、上档次的老人,经历很多场面,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有这样的人才懂得经典的音乐。一听这音乐,就会想起年轻时,在大学里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跳舞、喝咖啡。”徐元章沉醉在流行于1919-1930年、据说现在只有在欧洲皇宫大院才能听到的贵族音乐《永久的爱情》中。听到愉悦处,徐元章双臂舒展,深情地和着音乐,“这些人都喜欢来我这里,这种音乐、这种房子都会让他们觉得与身份匹配。” 上海的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关注着这些“老克勒”们。他认为徐元章的趣味是令人尊敬的,在最压抑的年代里,他仍然保持了对西方文化的热爱。朱大可把“老克勒”作为海派文化第二阶段的核心,是租界形成以后、严格讲是1860-1949年形成的海派文化。这是很多人提到的上海人擅长兼收并蓄的时期,由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崇拜心理,转变为一种生命的信念和哲学,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老克勒”。朱大可这样为“老克勒”画像: “走路笔直、穿花格子的衬衫、衣服一定要送到洗染店去洗、裤子上的两条熨线是一定要有的、皮鞋一丝不苟擦得非常亮。他们再穷,也会保持一种绅士的风度和生活状态,在想象的空间里消费西方文化。不仅这些,他们还狂热地热爱西方的爵士乐。西方古典音乐当中比较通俗的部分,西方音乐当中有一些非常有思想的东西,他们不听。说话喜欢带一点英文,是一些洋泾浜英文。‘老克勒’狂热地收集爵士乐的老唱片,到后来不单是去听这些唱片,收集后放在那里就是一种巨大的满足,听到爵士乐就浑身颤抖,这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族群。 1949年后,‘老克勒’用劣质的咖啡茶代替南美咖啡,在平庸的生活中创造着情趣。‘老克勒’就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层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们也顽强地保持体面和尊严,在经历了短暂的苦难之后,‘老克勒’们又死灰复燃,重新焕发出青春。” 然而,一旦这最后的“老克勒根据地”———宝庆路3号消失的话,这个圈子又会怎样呢? 本报记者发自上海 作者:苗润华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