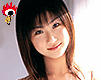中国应以平常心看待日本的重新崛起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10日22:44 新民周刊 | ||||||||
|
2004年10月18日下午2时,沈阳市育才外国语学校,“辽宁省第9届高中生日语大赛”正在紧张地进行。 比赛进入到自由问答阶段,一位评委即兴问道:“如果让你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架一座桥,你会把这座桥架在哪里?”
一个女孩抬起双眸,纯真的脸上挂着阳光般的微笑。 “我会把这座桥架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里”,她朗朗答道。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不解之怨 历史上曾经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和屡次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对日本国民心态最为复杂的两个国家。由于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曾饱受日本的欺凌、奴役和压迫,不断地签订各种战败割地赔款条约,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两国人民的心灵深处都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曾有过长达17年(1972-1989)的蜜月期,但在此后的10多年里,虽然两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在不断地增多,但彼此之间深层的心理情感芥蒂却开始日益加深。 2003年,中日双方的贸易总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达到了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高峰,但与此同时,双方舆论的恶化以及国民间心理上的不信任和互相蔑视,也达到了近30多年来的顶点。国内互联网上几乎涉及日本的任何一条新闻,都会招致网民们铺天盖地的嘲讽、谴责和怒骂,就连上海至北京高速铁路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这样的商业竞争,也招来海内外万名华人签名上书反对。 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最弄不明白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恨日本?”甚至在中国前任总理朱镕基访日时,一位日本记者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谢罪多少次才能令中国满意? 其实,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心理芥蒂,正是起缘于两国人民对当年日本侵华战争认识的差异。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二战期间在亚洲的暴行,与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主义绝无二致。但二战结束后,德国全民忏悔,特别是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出访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令人心颤的一跪,在让整个世界为之动容的同时,也让同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忿忿不平的感觉——日本从未对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进行过认真的反省。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更是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把参拜首次变成政府行为。而从2001-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先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宣布以后“每年参拜一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认为,中日之间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绝不是一个主观认识上的问题,而是有其深刻的背景。日本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选择的一个战略就是推翻二战结论,目前日本主流执政势力认为,如果二战结论不推翻就不会有日本的重新崛起。 “这是中国不能容许的,二战结论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如果任其发展而中国什么反应都没有,那有他们的崛起就没有我们的崛起,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永远也起不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零和游戏。” 此外,金熙德说,90年代以后,日本的和平主义退潮,年轻一代从未受过正确的历史教育,他们对二战历史的无知是惊人的。他们认为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太小气,是造谣,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仅仅是表明了最低限度的立场而已。 “在日本,这样的舆论已经做成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他的《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中指出,日本首相屡屡置亚洲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愤怒与抗议不顾,坚持把参拜变为年度参拜的惯例,有其利益所在。李培林对此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一是“选票说”。这是日本媒体最通常的解释,例如说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履行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对“日本遗族会”和“军恩联”的约定,是为了在参议院选举中确保靖国神社参拜派的选票。据说参拜派票过去有100多万票,但随着参拜派的高龄化,如今剩下不到50万票。 二是“新民族主义说”。很多中国和韩国的学者以及舆论多持这种看法,即认为日本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政府和民间都在寻找新的精神支柱,有别于旧的“军国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且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基础,政府也有意迎合这种情绪。 三是“政绩形象说”。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坛更迭频繁,首相走马灯似的换,一直都缺少一个铁腕型的首相。日本民众对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和“日本沉没”的忧虑,使小泉敢作敢言的形象深得人心。小泉试图在民众中维持一个“普京”式的强势首相的形象,他绕开涉及既得利益太深的痛苦改革,以安全战略为突破口重振民心,希望树立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相当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小泉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 四是“社会换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一代,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各方面的中坚,他们没有邻国同龄人那种从父辈接受的对战争苦难的深刻记忆,也没有对战争带来的自身灾难的恐惧,他们有的是对自己国家强大经济地位的自豪与优越感,对中国不断谴责和“厌日情绪”的增长感到厌烦和不满,他们希望日本能够确立新的国民自信和民族精神,摆脱战后国际社会给予日本的限制,成为一个所谓的“普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国际声望上,能够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下,参拜靖国神社涉及的显然就不只是50万张选票的事。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