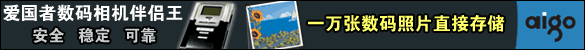南方周末:一群艾滋病感染者的幸福生活(3)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16日12:07 南方周末 | ||||||||
|
用我的爱温暖你 这是一个特殊的婚礼,在热闹和喜庆的背后,是辛酸而绝望的爱。两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用生死与共的承诺,温暖彼此的心灵。
“我任春立”,“我潘分玲”,“在此宣誓,我们愿意结为夫妻,从此患难携手,风雨同舟,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任春立的拳头一直紧握在胸前,仿佛这一生的誓言都握在拳头里。 这是在佑安医院爱心家园的红丝带下举行的婚礼。这是两个病人,两个艾滋病人。婚礼由佑安医院艾滋病爱心家园和艾滋病支持组织红树林主办。为一对艾滋病人举办婚礼对于在场的所有人来说都是第一次,也都是难以忘怀的记忆。 潘分玲,这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第一次坐了花车,并在长安街绕行一周,第一次有人帮她盘了新娘发髻。她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她的眼泪也一直含在眼里,这一切对她来说都像梦一样。 几个月前,任春立找到了她。 任春立出生在豫东边缘的一个贫困农村,他小学五年的学费都是母亲卖血换来的。看到妈妈因卖血而浮肿的胳膊时,他不愿意读书了。放假的时候他借了一辆自行车,偷偷地学骑车,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学会骑车后想跑到工地干活,结果人家嫌他太小不要他,于是他就开始卖冰棍,也卖了两次血。 2002年任春立在上海打工,开始不断地发烧,吃药,打针都不管用。家乡已经有不少人因为这个病死了,当任春立的母亲听说儿子的情况后,心里明白了:肯定是那病。 “我什么目标也没了,什么也不想了。”任春立说。 直到他在佑安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听说了一件事。和他同县的一个女子,因为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毒,丈夫就不要她了。 “他不要我要!”任春立当时就这么说,“我也是这个病,当时我身体还好,如果她愿意,我愿意照顾她以后的生活。” 或许是从心里需要一个人扶持,任春立选择了扶持他人的方式来扶持自己。 任春立找到了潘分玲。 他找到她的时候,她一只眼睛快要失明了。到他们结婚的时候,她那只眼睛完全失明了。 婚礼之后,任春立带她回了自己的老家。他们在河边的空地上,开了一点地,种上了果树。每天任春立走在前面,潘分玲跟在后面,任春立扛着锄头,潘分玲挎着篮子,任春立在地里刨,潘分玲就把刨出的东西捡进篮子里。 任春立从未结过婚,他对婚姻的憧憬一直是童话式的,在他所受不多的教育中,给他留下最大印象的是童年借到的皱巴巴的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和王子的故事。他记着一句话:“公主和王子结了婚,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纪录片的结尾,任春立对着镜头说:“我们不是王子和公主,但是我们也在幸福地生活着,并且会继续幸福地生活下去。” 想等到春暖花开天地轮回 只有两种结局,大败或者大成。因为怕大败,所以不敢说。慢慢地等吧,等到哪一天突然春暖花开天地轮回。 李想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是一个叙说者——这部片子的制片人,也是他所叙说的故事里的主角,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艾滋病人。 但在片子里他没有讲他的爱情,后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他的爱情是一种暗伤——无法说出的内心隐痛。在中国有100多万艾滋病毒感染者,但是他知道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人公开结婚的确非常的少。 “我知道的不超过5对,如果两个感染者结婚人们可能还能接受,但如果一个感染者和一个健康者的婚姻或者恋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是最后能走到一起,也是千难万险。”(本报2002年11月21日曾报道过贵阳市一个非感染者与HIV感染者结婚的故事)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婚姻爱情虽然是个人私事,但它却是几十万人的个人私事。” 李想所说的正是他所经历的。 曾经他拥有一个美好的爱情,现实粉碎了它。“我感觉我们之间相差太大了,根本不可能。” 这个差距就是艾滋病。8年前它把正在编织美好的人生梦的李想打入了谷底。当时的李想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未来的人,而姑娘的事业前途都处于上升阶段,这就是他们的差距。“我感觉身上非常地冷,全身止不住地哆嗦,眼前一片模糊,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为什么上天对我如此不公,如此苛刻,我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毁于一旦,我所有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对事业对爱情的憧憬,才刚刚开始,而我竟然感染了艾滋病。” “我无法想象当我说出真相时她的表情,事实是我根本就说不出口,但如果我们继续交往下去,我又无法隐瞒。” 于是李想选择了分手。李想称作“小玉”的那个姑娘,始终没有搞清楚李想为什么要离开她,也没有把艾滋病和李想联系在一起。当然李想和她交往的时候也不叫李想,李想是世界上的一个人和艾滋病毒有联系时的名字。 李想说,分手多年以后,有一次偶然见面,他发现这个姑娘还爱着他,也一直在寻找他。 李想感染艾滋病毒的时候只有19岁,现在他27岁。发现感染后他从大学退了学,想留在北京。因为北京有个佑安医院,病了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看看病,心里感觉有依靠。后来他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到医院治疗,最长的时间,李想有两个月没找到工作,每天只吃一袋方便面,每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护士就把自己的饭用微波炉热一下,谎称是吃不了的给他吃。“渐渐地,身体好多了,还有医生、护士的关爱,心情也好多了,我在北京开始了第二次人生。” “从300多块钱,到后来就是2000年之前吧,我工资大概就是四五千块了,我也没有什么文凭,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我觉得也算是比较不错的吧,现在我自己租了房子,有了一个很喜欢的工作,每天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 “我并没有奢望什么,只是想过回普通人的生活,我没有奢望天平向我们这一边倾斜,只是希望天平不要总是倒向另一边。”李想说。 李想主持了红树林组织的工作,这是给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帮助和支持的组织,鼓励别人比被别人鼓励更容易建立信心,李想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重建着自己的生活。 新的爱情就在这时到来了。他和那个姑娘的相识是因为两人共同关注着艾滋病。 “她是一个性情非常温婉善良的女孩,她长得不算太漂亮,但和她相处却总是让我很动心。”(李想让记者看电脑上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我是一个感染者,她爱的是艾滋病的我。”李想说。 “我追得也很有勇气,从不气馁呀。我觉得我很好,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甚至比有些人更好。我没觉得我比别人矮一头。人总要有信心有底气才能活下去,才能尝试着去梦想,才可以去追求。” 尽管如此,这也是一份沉重的甚至痛苦的爱——暗伤在心里。 李想和姑娘爱情只在极小的圈子里为人所知,他们维持了两年多的地下恋情。不能让她的父母知道,不能让所有的认识她的人知道。他们俩都爱得很艰难,有时候这让李想很焦虑很烦。 “让她父母知道了。只有两种结局,大败或者大成。因为怕大败,所以不敢说。慢慢地等吧,等到哪一天突然春暖花开天地轮回。” “她想嫁给我,我也想娶她。”但是他们却不能考虑将来。爱也许不会变,但很多东西是变的,它们会磨损甚至摧残爱,这是李想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艾滋病毒感染者来说,头等的问题是治疗和经济来源,我如果想要未来,就得有一个好的身体状况,那就得吃药,但药太贵了,现在的情况是生活还能维持,吃药就很难,而不吃药就可能在几年或更短的时间垮掉。前途有很多不可测的东西,这些东西我没有能力去把握。” 李想说。 很爱她却不能给她一个承诺,很想和她相伴终身,但却不能给她一个确定的未来。当你不能把握未来的时候,幸福也是不确定的。 “我家只有一扇朝北的窗,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太阳将要落下去的时候,阳光才会在我的阳台逗留片刻,可是我还是在上面种了一些花草。” 在片子的最后,李想这样说。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