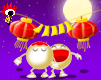马骅和他的后继者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16日18:13 新民周刊 | ||||||||
|
公派的志愿者和诗人昔日的身影在此重叠,应该允许追问,他们的灵魂是否同样经得起卡瓦格博峰的凝视。 撰稿/李宗陶记者 一个和八个
三支细细的、缠绕着经幡的竹竿在风中猎猎作响。它们站立在土石路的边缘,周围没有一星半点注解它们之所以在此站立的文字。即便是在事发半年后的2005年1月,云南省德钦县明永村的藏民依然会告诉每一个路人,这是马骅落水的地方。 冬日的澜沧江像群山陡然变细的腰,温顺地流淌,全无六七月间涨潮时的嚣张。此处的江风却是出奇的狂野,将人吹透不算,还刮得山上的小石头纷纷落下,提示着滑坡的可能。 周文斌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他眯起眼,向下望了望江水,有片刻的神凝。在过去的5个多月里,这个24岁的年轻人站在马骅上过课的讲台前,教马骅没教完的学生,用的,是马骅留下来的粉笔。 他的宿舍与马骅当时住的只隔着一间小屋;他会哼唱的那支《明永村》是马骅编的;他常常遛达的校舍前面的那块篮球场,是马骅用积蓄和化缘所得建起来的;还有他每天要去的,操场左前方马骅盖起的厕所……甚至于他之所以来到这个与上海相隔三千多公里的地方,都与那个叫马骅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文斌已经会对每月至少一批来到雪山脚下的记者这样说:“我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可比性,无论从年龄上还是经历上。”客观存在的分野也许还在起点上:周文斌是团中央“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第二批志愿者之一,与他同到迪庆的是上海团市委“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第七批中的六位医生和一位税务工作者——共八个上海人;而马骅,是通过朋友介绍自己来的。 马骅的大学同学、好朋友韩博说,在马骅准备去云南教书之前,他对几乎所有的朋友都隐瞒了实情,只是说想花上一段时间周游世界。马骅的复旦校友兼诗友天骄则告诉记者,马骅厌恶一切矫情的东西,在说和做之间,他选择后者。 “我们非常需要一位老师像马骅” 明永村坐落在滇藏交界处、梅里雪山脚下的巨大峡谷中,隶属于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云岭乡。梅里雪山是藏民心中的神山,共十三峰,最高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至今无人登顶。1991年1月,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在卡瓦格博峰下遭遇雪崩,全军覆没。 雪山冰川引人,但要到达明永村实属不易。天气好的话,从迪庆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县到德钦县城须在蜿蜒山路上颠行八九个小时,从德钦县城到明永村还有一个多小时更危险的山路。记者此行的一路上,藏族司机农布扎西在每一个“发卡弯”(180度转弯)的身手令人叹为观止。 马骅在给朋友的信中,对这段路有过描述:“有的路段全是山上滑下的碎石子,脚下一不小心就有掉到澜沧江漂至越南的危险”,而且“到夏天,雨季时,公路太容易塌方,不但麻烦,而且危险”。 周文斌已听过无数遍发生在这个地点的事故,先是媒体说,接着他周围的上海人说,最后是听当地人说。有意无意间,命运推着他向这个地点靠近,向真实靠近: 2004年6月20日19:30左右,在明永村小学志愿任教的诗人马骅在明永冰川景区公路距澜沧江桥约300米处不幸遇难。他搭乘的吉普车(车牌号为云R05069)不慎翻入澜沧江,随即被激流卷走。司机是景区门票办主任阿柱,他被抛出车外,摔成重伤。同车的还有一位搭车的女尼,年过七旬的卓玛,与马骅一起被江水吞没。据生还的司机说,马骅出村是为联系村里开通互联网的事。 农布扎西告诉我,当时搜救范围已延伸至下游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临沧地区等沿江县乡,晚上都有人在江边守着。尸体倒也曾浮上来几具,可就是没有马骅。 马骅的藏族朋友斯那伦布说,如果没有这次意外,除了明永村人和马骅的几个朋友,谁也不会知道有个从北京来的都市青年在深山僻壤的藏族村落里,箪食瓢饮地生活了16个月;谁也不知道他给这个52户、360人的村庄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纷纷扬扬报道中,明永村进入媒体视线。村长达扎西一句“我们非常需要一位像马骅这样的老师”见了报,且一路从德钦县经州团委传递到上海团市委,于是第七批志愿者的招募中定下了一位“马骅的接力者”。家住上海普陀区的一对普通工人夫妇偶然看到了招募广告,就问儿子周文斌“愿不愿意去试试”。 上海团市委宣传部的胡倩立告诉记者,原本选拔的是一位女同志,可云南方面一再强调,“我们这里很苦,务必派个男的”。 2004年7月16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本科毕业生周文斌乘坐K79次列车,先到昆明,再辗转两日,到达明永村,途中经过4290米的垭口时,他出现了高原反应。安顿、家访,从组织到组织少不了见许多人。9月20日,他走上了马骅站过的讲台。 这个讲台也就是学生用的课桌,这间教室也就是两个周文斌的宿舍大小。教室在一楼,宿舍在二楼。教室里的主要元素是一块被粉笔灰浸润得发白的黑板和一枚白炽灯泡,此外密密排着六七张课桌。已经放寒假,没有学生在,我拿起粉笔在黑板前站了会儿,想象着马骅、还有周文斌面对底下若干张“有点鲜艳,有点脏”的小脸的情形(“十二张黑红的脸,熟悉得就像今后的日子:有点鲜艳,有点脏”——马骅组诗《雪山短歌》之《乡村教师》)。我见过一张长头发、穿格子衬衣的马骅给学生上课的照片,黑板上写着“你叫什么名字”。 现在的明永村小学设有一、三两个年级,共八名学生。马骅教过的那批学生里,有几个已从四年级毕业,转到西当村的完全小学去了。周文斌第一天上课时,觉得三年级的“底子打得很好,上课很轻松”,但一年级新生却因为听不懂普通话,一节课40分钟只教了a、o、e三个拼音字母。据说马骅刚来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苦恼。 周文斌觉得当地的孩子很聪明,但接受能力不及外面,因为他们的知识面比较窄,与外界的接触一是通过来雪山的各色游客,二是跟着父母看电视连续剧。而他们的父母,大多希望孩子从事与旅游相关的服务业,譬如为坐在骡背上登冰川的游客牵牵坐骑,如果能学几句对付外国游客的英语,也好。马骅最初与村民的交流也是从开办“英语班”开始的。 当地村民对教育的淡漠由来已久,周文斌叹口气说,“许多事很难靠我们的力量来改变。”但他记得马骅说过:“只要还有一个学生在听,我就会讲下去。” 这幢两层校舍是纳西族样式的木楼,顶上插杆红旗,以与民居区别。没有校门,也没有卫生设施。负责接收上海志愿者的迪庆州团委书记李毅龙告诉我,马骅来了以后,搭建了男女厕所;得到村长达扎西分配给小学的一台太阳能热水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送给村里几台)后,马骅带领学生到河边和山上背石头,要了些水泥,买了些青砖,花了两星期盖了男女两间洗澡室,藏族学生冰河于是有了那次体验:“温暖的水从水管里流到我的身上,我都能闻出来里面太阳的味道。”这台理想主义的热水器很快就没法用了,马骅和周文斌都选择两周去一次德钦县城洗澡,它现在就躺在小楼前的空地上。 周文斌的宿舍站进三个人就难以转身了。一顶蚊帐、两张木桌,陈陋逼仄。一个多月前,州团委送来一台电视机,填补了“上海来的志愿者的文化生活”。周文斌在同校教师仁钦家搭伙,马骅原先用的厨房在他刚到时候被布置成一个灵堂,每日有藏民前来上香,周文斌对马骅在当地人心中分量的感知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马骅宿舍的木门上挂着把小锁,据说,从天津赶来的哥哥马捷收拾完遗物后再也没人打开过。透过薄薄的窗帘,可以看到桌上还有一枚打火机和一瓶橘子汁。打火机大约是用来点“中南海”香烟的,在最穷的时候,马骅曾写信给朋友说“没烟抽了”;橘子汁让人想起开客栈的阿亚提起的那一幕:“2003年的儿童节,马老师带着村里的小孩去爬明永冰川,下山时太阳很毒,马老师在我家对面的小卖部买了一瓶很大的‘奥得利’饮料,让孩子们轮流喝,孩子们喝了一圈后,他一点也不嫌弃,接过瓶子大口大口地喝。”阿亚说,“一些小孩流着长长的绿鼻涕,可能他家大人都会嫌弃。当时我和附近的几个村民看到了,都说,像这种事我们村民都做不到。” 类似的事情还有,马骅和城里来的朋友在阿亚店里吃饭,苍蝇乱飞,爬满杯子。城里朋友不停地赶苍蝇,马骅好像没看见,拿起杯子就喝。阿亚说,马骅来了一年多,他们总共说过不到三句话,可他打心眼里敬佩这个“纯白、不假模假样”的城里人。 为什么“志愿” 如同希区柯克电影《蝴蝶梦》中的丽贝卡于新女主人“我”一样,马骅是周文斌的一个悬念。后者应该受到足够的暗示去感知前者的一切。坐在仁钦客栈二楼的平台上,周文斌告诉我:“他(马骅)原来是北大在线的经理,收入是五位数的。他是对藏文化感兴趣,通过北京的朋友朱靖江、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郭净和德钦县旅游局办公室主任扎西尼玛,一层一层联系到这个村子,想潜心做研究,顺便为当地人做点事情。” 扎西尼玛是明永村人,当他告诉村长“有个名牌大学生想来我们这里教书,还不要报酬”时,达扎西乐坏了,可冷静一想,不可能,“没想到,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时,嘿嘿,他真的来了!” “他个头很高,留着一头长发,看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跟村里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达扎西第一眼见到马骅时,无论如何也难把他和“一个支教志愿者”联系起来。“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当时的表情很平常,没有一点点能让我想得起来的地方,他的回答我也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帮助一下这里的孩子们。” 谁也不知道马骅为什么“志愿”了一把,因为他从没有对此说过什么。最早发现这个“支教典型”的迪庆州电视台的记者曾经扛着摄像机赶到这里,仁钦老师回忆说:“我从没见过这么躲避采访的人。记者来明永村,他就跑到德钦县,记者追到德钦县,他又回到明永村。后来,记者终于在他下课时堵住他了,我想,他总该说些什么了吧。没想到,记者问了他一堆问题,他要么不说话,要么应付一两句。”仁钦还记得,记者笑眯眯地问他这么年轻来免费支教,以后老了怎么办,有什么打算等等,可他却说没想过,没什么打算。“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搭理记者,他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在司机农布扎西口中,马骅躲避镜头是用整条胳膊来遮脸的。 马骅前同事、北大外语教师胡旭东说,“三十岁以后,我们都被不知不觉纳入生活的轨道。只有马骅,他可以把外面世界的规则玩得很好,内心却一直在坚守自己的规则。” 引荐马骅来明永村的北京朋友朱靖江说得比较明白:“他就是想过一段纯朴自然的日子,让内心宁静下来。” 韩博说,马骅到了明永村之后,确实踏踏实实地生活下来,耐心做好一个乡村教师该做的一切。与此同时,潜心研究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地文化,为当地做了很多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撰写了若干文章。马骅本来打算在2004年夏天学期结束之后,去附近旅行,拍摄一些资料性的幻灯片,然后结束在云南的生活,9月份就回到城市生活中。他的计划是选择一所学校的历史系,结合自己的积累,研究深造。云南,并不是他的终点,而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 诗人拉家渡则从马骅的作品中嗅出经受洗礼的意味:“马骅以前写诗还讲究语言技巧,可组诗《雪山短歌》褪去了先前的戏谑与沉痛,他现在的诗变得纯净而开阔。” 藏族诗人、藏人文化网总监旺秀才丹传来一些马骅过去和现在的诗作,我从中找到这样的诗行:“登高,再继续/登高。清点眼前丛生的/水泥柱,找一棵/属于自己的。/但那些水泥柱!那些/城市的坐标,从平地上/猛然跃起的钢筋/只是在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方向/锲起九月的午后。……”在这首《山楼粉堞隐悲笳》的末尾,诗人说,“岁月无声地摧动着躯体深处的每一处暗疾。” 但你听《雪山组诗》中的《风》:“风从栎树叶与栎树叶之间的缝隙中穿过。/风从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开阔地上穿过。/风从星与星之间的波浪下穿过。/我从风与风之间穿过,打着手电/找着黑暗里的黑。”这些遗作收录在新近出版的《在变老之前远去》,这是马骅唯一的出版物。 当地人似乎也懂了。在距离小学不远处,有一座为马骅而建的白塔(藏文化中,为某人建白塔,意在为其超度、祈祷,视其为神圣而祭拜),是德钦县委、县政府在他出事三个月之后修建的。塔前立有一碑,上书“马骅,诗人、学者。1972年4月11日出生……”这个开头让许多熟悉他的人长舒了一口气。 至于周文斌为什么“志愿”,他在一句“这种历练对人有好处”之后,就不再说什么了。 他每天8:30起床,9:00上课。每天六节课,一、三年级的语文和思想品德。下午四五点放学后,看看书或电视,打发一下时间。周文斌觉得,这样的日子就像继续在大学里念书,而且更自由,只是周末不能回家罢了。他喜欢这里清静的日子,“如果工作压力大的话,来呆一两周会很好。”周文斌有个同校的女朋友,因为知道“也就一年,总要回去的”,倒也相安无事。他现在每个月拿600元工资,在当地用用,足够了。 马骅没有通过组织渠道领到过一分钱。李毅龙告诉我,他跟马骅接触后,很想帮助他做点什么,特别是为改善他的生活条件做些事情,一来苦于经费少,二来马骅没有组织关系,名不正,言不顺,只能作罢。记者在采访中隐约体会到,当地似乎更需要“有工作经验的、成熟”的支教人员。 两种“志愿者” 始于1998年的上海“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促生了180多名志愿者,医生占了三分之二。6年多来,他们在云南省红河、文山、思茅三个地州、18个市县留下短暂的痕迹,因为每一批为期半年。又由于接力,上海的志愿者得以源源不断地注入当地,驻沪企业的善举也细水长流,譬如安利(中国)公司,新近向香格里拉县西尼乡捐赠了当地急需的药品。 在去云南寻访第七批志愿者之前,记者在沪采访了第三批的刘江斌(上海儿科医院外科医生)、第五批的周文浩(儿科医院内科医生)。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们改变不了许多东西,但因为我们去了,确实给当地带来一些好的转变。”譬如先进医疗理念的输入,过硬手术技能的展示,外界信息的传递,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灌输。至于他们收获的,那些人与人之间触及内心的感受,则深深埋在他们心里。有一些,是无法言说的。 周文浩讲了一个故事:当地一个藏民,十年前治病欠了医院一笔钱,这些年他收入状况好些了,就来医院还钱,他说,慢慢还,有钱就来还。 这类在一些大城市已经罕见的行为和医患关系,也深印在现任迪庆州医院外科医生张念(原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医生)的脑海中。有时候,几个志愿者懒得做饭,结伴在小店对付一顿,结账时老板说,刚才有人帮你们付了。有时候在某个厕所门口,突然会被人拍拍肩膀,随后听到一句“多亏上次你给我开了刀”,对方的脸也许黑红,嘴里也许还带点酒气,但他们的笑却不浮,而是像高原的阳光那样扎实。当地人是真心感佩“上海来的医生”。 从情节上看,他们都是踩着马骅的足印来到这里的。张念结识的藏族朋友也问过他“为什么来这里”之类的问题,他也说不上来。他只是说着不用再随着“气场”跟人谈论房子、车子和位子,说着没事的时候可以跟当地朋友开辆吉普车去大草原上踢球,说着州医院里但凡有大手术都会来找他、听他的方案,说着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开心”。在这个阳光会将皮肤晒得很黑的地方,他觉得自己被需要,还没有别样的压迫感。听完这些,朋友点拨他:“哦,你是为了治疗自己过来的。”张念一想,觉得有点道理。他说半年真快,怎么就要回去了呢?如果不是老婆孩子在上海等他,他愿意留在这个地方。 公派的志愿者大多是共青团系统的积极分子,从他们身上,我确实捕捉到与马骅相近的、发自心灵的光芒。 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这光芒曾照亮诗人的归程: “7月10日下午5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作一团的20多个学生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茬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这是自由的、不羁的灵魂的诗性。也许,它也会在“轨道中人”平凡的瞬间感念里一闪而过。 上海第七批志愿者中唯一的女性是闵行区江川地段医院的内科医生符珺,今年26岁。她曾经跟队友赶了一天山路,到达距离明永村50多公里的另一个村子雨崩村。在那里,她认识了与马骅类似的“自己跑来”的昆明志愿支教者戴凌云,以及戴凌云的接班人、也是非公派的、从上海去的宁勇。在闭灯长谈的夜里,符珺有些难过地告诉我:“我觉得,他们一定从内心里看不起我们这种志愿者。”但她忽略了一个事实:公派或私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当地留下了什么,自己又收获了什么。除了治病救人的本分,符珺为德钦县建立了第一套居民健康档案,那是她花了两周时间挨家挨户跑出来的。在这个7000多人的县城里,已有700多人的健康状况有案可查…… 尾声 2005年的春节,钮骏(儿童医院)、许建中(九院)、顾磊(一妇婴)、蒋炜(中山医院)、祝军(南汇区国税局)以及周文斌、张念、符珺八人是在上海与家人、朋友共同渡过的。而马骅,长眠于神山脚下,过年的时候,当地人自会替他点上一盏酥油灯。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