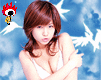死刑存废之争:制度改革应符合我国国情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19日16:29 法制早报 | ||||||||
|
李久明案、杜培武案、聂树斌案,一度在学术界引发过死刑存废之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问时指出,出于国情,中国不能够取消死刑,但将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这是对激荡一时的死刑存废之争最为权威的官方回答。
而刚刚被改判无罪的佘祥林案,一方面引发了媒体和社会关于冤案之源的反思,另一方面,也使不久前讨论激烈的死刑存废之争超出学术界范围,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再度升温。 没有了死刑的威慑作用,谁来为一个国家极端犯罪率的上升而负责(尽管这也许只是一种可能)?如果用长期刑代替死刑,那么,又有何理由让纳税人为监禁这些人的费用而买单? 谁能保证权力、金钱与关系不会扭曲正常的执法?如果废除死刑,谁能保证杀人者能够真正的处于被监禁状态而不是逍遥法外? 2005年1月16日,在“当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全国杰出青年刑法学家论坛上,就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提出的全面废除死刑观点,司法部副部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军表示,我国当前要重点解决的是改革刑罚制度,设立更多的20年、30年以上的长期刑,以此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 早在 2003年1月9日《南方周末》刊出《死刑:保留?废除?》一文引发的网络世界的死刑大讨论显示,与部分法学学者形成的限制并最终废除死刑的“精英共识”截然不同的是,在绝大多数网民看来,“杀人偿命”却是天经地义,对其他严重犯罪适用死刑也是罪有应得。 而2003年8月15日刘涌被二审改判死缓,媒体和舆论对法官、律师和学者的口诛笔伐,则再一次张显了公众对死刑的态度。而此后人民网所举办的网上调查中,截止到今年4月11日,有58.8%的人认为应“反对废除死刑,要加大刑罚力度。”而选择“立即全面废除死刑,尊重生存权”的只有9.6%。 中国历史上死刑存废之争 支持者:“刑为盛世所不尚,亦为盛世所不能废。” 反对者:杀人者死,不杀不足以平民 愤事实上,中国虽然一直存在死刑,但死刑与中国文化之间却有着一种微妙和矛盾的关系。 一方面,“法峻刑严”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历史上的各种严酷死刑贯穿着整个历史,中国刑法里有很多残酷的刑罚,“杀人者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但是中国法制的关于死刑运用的基本指导思想,也为中国国民的普遍民意。 另一方面,先秦时形成的“明德慎罚”思想,也有着对死刑的某种限制。孔子的“无讼”思想,则成为2000多年中国的主导性法律思想。“不教而杀谓之虐”,传统中国的刑事政策注重的是教化,讲的是正风俗,饬人心,即使有死刑也是以杀止杀,以刑去刑,以达到无刑为目的。 所以,古代对盛世的最高评价就是“近于刑措”。意思是很少处决犯人,死刑基本上用不着。比如文景之治,比如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但死刑却又是保持“刑措”的必要条件,正如清人之所言:“刑为盛世所不尚,亦为盛世所不能废。”如果人们和睦相处,连刑罚都用不着,何况死刑? 中国最早思考死刑的人是沈家本先生。他在清末主持修订法律时,深悉“废止死刑之说,今喧腾于世,而终未能一律实行者,政教之关系也”。 鉴于中国当时的“国情”,他只就死刑统一划一的可能性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际推动。由于他的努力,中国法定的死刑终于由常法中的两种(斩与绞)统一为一种,死刑执刑处也从公开场所转入监狱内。 二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民国司法界也有关于死刑存废之争,但由于中国政治的动荡局面,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而真正形成风气的讨论是在90年代以后,主要是一些鼓吹废除死刑的“精英学者”。 同时,中国也不具备废除死刑的人文语境与民意基础。西方废除死刑大多有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贝卡利亚则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石。而中国一般民众和政治家们很难接受那种笼统的认为废除死刑为的是保护人权的说法。无论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基于多么人道的考虑,在中国这个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下,都很容易被理解为只保护罪犯的人权,不保护被害人的人权。一次又一次的“民愤”,正是反对废除死刑汹涌的民意之潮。 西方死刑:从达米安到《论犯罪与刑罚》 著名的达米安案是西方酷刑的最好诠释 1764年贝卡里亚发表《论犯罪与刑罚》,首先向死刑制度挑战 当代废除死刑的大多是西方国家,但是西方历史上死刑的残酷程度毫不逊于中国。著名的达米安案便是西方酷刑的最好诠释。1757年3月2日,法国人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死刑,他要被“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但实际上的执行却非常困难,“因为役马不习惯硬拽,于是改用6匹马来代替4匹马”。 在屠杀自己的同类上,人们穷尽了智慧,各种各样的死刑匪夷所思。水刑、活埋、凌迟、吊死、割乳、碎身、火刑、尖刀刑、沸油刑……等等数百种。而且,我们千万不要头脑简单了,每一种死刑都有很多花样与技巧,其目的就是给受刑者最大的痛苦。 如果读者有暇,可参阅法国人莫内斯蒂埃的《人类死刑大观》。说实话,作者对他的欧洲祖先还是留了情面了。在古代与中世纪的欧洲,攻城略地杀人盈城,宗教狂热更是充满血腥与屠戮,即使在近当代“文明的”欧美也不能说没有野蛮。 18世纪,在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了以贝卡里亚和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个人理性和尊重人权以及自然法合理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社会意识,对死刑、拷问制度以有力冲击,从而提出了废除死刑的刑罚论点,以法国革命为转折点,刑罚制度的宽容化和死刑的废除运动日臻普遍化、立法化。1764年贝卡里亚发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首先向死刑制度挑战。从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死刑存废之争,人们从法律、伦理、道德、功利等等各个角度对死刑存废进行了论证。这种争论在丰富刑事政策内涵、唤醒人类对死刑制度的理性思考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各国限制和废除死刑的步伐。 死刑存废 现实需要与理想期望 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3条提出人人享有生命权,第5条禁止使用酷刑 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从制度上或者实际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总数达到111个,而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总数则为84个。 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下,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3条提出人人享有生命权,第5条禁止使用酷刑;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则提出废除死刑。1989年经联合国大会决议对此予以重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1997年4月3日的 1997/12号决议敦请所有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从完全废除死刑着眼,考虑暂停处决。 在1997年关于废除死刑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大赦国际发表《斯德哥尔摩宣言》。该宣言总结了废除死刑的原因:死刑是根本残忍的、不人道的与有辱人格的刑罚,且侵犯生命权;死刑经常被用作镇压敌对的、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与低下阶层的群体的手段;死刑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易于引起暴力:死刑的适用对于卷入该过程中的所有人都是残酷无情的:死刑根本没有被表明具有一种特殊的威吓作用;死刑越来越采取原因不明的失踪、法外处决和政治谋杀的形式;死刑是无法纠正的,而且可能被适用于无辜的人。概而言之,无非两条:死刑是不人道的,死刑是没有用的。 然而老百姓却并不领受这些良法美意,他们用选票与游行来抗议政府和议会对死刑的废除,并且至今仍然强烈要求恢复死刑。 事实上,死刑制度产生以来,通过对最极端犯罪的道义报应满足了深藏于集体意识中的正义情感。而集体意识、正义情感对死刑的广泛的公众认同,又使死刑制度获得了凛然于所有的功利性追求之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强大的民意基础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死刑对犯罪的威慑作用。 1949年德国制定基本法时,民众支持死刑的比例远远超过反对死刑的比例。法国于1981年正式废除死刑,但过程几经曲折。特别是1976年发生的帕特尼克·亨利绑架杀人案曾使公众对死刑的认同和支持达到顶点,公众、政客与新闻媒体几乎众口一词地反对废除死刑。直到2001年,希望恢复死刑的民众才不足50%。在英国,政府于1965年推动国会废除对谋杀罪适用死刑时,只有20%的人赞成废除死刑。即使在已经废除死刑的1966年,仍然有高达85%的民众支持对谋杀罪适用死刑。在舆论压力之下,英国议会直到1998年才彻底废除了国事罪中的死刑。在意大利,也有一半左右的民众希望恢复死刑。另外诸如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人口在 1亿以上的大国,均未从制度上完全废除死刑。 中国当代死刑存废之争 全面废止死刑而替代的方法则是设立长期刑 是不是发达国家有的我们都要有,这是学习先进还是邯郸学步? 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认为,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而替代的方法则是设立长期刑。 然而持不同意见的人民大学谢望原教授则认为,废除死刑是不是历史的趋势很难说,因为各国的法律制度及历史习惯是不同的。 即便如此,废除死刑论者的观点也要经受许多其它质疑:是不是发达国家有的我们都要有,这是学习先进还是邯郸学步?与国际接轨是不是就一定要去模仿与拷贝?如果可以基于人道而考虑杀人者的人权,那么谁来考虑被杀者的人权,谁来考虑被杀者亲人的感受? 人们反对废除死刑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深奥的哲理基础,而毋宁是出于最为现实的考量:自保!在当前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制度并不完善、司法腐败甚为严重的情况下,谁能保证权力、金钱以及人际关系不会扭曲正常的执法?如果废除死刑,谁能保证杀人者能够真正的处于被监禁状态而不是逍遥法外? 事实上,的确有些人服刑时竟然能够自由进出监狱,甚至再次犯案。而一些弱势者在监狱里却连合法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杀妻冤案”中的佘祥林,视力在监狱里给弄坏了,一截手指头也丢在了监狱。如果不健全监狱制度及监狱设施,不能够给在押犯人以“人道”待遇,废除死刑又怎称得上“人道”? 事实上,今天中国法学界主张废除死刑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类似聂树斌、佘祥林等冤假错案的存在。但只要分析就可以发现,每一起冤案里都有刑讯逼供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防止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严格履行罪行法定、无罪推定等原则,严格履行法定程序,严格证据制度以及死刑复核程序,我们就能够有效地杜绝聂树斌类冤案的发生。 因此,正如总理所言,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而非因噎废食,草率地将死刑制度“判处死刑”。一句话,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保持死刑制度的正当运作。 废除死刑标志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没有了死刑的威慑作用,谁来为一个国家极端犯罪率的上升而负责 尽管如此,欧洲各国的政治家们仍然不懈地致力于推动全面废止死刑。而且,由于欧美各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废除死刑甚至成了区别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保护人权与践踏人权的分野之一。 然而,问题却绝不能到此为止:能否因废除死刑的大多为西方发达国家,就说废除死刑标志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没有了死刑的威慑作用,谁来为一个国家极端犯罪率的上升而负责(尽管这也许只是一种可能)?如果用长期刑代替死刑,那么又有何理由让纳税人为监禁这些人的费用而买单? 在法治还不健全的国家,死刑的废除如何能够保证公权力者不会更为暴虐地欺凌百姓贪污腐化?由于司法腐败、执法不公等因素的存在,谁能保证所有罪犯能够得到公平对待,而不会出现有权有势者坐牢像住宾馆而弱势者被监禁时合法权利被侵害呢? 一句话,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传统,甚至人口数量各不相同的国家,废除死刑能否一刀切呢?不回答这些问题,死刑的存废就不可能从现实达致梦想! 支振锋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