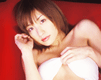通讯:见证爱泼斯坦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3日22:36 新华网 | ||||||||
|
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见证中国 写作一生 新华网北京6月3日电 通讯:见证爱泼斯坦 记者 吴晶
他在波兰出生,从一个无国籍的犹太人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他在中国成长,从一个高中毕业生最终成为影响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他见证半个世纪的中国,新中国历代领导人都与他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他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却从未动摇过对中国深沉的热爱和信赖;他永远示人以和善的微笑,周围的人们却敬畏他在工作中的完美主义。 他就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不同年龄的人都用中文昵称他“艾培”。 5月26日,爱泼斯坦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很多朋友都到他的家中悼念。他的书房里摆满了各界人士送的花圈;他的书桌上,还放着他没有来得及看的报纸;他的轮椅上,仍旧铺着洗得有些泛白的小花毯。他的夫人黄浣碧,不停地接听来自海内外的慰问电话。 与“艾培”共事50多年的原《今日中国》杂志社第一副总编辑张彦难以掩饰内心的悲痛。他说:艾培虽然长着大鼻子,蓝眼睛,可是他的思想感情是一个很淳朴的中国人。他亲眼目睹中国的历史、亲身经历过中国的灾难。他与中国同甘共苦,也受过很多的委屈,但却始终无怨无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爱泼斯坦于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华沙,两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为爱泼斯坦翻译众多著作的翻译家沈苏儒说,艾培曾多次讲起幼年时在天津租界看到的中国儿童被欺侮而上前打抱不平的事。他说过:我是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大的。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不喜欢民族压迫和歧视,”爱泼斯坦说:“我的父母教育我要反对歧视,不管这种歧视是针对我们,还是任何别人。” “儿时经历使他从心底同情中国人,后来投身到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和侵略的革命中,最终他自己也成为中国人,”沈苏儒说。 为中国革命创造“四个第一” 15岁的爱泼斯坦跨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他的新闻生涯,并因此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埃德加·斯诺,并加入了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的行列,参与了对“一二·九”运动南下请愿学生的接待、安置活动。斯诺震惊中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也照亮了爱泼斯坦的眼睛。他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真实地记下了卢沟桥事件的第一声枪响、天津争夺战的激烈悲壮、南京武汉政治军事事态的发展、台儿庄战役鼓舞人心的胜利,直至广州沦陷时的情景。在战火硝烟和残破不堪的中华大地上,爱泼斯坦冒死写出了26万字的新闻作品《人民之战》,用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呈现了中国普通军民抗战救亡的英勇和意志。 “是什么使您留在了中国?”1995年,有人这样问时年80岁的爱泼斯坦。 “是中国革命。”老人回答。 沈苏儒说,艾培一生为中国革命创下四个第一: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爱泼斯坦,为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英文定稿并将其广泛传播到海外;1944年,经他改写,新华社在延安窑洞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从此,世界开始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同年,爱泼斯坦与叶君健合作,第一次将冼星海写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译成英文,为很多国际友人广泛传唱;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在爱泼斯坦等进步人士的推动下,美国《远东之光》刊物出现了五星红旗的照片,这是美国第一份印有新中国国旗的出版物。 因为走在中国革命的最前沿,爱泼斯坦的一生与中国领导人结下不解之缘。他冲破国民党政府对敌后根据地长达5年的封锁,在延安窑洞里采访了毛泽东,结识了朱德、贺龙,写下了一批生动详实的报道,使外界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感受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 半个世纪过去了,爱泼斯坦的客厅里一直高挂着他离开延安时,毛泽东送给他的签名画像。黄浣碧说,艾培一直珍藏着在延安的采访笔记和照片。照片上年轻的爱泼斯坦总是在笑,他对当地民众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以至当时同行的国民党代表团团长谢保樵生气地说:爱泼斯坦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了家。 “还有一样东西是艾培很少示人的,就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他在美国一家录音店里录下由他自己演唱的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黄浣碧说。 1951年,爱泼斯坦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创办中国第一本对外刊物《中国建设》,它就是如今用7种文字对外发行的《今日中国》。“这本刊物就像是艾培的亲生孩子,他读起来永远爱不释手,”《今日中国》杂志社社长宫喜祥说。 思想感情上一个朴素的中国人 “这时已是四月,路旁的树木和麦田刚显出一片嫩绿。我陶醉在这片熟悉的、稚嫩的、很快就会消失的色彩中……华北,这是我生长的地方,我所认识的唯一故乡……” 这是爱泼斯坦在临终前最后出版的回忆录《见证中国》的一段话。但是沈苏儒对记者谈起这段话时眼中却噙着泪水:“多么美的意境!要知道,这是他在文革期间被非法押送入狱时凝望吉普车外的大地时产生的啊!” 5年后,他从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出来,马上忘我地投入工作。这么多年,即使别人提起,他都没有一句抱怨。他对周围的人说:既然我们能够在一起拥抱胜利与欢乐,就应该在一起面对挫折与悲伤。 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的爱泼斯坦说:我走的是一条奇特道路,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对他说:您爱中国从而爱世界;您贡献于中国从而贡献于世界。 艾培总是把对国家的高度负责任,放在个人的考虑之上。1985年在他七十寿辰招待会上,他对前来道贺的邓小平说:是中国人民哺育了我,教育了我,并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八十大寿时,他对前来祝贺的领导人没有说客套的答谢辞,而是就如何做好中国的对外宣传提出建议;今年九十大寿时,他在答谢辞中谈的仍然是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爱老是个率真的人,他相信越是对人好,越要说真话。所以他总是在中国给予他荣誉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的赤子之情,”沈苏儒说。 对人世沧桑的追忆,爱泼斯坦的感觉总是“欣慰”:我去采访毛泽东,他也采访我,他说话很幽默,让人觉得轻松自在;而朱老总则根本看不出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头儿;还有周恩来,还有孙夫人…… 与艾培共事50多年的原《今日中国》杂志社第一副总编辑张彦说:艾培外表上是个十足的大鼻子洋人,可在感情上却是一个朴素的中国人。 完美主义者的事业追求 爱泼斯坦在《见证中国》中写道: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更加美好和更有意义。 在普通人眼里,总是微笑着的爱泼斯坦是一个朴素而平易近人的长者。“如果不看他写的书,没有人会想到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握过手,邓小平向他敬酒敬烟,连外国高层官员来中国都希望能和他见上一面,”宫喜祥说。 《今日中国》的年轻记者们都忘不了这位见面就与他们讲笑话、掰腕子的老人。他们也敬畏这位“挑剔”的老记者,因为稿子到了他的手上,不到最后印刷肯定要反复修改。为爱泼斯坦翻译著作的沈苏儒干脆和他达成君子协定:在他每本书的中文版译者后记里可以注明,中、英文版本的不一致是爱泼斯坦对定本再度修改造成的。 为了写《宋庆龄传》,爱泼斯坦用了10年,仅中英文注释就有850多条。“书中凡是宋庆龄的直接引语,没有一句不出于她的口或笔”;为了写《西藏的转变》,他又用了30年,第三次进藏时已年逾六旬,三次采访笔记逾百万字。 张彦说:“我和爱老好象永远都在谈工作,他关心中国的市场经济、农民生活的改善,也关心改革开放的进程。他最放不下的就是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 沈苏儒说:“没有看他下过棋,也没听说他和谁打桥牌。他一年唯一的消遣就是去北戴河游泳,因为他的童年在海边长大。” 夫人黄浣碧说:戒烟以后,精益求精就是艾培唯一的嗜好。 与艾培并肩走过半生的人们坐在一起,重拾往事。黄浣碧说:“他是个重感情的人,保留着很多前妻邱茉莉收藏的中国古董。他对收养的两个中国孩子更是视如己出,一有闲暇也爱摆弄孙儿的玩具。” 他的儿女说,父亲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爱戴,他的一生应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在一个月前,爱泼斯坦在人民大会堂度过了他的90寿辰。他说:和过去一样,前进道路上还会有很多阻碍和磕绊,可是中国的进步将会继续。 爱泼斯坦毕一生之精力见证中国、并投身中国的解放和进步;他对中国的热爱和贡献也被中国人见证,被历史见证。(完)(责任编辑:张守生)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