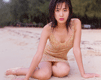社会周刊·中国西部禁毒调查报告(下)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6日10:15 工人日报天讯在线 | ||||||||
|
镜头三:草原毒姐妹 在去看守所的路上,我问缉毒大队长周军,这些年,在办过的所有贩毒案件中,哪个毒贩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周军脱口而出:红英呗!
我问:为什么惟独记住了她? 周队长苦笑着说:待会儿,你自己到看守所去见过她之后,感受就来了。典型的靠贩毒脱贫致富的农民。抓住她时,家里搜出两千多克毒品。你说还不该杀头吗? 从缉毒民警们嘴里描绘出的红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孩,一个从小失去了父亲,跟着母亲要饭长大的女孩,有一天嫁人了。当了妻子的她,很快也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母鸡的天性是把小鸡们庇护在自己的翅膀下,这个母亲也不例外,她不仅细心地照料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并且决心要把他们培养成才,培养成才的标准就是儿女们都要上大学。这个母亲的初衷是伟大的。然而,在饱受了贫穷的滋味后,在第一次贩毒意外地获取暴利之后,这位母亲为了自己神圣的目标,开始明目张胆地干起贩毒的勾当。七八年下来,她不仅让自己的小家走上小康之路,而且揽下抚养两个外甥女的重任,贩毒赚来的钱,还让她分别在本地和外乡盖起两座漂亮的小楼。 这个女人就是红英。我意识到,从现在起,我采访的每一个“重量级”毒贩,都是明天的死人了。有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红英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通往看守所的路显得有点漫长,因为这天包头市的上空弥漫着厚厚的沙尘,寒风依然包裹着这座草原城市。 在经历了两个多小时的等待之后,毒贩红英被批准与我见面。她已经被二审判处死刑,现在处于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阶段。 我和红英分别坐在两个屋子里,中间隔着一道钢筋栏杆的窗户。她的一只手臂被铐在钢筋栏杆上。她个头不高,身体瘦瘦的,颧骨很高,尖下巴,牙齿凸在唇外,弱不禁风的外表下透着凶相。整张脸上,眼睛十分有神,只不过不安分地带有一些狡猾的神情。她疑惑地看了我几眼,随即便问:你是哪来的?你要干什么? 我淡淡地回答:来看看你。 未等我的话说完,她的眼光顿时往我的身后扫去,原来,禁毒大队女教导员谢向丽不放心地跟进来了。红英愤怒地盯着眼前的女警官,首先发话道:“我认识你,你是《法在身边》节目的主持人,他们抓我那天,你也在场,你还打我了。”由于激动,她的身体几乎都挤贴在铁窗上,她伸出一只手臂,如果没有铁栏杆的话,她肯定要一把抓住女警官,撕了她。 谢教导员却微笑着一言不发。 《法在身边》是包头市电视台和市公安局联合举办的一个普法电视节目,谢教导员在工作之余兼做节目主持人。红英所以记住她,不是因为节目的原因,而是由于她参加了缉捕行动。 红英瞪着女警官,在喘粗气。 当听说我是北京来的,红英马上作出一副可怜相,说警察抓她的时候踢了她的脚,她的一条腿现在肌肉萎缩了,需要住院治疗。说着说着要动手脱裤子给我看,我急忙制止。她的表情变化很快,裤子还没系好,就抑扬顿挫地一句接一句地喊冤枉,让我给她做主。采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 问:你说你冤枉,冤在哪里? 答:我只卖了几克毒品,他们却说我卖了很多克,把我的家产全给没收了。我的房子不是毒资,是我的合法所得,做生意挣来的,他们为了立功,诬赖我有很多克海洛因。 红英几乎是用气声在说话,一副乞怜的样子。 我随意地问着:你们姐妹几人? 怕我听不清,她特意伸出三根手指答道:三个,我是老三。 我问:你身体怎么样? 红英马上诉说:有哮喘病。我的眼睛不好,近视,是有了孩子以后近视的。在进来之前,你知道我有多么胖吗?可是现在我瘦成这样。你去跟他们说说,给我弄点好吃的。我是个快死的人了,我得吃顿好饭。 我转移话题,问:听说你对母亲的感情很深? 红英现出痛苦的神情,说:母亲拉扯我们不容易。我爸死后,我跟着母亲要饭要了十几年。 问:听说你母亲总用一句话教导你们,还记得吗? 答:记得。三条路,走中间;做好人,结善缘。我母亲一辈子都是老实人。 问:可是你贩卖毒品,背叛了母亲的教导。 红英狡辩道:我只是做自己的生意,没有坑害别人。 我一字一顿地告诉她:你知道吗,一克海洛因,就可以让一个好端端的人成瘾,最后走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道路。你贩卖了多少克海洛因,就等于坑害了多少人,怎么能说没有坑害别人呢? 红英回避说:我不清楚。 我紧追不放地问:不清楚?不可能吧?就算你不清楚这些,那么起码你应该知道这是违法犯罪吧? 红英继续狡辩道:我真的不知道这是犯罪。我姐姐先被公安抓住之后,我才知道这是犯罪。 问:但是你姐姐出事之后,你依然在贩毒,这又怎么解释? 红英理直气壮地说:我为了筹钱救姐姐出来,我求人帮忙,对方说在省里找到了一个司法大官,可能是公安厅的副厅长,也可能是法院的副院长,说是可以救我姐姐出来,需要要钱,我只好把手里的货卖出去换成钱了。 问:你贩毒挣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答:我没有挣到钱。 问:那么你哪里来的钱买好几套楼房? 答:我做生意挣的,倒粮食、香烟、服装,还有卖树林就得了几万元。 问:你挺能干的,是你们家族的主心骨? 听到我的夸奖,红英顿时面露喜色,她把手心捂在胸口,用神秘的口吻对我悄悄道:你知道吗?我死了不要紧,可是,我的一对儿女都有出息了,他们都上大学了。 说着,红英哈哈大笑起来。 我问:他们都在读什么大学? 红英得意地回答:一个要当检察官了,一个要当医生了…… 突然,红英吐了一下舌头,自知说漏了嘴,会影响孩子的前程,她马上又摆摆手自言自语:不能说,不能说,说了我儿子就完了。 正在这时,禁毒大队队长周军进来了。一见周军,红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冲动,她厉声大叫道:“周军,是你带人抓的我,我到死也忘不了你!你我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我明明才卖了两百克毒品,你为了立功,硬说我贩毒两千克,你为什么置我于死地?我求求你高抬贵手,就留一套楼房给我儿子住吧。” 周军显然已经习惯了她的歇斯底里,平静地说:“没收你家的非法所得,是法律的规定,当初你在法庭上,怎么不说这些话呢?你说你卖了两百克,我说搜出两千克,咱俩说的都不算,给你量罪的是检察院,法院,谁敢拿法律开玩笑呢?” 红英自知无趣,便跳着脚指着周军大骂起来。身上的手铐脚链在铁窗那边发出很大的声响。 红英的哭喊惊动了看守人员。我暗示周军,访谈结束。 但红英双手死死把住铁栏杆,她不走,固执地向周军要钱:“周军,你搞得我倾家荡产,现在我没有钱花了,你给我钱!” 周军不理她。 “周军你不仅置我于死地,还判我老公也是死刑,害得我姐姐也判了无期,你让我家破人亡,你是我们家的仇人,我们家两代人都死在你们手里,你给我钱,我没钱花了!你给我呀!” 纠缠半天,周军没有办法,只好把衣袋里仅有的一张百元大钞递给她。 此时的红英一把夺过钱,用双手捧在面前,两眼放光地仔细验看钞票,大概确认这的确是一张久违了的钞票之后,她才小心翼翼地把钞票攥在一只手里,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这个时候,我似乎听到了这个女人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哈哈,周军,老娘又白花了你的钱!” 待红英的背影消失后,我转头看看一脸无可奈何的周军,说,当个缉毒警察真不容易啊,挺受伤害的吧?周军苦笑:这算什么?这一年里,她每见我一次都问我要钱。不给就骂,她分不清公安和法院的职责,把所有的仇恨都记在我的头上。听说,她还偷偷把我做成纸人,在纸人的头上和胸口插上针,每晚在脚下踩,咒我。” 红英离开不久,她的姐姐春英被看守人员带到我的面前。她同样是个瘦小的女人,今年57岁了,满脸皱纹,牙齿露在唇外。她看上去比妹妹红英温善一些,也胆怯一些。但有一样,春英一见我面,就追问周军来了没有。 我奇怪地问:你找周军有什么事情? 她简洁地回答:要钱,我没有钱花了。 我问:周军欠你钱? 她恨恨地说:当然欠我钱,他把我家的财产、我妹妹家的财产全给没收了! 我说:那是法官判的,你怎么不去找法官要? 她武断地说:是周军把我抓进来的。就找他要。 我问:你认为你妹妹、妹夫是什么样的人? 她答:好人,善良之人。你是北京来的,求求你给她申冤,要是你们判他们死刑,我就自杀,我要是不出事,他们就不会被抓。我妹妹是为了我,才被抓进来的,我求你了,别让她死。 说着,春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我的眼前只剩下一双紧抓住铁栏杆的手。 停顿了一会儿,我叫她:我看不见你的脸怎么说话?你起来好好说。 叫了几遍,她才起身。那时,她已是泪流满面。我知道她动了真情。就问:你的儿女在干什么? 她痛心地说:我的女儿目标是研究生,现在也没有办法考了,在上班。是我把女儿的前程耽误了。 我问:怎么耽误的? 她答:我要不出事,她可以继续考研究生。 我问:其实真正耽误她的,不是你的出事,而是你的贩毒,你清楚这一点吗? 她老实地回答:可是我要不贩毒,她什么书都没得念。 我试探地问道:你认为自己做错了吗? 她点头承认:错是做错了。可是也不至于判得这么重。把我的妹妹和妹夫都判死刑,他们太狠心了。 春英开始痛哭。边哭边扭动着身体,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数落,嘴里说着的时候,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那个样子,似乎不像是哭,更像是在唱歌。我对中原一带的风俗习惯比较了解,知道她这是在哭丧。她也很清楚,她的妹妹和妹夫再过两个月就是死人了。 我及时劝住了正在哭丧的春英,问了几个小问题,使她平静下来。可是,她一平静下来,又开始寻找周军,索要钱。看来,她和红英一样,把自己所有的人生失败归结到周军抓捕了她们。她们用贩毒积累着个人财富,并把这种财富视为自己人生的全部价值,当这一切都被依法剥夺之后,她们就怀着气急败坏的恼怒,迁怒于周军。 走出审讯室,我对周军说:这红英还真是个人物,一个农村妇女靠贩毒竟然供出两个大学生。 周军叹口气说:她倒也真不容易。审讯时,听她说了些家世,她的父亲死在劳改农场,当时排行老三的红英只有四岁。她母亲为了不让三个女儿吃苦受虐待,宁肯乞讨维生也不肯改嫁。红英长大后嫁到了河南信阳地区的明岗镇,丈夫是一个农民,在蔬菜队种蔬菜,两人生了一儿一女。 和所有为人母的女人一样,红英是希望孩子有大出息的。可是她知道出息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叫智力投资。可丈夫是一个菜农,能拿出钱来给儿子智力投资吗?自然不能。“我要自己想办法挣钱,一定要把儿子供出去!”可是做什么生意挣钱呢?河南的道口烧鸡还是很有名的,就做道口烧鸡吧。于是她跑到道口那个地方,一天销售几只烧鸡地做起了买卖。烧鸡生意让她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手里有了钱,红英开始觉得这烧鸡生意艰苦、利润不高,决心干大生意挣大钱,就转行改做服装生意,间或的还搞香烟的倒买倒卖。一个乡下妇女,要为城市人提供服装服务,没有很高的文化素质,是很难从服装生意上盈利的。结果滞销积压,红英赔了。于是她又转而做起了倒卖香烟的生意,还是不赚钱。红英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灵活,总是不断地变换着挣钱的项目。她又做起了贩卖粮食的生意,这回赚到钱了。不过粮食生意总有一种轰轰烈烈的运作模式,于是招来了强盗的惦记,在一次异地运输的过程中,她被歹徒洗劫了,赔蚀了几万元。这个时候,她的儿子高考传捷报,被一家政法大学录取。四年大学,一笔巨大开销,红英看看自己手上的存款,倒是也够孩子用。不过,红英为孩子设想得很长远,儿子毕业后要结婚,要有楼房,要有汽车,这些还需要一笔更多的钱。自己可不能委屈了孩子,要为他挣钱。可是粮食生意再也不敢做了,就在这时候,一个信息被红英知道了:贩卖毒品最挣钱,几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红英清楚,国家对贩毒者的刑罚是最严厉的,百万富翁的代价是随时被缉拿被判死刑。想到这些,红英心里有些打怵。不过,一想到能够为儿子积累百万家产,红英的心又活泛起来,在数夜的辗转反侧之后,她终于下定了一个决心:为了儿子,我豁出去了,大不了就是一死,能给儿子留下百万财产,死了也值得!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丈夫因为自己不能独立地做任何事情,收入又微不足道,早就形成了对妻子言听计从的习惯,听了妻子的计划,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看中就中!”于是夫妻俩开始贩卖毒品了。 我问周大队长:这河南与内蒙古,并非相邻,红英又是怎样把毒品卖到内蒙古来的呢?周大队长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一个叫老赵的男人。老赵也是河南的农民,因为嗜赌如命,在村中欠下了倾家荡产也难以偿还的债务。为了逃债,他来到了包头市,租赁了房屋,开一家食杂店维持生活。 我问:老赵怎么认识红英的? 周大队长说:他们之间的媒介,是阿丽。阿丽是湖北人,丈夫是河南农民,与红英熟悉,这样通过丈夫,阿丽与红英也熟悉了。这阿丽长得挺漂亮,因为不肯守在庄稼院过穷苦日子,就跑到了包头市打工。她没有手机,就常去老赵的食杂店打电话,一来二去,俩人就熟了。老赵一人离家在外,寂寞难耐,于是就对自己年轻十几岁的阿丽垂涎三尺。两人没用多久,就搅在了一起。可是,问题很快出现了,老赵身边多了一个漂亮女人,原本能够维生的食杂店收入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于是,他开始想挣钱的新路子,最后选择了贩毒,只是他还没有拿到毒品的渠道。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阿丽后,这女人兴奋地告诉他:“我倒是认识一个女人,她可能就做这玩命的生意,我给你联系一下。”老赵高兴地直点头:“中,中,中!”就这样,老赵与红英,建立了上下线的关系。几年的光景,两人都发财了。作为暴发户,红英尽可能地给儿女购置了房产,仅在湖北就购置楼房两套。而作为暴发户,老赵则满足着自己的赌徒之瘾……说到这儿,周大队长停顿一会儿,问:你知道这个农民是怎么挥霍钱的吗? 我摇摇头说:想不出来。 周大队长接着说:他用尿素袋子背了90万元现金去了北京,财大气粗地在王府井饭店包住了一个月。干什么呢?每天就是两件事:赌博和找不同的美女陪着。90万元就这样迅速地在一个月内挥霍得一干二净。 我问:看来这红英要比老赵有点“正事”啊? 周大队长想了一下说:本质上都是农民。贩毒赚到了钱,红英觉得这是福,就怀着“有福同享”的想法,把姐姐春英发展进来,让姐姐给自己当送货的马仔。她哪里知道,她这是给自己的姐姐在前面挖好了坟坑呢? 春英的丈夫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对于歪门邪道一向嗤之以鼻,一听说妻子要去贩毒,极力反对,但是妻子不听他话,气恼之下,他中风瘫痪,躺倒在床。春英是看着妹妹发起来的,她也想脱离苦海。于是,她义无反顾地帮助妹妹送货到包头。结果,这对老姐妹全都是死路一条。 尾声:答案直白得可怕 在西部,我走访了上百名吸毒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只想探询一个问题:人一旦吸毒,到底能不能戒断?答案是失望的,几乎没人能够戒断。只有少部分人在某个阶段,比如三年或五年,往乐观里说,八年或十年里能够相对戒断。在我调查的过程中,一个吸毒者复吸次数在二十次以上的比比皆是。也就是说,一日吸毒,终身就废了。许多吸毒者因忍受不了戒毒的痛苦,往往选择了自残或自杀的道路。在西部,我不知疲倦地往返于看守所之间,采访了数十名毒贩子,就想弄明白一个话题:他们为什么要贩毒?不知道要杀头吗?答案直白得可怕,一个字,为“钱”!而且,毒贩子中,不管有文化没文化的都懂得一个道理:贩毒50克就要杀头。可是,铤而走险、前仆后继者大有人在。为什么?难道毒贩子真的不怕杀头吗?在看了许多法院审判的重特大贩毒案件后,我瞠目结舌了。几百克甚至上千克贩毒案的涉毒人员,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有的十几年,被杀头者竟然不多。 在西部,我还心有余悸地走到十几名艾滋病感染者中间,试图想看到他们悔恨的眼泪。然而,他们满脑子都是毒品,根本不可能有眼泪了。我为一个瘦成骷髅状的女艾滋病患者做了近距离的拍摄,她是因吸毒感染的艾滋病,脸部已经溃烂,正在发烧和咳嗽,现在我不知她是否已离世。这一回,我看准了,什么是艾滋病。 在西部,最不能令我释怀的是那些在一线奔波的缉毒警察。从零距离接触他们的那一刻起,我才深刻地理解了“警殇”的含义。一名内地的缉毒警察奉命到西部执行卧底任务。毒贩子为了验证卧底人员的身份,强迫卧底警察吞冰毒,为了完成任务,卧底警察毅然吞下。当毒贩子被抓获后,卧底警察被急忙送往医院进行输液。我问另一名参战的缉毒警察对此事有何感想,他直摇头说“太恐怖了。”我又问那个卧底警察会不会因此染上毒瘾?他打了个比喻,“就像我正在抽的这支烟,已经吸入肺里了,你说再到医院输液,能把吸进去的烟清洗出来吗?”我不知道这位警察是谁,我在西部采访时,他刚刚完成任务返回内地,我真想向这位内地警察敬礼,这种付出太沉重了。 在西部,我接触的禁毒资料很多,但我不愿意停留在表面资料的数据上,因为它和我自己暗访的数据相差很远。我只知道,在西部共同存在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问题。各级政府不能说不重视禁毒问题,但停留在口头上的多,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多。这些领导其实也知道当地的毒情状况,但由于怕影响经济,怕丢乌纱帽,禁毒力度被人为削弱了。这也许是毒情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吧? 后记 像我一样不了解毒品者大有人在。我一向以为自己与毒品无缘,因为我的生活态度是做个良民,还因为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中国处于成功禁绝了毒品的真空地带,我的青少年时代根本就不认识海洛因是谁,也没有读过史书,那样的环境,使得我内心轻松了许多年。现在看来,那真是一种单纯的幸福。 等我跻身社会后,同事多为知识分子和出生入死的警察,即便是生活中的朋友以及更远些的朋友都与毒品无关,那时,谁要是提到毒品二字,总觉得是很遥远很荒诞的事,甚至以为有人蓄意散布谣言。由此我轻率地断定,周边的环境是安全的,也有理由相信我所在的城市、我所走过的地方、我们这个国家都应该是安全的。 因为长期处于无毒的环境,我对毒品缺乏认识,我想,像我一样不了解毒品的人应该大有人在。某省厅刑侦总队队长调到禁毒总队之初就以为,禁毒部门能有什么事?可是,在他上任当天,一位县长就焦急地打电话来说,儿子失踪两天了,让帮着找人。到了晚上,那位县长又打来电话,说儿子找到了,因为吸毒过量死在一个公共厕所里。总队长问那位县长,知道孩子吸毒的事吗?县长痛苦地摇头说,真的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才知,从一两年前开始,家里时常出现丢钱的事,孩子母亲的首饰也常常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三年前,我也曾问某省公安厅的厅长,现在哪个处室工作轻松些?那位厅长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禁毒啊。连一个堂堂的厅长都是这个认识,我更有理由盲目地相信,涉毒人员于社会来说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一件小事。然而,这次西部之行,不仅击碎了我的想当然,而且给我补了一堂深刻认识毒品乃至艾滋病的教育课。用肉眼看到事实的真相是很残忍的,这令我一遍遍回味鲁迅说过的一句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打碎了给人看”。两个月的西部之行,所见所闻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我宁愿没有去过西部,而保留对西部的美好向往。 我在游走了西部的包头、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宁夏、甘肃、新疆10省、市、自治区后发现,吸贩毒者竟然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农民。在我采访的几百名吸毒者中,农民占85%;在我零距离接触的几十名毒贩子中,农民占75%,吸贩毒行为几乎等于贫穷的农民!联合国国际麻醉品控制局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毒品生产不但不能让穷国致富,反而会阻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越来越贫穷。报告警告说,如果以为生产毒品能让国家变富,这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国际麻醉品控制局成员赖纳·施密特在发布报告时指出,通常来说,只有1%的毒品生产收益留在毒品的发源国,大部分的钱是在毒品分销过程中产生的,而这些钱都留给了发达国家。 在看过太多的因涉毒而导致的人间悲剧后,触动是不言而喻的,“触目惊心”可以概括我整个西部之行的感受。也许我给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有病毒的西部,然而我不是悲观的。因为在西部,我们数以万计的英雄的缉毒警察们正在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践行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神圣职责。同时,部分吸毒者不仅自己努力脱毒,而且义务帮助周围的吸毒人员也步入脱毒的尝试中。我还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由民间发起的“戒毒志愿者”队伍,成为戒毒者温暖的安慰。更让我振奋的是,在西部,大多数政府部门都行动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态度和投入程度,决定着这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禁毒战役的胜负。许多毒品重灾区,经过政府的整治,正在向无毒社区靠拢。(续完)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