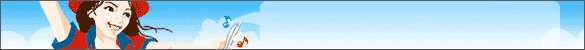1941年5月5日辗转香港的文化精英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4日13:46 三联生活周刊 | |||||||||
|
记者◎郭娜 邹韬奋的流亡和茅盾的任务
1941年5月5日早饭后,邹韬奋便匆匆起身,离开半岛酒店旁的家横穿马路来到天星码头,今天要专程跑一趟茅盾的家。 从九龙渡海到香港,7分钟,天星小轮上人不多。两个月前,3月5日下午14时,在香港地下党负责人廖承志安排下,邹韬奋从桂林抵达香港,同行的还包括张有渔、韩幽桐、孟秋江。 飞机起飞两小时后,当重庆参政会秘书长王石按蒋介石吩咐急电到桂林,要求“坚决挽留”邹韬奋时,飞机已经在启德机场平安降落。 皖南事变后,文化人向香港迁移的第二次浪潮涌起。1941年2月起,在周恩来部署下,夏衍、邹韬奋、茅盾等人先后到港。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记述此次赴港经历,称其为“第四次流亡”。 到港两个月,为了《华商报》创立和《大众生活》复刊,邹韬奋昼夜奔忙。他给在重庆的沈钧儒写信说:每天一定要写若干字数的文字,还要开会,忙得不亦乐乎。到了晚上,放下笔杆,倒头便睡,“真如僵尸一般”。一次聚会上,有人问起他在香港的打算,他说:“我的能力和志趣,都不允许我做一个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我不过是一个喇叭手,吹出人民大众的要求罢了。” 事情进展总算顺利,登记难关也迎刃而解。在1936年的《生活星期刊》上,邹韬奋曾撰文说:“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的商人出来办报,理由是他的惟一宗旨是在赚钱……要赚钱是他们认为最可钦佩的大志……”来港不久,邹韬奋很快通过朋友认识了这样一位港绅的儿子曹克安。曹家早已登记好要办一个周刊,只是没有合适的主编。曹克安钦佩邹韬奋的人品和文章,事情很快商定。 刊名仍用曾在上海发行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人曹克安,主编邹韬奋,金仲华、茅盾、夏衍、胡绳、乔冠华、千家驹等为编委。 5月3日,第一次编委会刚刚在香港湾仔凤凰台生活书店办公室开过。会议商定5月10日发稿,5月17日出版《大众生活》复刊号。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道:“邹韬奋的确抓得很紧,我们约定以后每周六编委会雷打不动,讨论时事之外,还要决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并在这个范围内每个编委担任一篇以上的文稿。韬奋不止一次说过,他办刊的经验就是抓‘一头一尾’,也就是社论和读者来信。一次私下谈话,他对我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会上还有人提出最好有一连载的长篇小说,内容能够吸引香港的读者,否则,全是硬性的政论文章,他们接受不了。 “五四”过后,邹韬奋为此专门来到茅盾家。1938年茅盾曾在港10个月,创办《文艺阵地》。这次由周恩来安排赴港,任务是“和其他同志一起开辟‘第二战线’”。此时茅盾已经搬到香港西边上环的坚尼地道(Kennedy road),环境好过邹韬奋一家5口挤住的两间陋室。半山上的这条路如今仍是个幽静所在,即便对香港市民也并非耳熟能详。路段望海靠山,街巷疏落,不似市区般拥挤嘈杂,正是写字的好地方。茅盾一家租住的是两层的小洋房,附带花园。房东是旅美华侨,70多岁,原是香港某大银行广州分行的经理,广州沦陷后返港。原配早亡,当家的是二太太,一位50多岁的胖女人,另外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他们住在楼下,楼上全部出租。厢房住的是沈兹九和她的女儿,正房住的是《世界知识》的编辑张铁生。茅盾夫妇住装了玻璃窗的阳台,只容一张床和一张桌。 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5月5日邹韬奋来访,茅盾写道:韬奋来看我,开门见山道:“前天会上当着你的面,大家不便说,会后都向我建议,《大众生活》上的连载小说,应该请你来写,你的名气大,下笔又快,承担任务是不成问题的。请你就作为紧急任务赶写一部吧。”茅盾为难道:“长篇小说哪能说些就写?”邹韬奋说:“这也是万不得已,你就把平时积累的素材拿出来编个故事吧。你可以一边写一边登,大约每期只占4个页码,8000字左右。”茅盾沉吟片刻,咬咬牙说:“好吧,我来写!你什么时候要第一批稿?”邹韬奋扳了扳手指道:“给你一个星期,13号交稿。我给你留出4个页码,你给我4天印刷的时间。” 这篇小说便是“抗战第一长篇”《腐蚀》。考虑到“香港和南洋一带读者喜欢看武侠、惊险小说”,茅盾写了一个“被骗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沉沦的青年女特务的遭遇”。故事背景“放到皖南事变前后,从而揭露当时蒋介石勾结日汪,一手制造千古奇冤的真相”。小说采用日记体,序言称这本日记在重庆防空洞中发现。1941年秋连载完后,小说一版再版,不少读者来信问日记主人后来的下落。 《腐蚀》之后,邹韬奋又请夏衍写了《春寒》。名家文字、时事政论加上长篇连载,《大众生活》很快在素有小报传统的香港打开了天地,销量达10万份。夏衍认为:“《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来,在当时当地,《大众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华商报》还大。” 长袖善舞的粤华公司 1941年的香港,依旧一派歌舞升平的享乐氛围。西方人、日本人、共产党、国民党、汪伪、黑道烂仔,形形色色的势力在港英当局统治下各有道场。丘吉尔上台组成战时内阁后,港英政府开始对日本态度强硬,抗日宣传不再被阻拦。 茅盾写道:“黄昏时候,皇后大道中段开始排演着每个星期日晚上照例的繁华节目。血一样鲜艳的霓虹灯管,配着苍白色的日光管,还有磷火似的绿光管,不但不觉得有一些不大调和,而且好像非此便不足以显示都市之夜的美丽。各色各样娱乐的机构,已经开足了马力。各路巴士和电车一批一批载来各色人等;娱乐戏院和皇后戏院门前挤得满满的,似乎那钢骨水泥的大建筑也饱胀得气喘了。” 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一楼的临街房开着一家并不起眼的商铺,门面招牌写着四个大字,“粤华公司”。店里经营各式中国名茶,货色齐全,价格公道,每天都有不少客商光顾。这里正是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机关所在地。办事处负责人是廖承志,何香凝和廖仲恺的儿子,人称“国民党三公子”。 1937年5月21日,埃德加·斯诺的前妻海伦·斯诺在延安访问过廖承志后,有一段生动的描写:“他说着一口漂亮的英语,操美国口音。我在延安红军剧社里,已经不止一次看见过他。在一幕名叫《间谍》的剧中,他扮演西班牙军官,在舞台上严刑逼供不幸的共和党人,把傲气十足、惨无人道的佛朗哥军官表演得惟妙惟肖,以致使我担心观众会一哄而起,把他毒打一顿。后来,他在《阿Q》一剧中,还扮演过两个角色,他表演得非常成功。他说:‘我什么都会干。’ “我发现他的确多才多艺。他讲德语、日语、法语、俄语、英语和汉语。我们交谈时,他不停地吸烟,手持蝇拍,在他的炕上跳过来、蹦过去地打苍蝇。他说,长征过草地时,吃的东西很差。他丢失了他自己的那份儿炒面,因而,靠给同志画像‘混饭吃’。有人告诉我,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曾经协助编辑过两份杂志,他的文采是众所公认的。他写过剧本,搞过蚀刻画、木刻画、漫画、油画以及水彩画。他给徐特立等领导者画过像。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还是有名的歌手和导演。他的乒乓球、篮球也打得不错……他是苏区最富于幽默感的人。为了说明狗肉好吃,还是驴肉好吃,他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他显得非常西方化、美国化,工作、讲话都很快……” 周恩来正是看中了廖承志身上诸多的优越条件,1937年底派他到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任务是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以适应内地文化人来港和即将到来的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势”。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香港成了文化人的避难地。他们从上海、广州、重庆、武汉相继辗转至香港,除了大批新闻工作者,还包括梅兰芳、胡蝶、蔡楚生、萧红和端木蕻良等大批名士。很快,粤华公司便成了共产党在香港组织文化事业的得力舞台。自称“肥仔”的廖承志凭着“求同存异、广交朋友”的圆通,团结起大批文化人士协同抗日。 1938年起,曾经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在内地战火纷飞的大背景下上演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茅盾主编《文艺阵地》、金仲华主编《世界知识》,戴望舒和叶灵凤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张光宇主编《星岛日报》画刊,郁风主编《耕耘》杂志,萨空了主编《立报》、爱泼斯坦为保卫中国同盟主编《新闻通讯》,黄苗子担任《国民日报》经理,叶浅予肩负着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的使命,在香港主编和出版《今日中国》,用英文版向海外宣传抗战中国。丁聪参加马国亮和李青主编的《大地》画报并兼《今日中国》编务,杨刚在《大公报》、白望春在《香港日报》工作。蔡楚生和司徒慧敏制作了《血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一系列抗日电影。徐迟、冯亦代虽在中国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工作,但还兼职《星报》电讯翻译,他们和同在中国银行任职的诗人袁水拍,都与文化界关系十分密切,年轻的乔冠华开始凭借国际社评崭露头角。 因袭香港旧例,这些文化人时常聚会喝下午茶。粤华公司附近、皇后大道转角上的“蓝鸟”咖啡馆和皇后大道中华百货公司“阁仔”茶室,都是常去的所在。但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让文化人并不轻松。茅盾每月编《文艺阵地》所得付了太子道公寓房租便所剩无几。10个月下来,倒贴了一千多积蓄。这也成为他后来决心去新疆的一个原因。 1939年,3月26日,成立于武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香港设立分会。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地山任主席,因茅盾已经离港,戴望舒成为实际上的负责人。此后,文协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文化团体。此时的戴望舒很享受在香港的生活,他租在薄扶林道山上的花园洋房原来住的是一位叫巴尔伏的爵士,绰号“南海岛王”,是英国世家子弟。这位爵士经常在府上举办聚会,邀请戴望舒这样的社会名流参加。1940年初他奉命回国后,房子以较便宜的价钱租给了戴望舒一家。 这房子的英文名叫Woodbrook Villa,戴望舒译为“林泉居”,他用“男耕女织”来比拟这战乱年代难得的安居。他雇了一个手艺不错的广东厨子,不时举办家宴,请文艺界的朋友来喝酒、聊天、表演节目。他还和妻子穆丽娟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菜地,种了番茄和金笋。他在《示长女》中写道:“我们曾有一个临海的园子,它给我们滋养的番茄和金笋,你爸爸读倦了书去垦地,你妈妈在太阳阴里缝纫,你呢,你在草地上追彩蝶,然后在温柔的怀里寻温柔的梦境。” 戴望舒感到生活前所未有的扎实舒畅,《星座》副刊的成功和文协香港分会的组织工作让他格外忙碌。袁水拍、徐迟、楼适夷、郁达夫、胡愈之、萧乾、梁宗岱、李健吾、艾芜等名家的作品,常常在《星座》上刊出。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发表过《到底都是上海人》一文。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也是在《星座》连载。正如茅盾后来所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戴望舒主持下的《星座》,无论作者阵容还是作品质素,都让当时香港其他报纸副刊望尘莫及。这景象,甚至让戴望舒感觉在香港找到了家园,似乎也为他在香港沦陷后选择留守埋下了伏笔。 1941年5月4日,文协香港分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召开,会上热烈欢迎皖南事变后来港的内地作家和艺术家,其中包括茅盾和夏衍,会上二人当选为香港分会理事。 此时,廖承志每周都组织一次时局漫谈会,参加者包括:邹韬奋、茅盾、金仲华、杨东莼、乔冠华、范长江、夏衍、胡绳。据茅盾回忆:“每次开会,先由廖承志介绍国内形势,再由乔冠华讲讲国际形势,然后大家漫谈。廖承志的国内形势报告是漫谈会中心,他经常在报告中传达党的重要文件和指示,介绍延安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邹韬奋到港的第二天,3月6日,廖承志便组织了一次会议,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商讨办报事宜。根据周恩来“不红不白,灰一些”的指示,报纸很快定名为《华商报》,由香港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和他的弟弟邓文钊(廖承志的表妹夫、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出面登记。报社在香港最热闹的中环荷里活道租下一间两层楼铺面做社址,社长是范长江,胡仲持任总编辑,刘思慕、乔冠华、羊枣(杨潮)等写社论,夏衍除写社论和短评外,还负责副刊《灯塔》。 从4月8日创刊号起,邹韬奋为《华商报》连载长文《抗日以来》,至6月30日止共77篇。此时,邹家5口的日常生活,全凭范长江每月预支出400港币稿费。两个孩子上学外加房租,生活愈发拮据,连邹韬奋每日外出用钱,都是妻子沈粹缜算好放入他口袋。 左右摇摆的审查老爷和“开天窗” 1941年5月,正当新创办的《大众生活》和《华商报》在香港本土双璧生辉之际,长期以来最有影响的进步报纸《星岛日报》被国民党收买。国民党同时以盟邦身份要求港英当局“取缔一切违背国府抗建国策和损害国府声誉的言论”。香港政府同意了后一条要求,并且执行得有板有眼。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写道:“我二进香港之后,首先发现的,就是报纸杂志(当然是进步报刊)上的天窗比1938年开得更多更大了。我研究了这些天窗,看得出香港政府那些检察官的水平确实有了提高,甚至使人怀疑他们之中有重庆推荐来的。” 二进香港的茅盾发现:“香港经过3年的战火熏染,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空气浓厚了,持久抗战的道理,在先进工人和知识界中已成常识,一般市民对于国家大事也不再漠不关心……与1938年相比,香港是大大的不同了,那时还是一片‘文化荒漠’,现在已出现了片片绿洲;那时是不准谈抗日,现在已能自由宣传。” 这其中原因,除了同盟国和轴心国战况的变化,丘吉尔上台,宋庆龄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发挥了作用。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挽着路易·艾黎的胳膊一脸轻松地跳上外滩码头的一艘客轮,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出走香港。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攻占启德机场前的6小时,宋庆龄在香港居住4年,期间只有短暂的赴重庆旅行,这也是宋氏三姐妹最后一次同行。 在香港,即使小学生都知道宋庆龄是“国母”,她领导的保盟成功地建立了统一战线,社会各阶层人士,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都认为同宋庆龄交往是自己的殊荣。各界人士踊跃为保盟提供支持和捐赠,其中有中方和外籍的官员、银行家、工商业家。应宋庆龄邀请常在保盟活动场合出现的还有港督罗富国爵士。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夫脱爵士捐赠了带手术间的新式救护车。在远东有一支商船队的挪威船主埃里克·莫勒也捐赠了一笔巨款。 至于香港的中国富人,一位前保盟会员回忆起他在一次“工合”筹款聚会上所见的一幕:“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拉着香港中国首富何东爵士女婿罗文锦的右手,硬是逼着他写下捐款的数额。其他名人排成队,挨个来,为‘工合’筹到了一大笔钱。”当时,何东爵士的女儿何娴姿医生,也在保盟做基层工作。国民党右派要人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帮忙码放和分发供应品。 皖南事变后,宋子文退出保盟并没有给香港的统一战线带来危机。宋庆龄很快筹建了一个由中外赞助人组成的新机构。中国方面有孙科、冯玉祥;国际方面有印度的尼赫鲁、国民大会党援华医疗队前队长爱德华医生,美国黑人艺术家保罗·罗伯逊,德国作家托玛斯·曼和赛珍珠,甚至还有克莱尔·布思——《时代》杂志大老板亨利·卢斯的夫人,联想到后来他们所持的“冷战”立场,她的参加似乎不可思议。 1941年中,英国已与德国交战但尚未对日作战,香港总督罗富国继续执行英国的绥靖政策,尽管他对保盟的募捐活动保持友好,但当局仍严格控制中国人的抗日言行,专门成立了特别检查组。审查老爷们直接对定稿的清样进行删扣,开天窗和空方格成了战时香港无可奈何的文化景观。- 声明:本稿件为《三联生活周刊》独家提供新浪网,如需转载请与《三联生活周刊》或新浪网联系。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