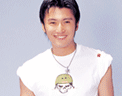艾滋病人和总书记握手后的困境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14日14:34 中国青年报 | |||||||||
|
小卫和老纪都是山西闻喜县农民,同是1965年出生,两人都因为采血,于1997年前后查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去年底,在北京佑安医院住院时,他俩见到胡锦涛,与总书记握了手。当晚,电视新闻做了报道,他俩的脸没有做遮蔽处理。 自此,两家起了风波,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一年来,跟踪拍摄他俩的“防艾”志愿者王天明,目睹了两个家庭发生的事情,写了情况反映:与胡锦涛总书记握手的两名艾滋病患者处境尴尬艰难。他找了若干家媒体,也多次找相关部门,但无人理会。 “12月1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也是艾滋病人受关注的高峰期。11月25日,王天明专门去山西,把老纪他们接到了北京。 “老百姓会觉得,看,国家主席都不害怕艾滋病病人,咱更不用怕了” 去年11月,在短短的时间内,小卫周围有3个艾滋病病友去世,他心里发毛,思想压力大,就给曾住过的北京佑安医院打电话,进行咨询。 “医院说,正好要赶上‘十二月一日’了,可能有些活动需要你们配合一下,你就过来吧。”小卫说他这样来了北京,老纪也在佑安医院住着。 住了一周,就赶上总书记到佑安医院。见面的情形,小卫记忆犹新:“那是去年11月30日下午3时40分,起先,医院没敢说是谁来,只告诉我们要见一个大的国家领导人。提前半小时,胡锦涛已经进医院了,他们才告诉我和老纪要见谁。” 小卫以前做过生意,妻子孩子是城镇户口,一家人一直在县城边上租房子住。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强,脑子转得也快。知道来的人是总书记,他准备好了签名本,还拿上一双妻子做的、上边绣着“关心关爱”的鞋垫。 我问小卫当时是什么感觉,紧张吗? 他说不紧张。只觉得脑子空荡荡,有点像梦游,当然也挺激动的。胡锦涛一行先是去了老纪的病房,再到小卫的病房。 “我坐在床上,胡主席一进病房就向我伸出手,我看到他衣服上佩戴着红丝带。他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是山西的。吴仪副总理跟在后边,说,啊,也是山西的,也是卖血感染的吧?” “胡主席的手挺热乎的。他还对我说:你们得这个病是不幸的,但党和政府都很关怀你们,社会各界也在关怀和支持你们,你们要有信心战胜疾病!” 时间很短暂,告别时,小卫掏出鞋垫,跟总书记说:我想送您一样小东西,是我爱人绣的鞋垫。“他将鞋垫拿到手里,仔细地端详,对我说非常感谢。我又赶紧掏出笔记本,请他签字留念,胡主席愉快地为我写下‘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 回到病房,心情仍不平静。一位当时采访的记者描述他俩“兴高采烈地沉浸在激动、幸福之中”。 没料到,晚上电视新闻一播,小卫和老纪家里就炸了锅。 先是小卫妻子来电话:“你还让不让我们活哩?”接着,老纪的老婆也打来电话,说16岁的儿子找不见,失踪了。 知道家里出事了,别的病人说:“两个傻×,如果我们答应见面,哪里能轮到你俩?就是给我30万元,我们也不会见,上电视曝这个光。” “我当时只是想,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全国的艾滋病感染者,胡主席代表的是党和国家。见了面、握了手,会起好的作用,老百姓会觉得,看,国家主席都不害怕艾滋病病人,咱更不用怕了。 “咱还想,能跟胡锦涛握手,跟国家元首见面,就是死了也不冤枉。但没考虑到家人,尤其没想到给小孩带来那么大的伤害。” “我最受不了的是对我家人的歧视。他们不是艾滋病人” 老纪和小卫以前也上过电视,但他们不知道这次曝光,跟以往比是天地之别。 “太厉害了!《新闻联播》都还是小问题,主要是那个‘新闻频道’,每小时滚动一次,到点就出来,铺天盖地。如果这个人七点看到了,他马上告诉另一个人,八点钟再看。现在都有手机、电话,一个传一个,越传越广,看到的人太多了,影响面太大。我想不光是县上,连市上、省上的领导也知道了吧。” 上电视的结果是:老纪和小卫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被彻底确认。以前,跟他们接触的人只是隐隐约约地猜测而已。 但老纪和小卫还没把事情想得太坏。见过总书记,在回山西的火车上,小卫还信誓旦旦,说回去要好好配合政府,为防艾宣传做哪些工作。 小卫一回家,妻子不准他进门,边哭边骂:你别进这个家,别影响一家人的生活,要不是你这样,我们怎么会让别人看不起?小卫回来后,她七八天没敢出门,说邻居像躲瘟疫一样躲她和孩子。小卫家一直在县城边租房住,房租便宜,租了6年。知道小卫的身份后,村干部找到房东:你让他家赶紧搬走,别把咱村人传染了。房东一再撵他们搬家,“大冬天的,现在怎么办?”妻子发愁地叫道。 到家第二天,小卫被有关部门喊去,他还以为是什么好事,结果被领导训斥了一顿:“谁让你把记者带回来了,你以为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吗?”小卫泄了气,回家躺到床上不起。 1993年,小卫被单采血桨,两次抽了他2000CC,回输不到400CC,挣了80元钱,结果染上了艾滋病毒。 “我自认倒霉,我也允许别人歧视我,这也是人们的一种自我保护。但我最受不了的是对我家人的歧视。他们不是艾滋病人,他们现在都好好的。” “你妻子不是?”我打断他问。 小卫一听急了:“干嘛我妻子就是?这是人们的误区,认为艾滋病很容易传染,所以觉得非常可怕。我是1997年查出感染的,真正感染的时间还要早。1998年,我们有8个感染者一块去地坛医院治疗,8个人都是夫妻一方感染,而另一方并没有感染。我和妻子孩子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现在仍然是健康的。” 他说自己和从前一样,只是身上多了一种病毒。“我吃剩的饭,我老婆也吃。要是我有破伤,比如手划破,出血了,我会注意,让他们别碰。其他跟以前生活基本上一样。” 我对小卫说,既然老婆赶你就走,你走呗! 他叹了一口气,道:“我现在就是走,也给家人带来麻烦。我还是小孩的爸爸,还是人家的丈夫,别人还是不会跟他们交往,照样歧视他们。如果我能给他们创造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我可以走。她说的也是气话,被逼无奈。以前的朋友都不找她,她又不敢跟人接触,生活圈子小了,而且还影响到她兄弟姐妹的生活。” 他家被房东赶走后,小卫找同学帮忙租房子。不告诉房东吧,将来人家知道了又要撵他们走;告诉吧,又没人敢租。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房子,一年的房租比原先贵了几千元。 闻喜县县城不大,总有人问小卫:看你这个人挺面熟,在哪儿见过你。小卫就说,咱闻喜就这么大,谁跟谁没见过,我看你也挺脸熟的。有一天在理发店,他差点儿又被认出来。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给他理发的人说,小卫听了心惊肉跳。“你是在电视台上班吧?”听他这么说,小卫松了口气,赶紧拿话搪塞过去。 上电视后,认识小卫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病。换一个地方住,隐姓埋名,但时间一长,人家还会问他姓什么,是哪个村的,小卫一家不敢讲。比如他是东村的,偏偏说是西村的,不敢让人认识了解,不能正常交往。知道了,房子又住不成了。小卫说最对不起的是他小孩,才10岁。小朋友都不跟他玩,很可怜的。 有天晚上,大人不在家,只有儿子一个人在,收电费的来了,敲门,小孩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很害怕。小卫一回家,孩子就问:“爸爸,他是不是又要赶我们走,不让咱住啊?”小卫说自己听了,很伤心。 “这一年吧,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像做贼一样。” 以前,小卫的妻子一直支持他做“防艾”工作,现在抱怨多了,俩人争吵也多了。小卫说不太愿意回家,家不再是避风港。 女儿中考,小卫在外头忙没管,孩子没考上,妻子就埋怨小卫。今年女儿找工作,要 面试,正好有电视台来拍关于艾滋病人的片子,让小卫帮忙找一下病人。女儿面试时小卫又没去成,结果没通过。小卫妻子气急了,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小卫,你死在外头,再也不要回来!”看了这条短信,小卫说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因为压力大,小卫身体出了问题。今年7月份来北京开会,一下车,人突然不能讲话,到医院一查,说是脑梗塞。 家人受到歧视,租不到房子,小卫去找过当地有关领导,看能不能帮他找一找房子,房租他自己出。“他们怎么讲,你干脆住我办公室好了。我感觉他们是这么想的,你上电视,又不是我们安排的,干嘛现在出事情了,要找地方政府管?” 后半辈子,总不能让家人躲着藏着过日子。小卫决定在县城买房,他这样考虑:假如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提心吊胆,被赶来赶去的。我们可以堂堂正正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是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别人也没权利赶走我们。“作为男人,我现在最主要的责任,是给家人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处,给他们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 在县城买商品房,需要十几万元,小卫已凑了一半的钱,交了定金。现在房子涨价,开发商催他交全款,否则就把房子转给别人。 小卫买房的事,招来不少非议。一位当地干部说:“小卫,你比我都强,你都敢买房。”还有人说:“一个农民、一个艾滋病患者,凭什么到城里买房?” “他们只对我买房的事说三道四,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关心一下我家的处境。”小卫神情暗淡地讲。“本来,自己是挺抱希望的!” 1997年他查出得这个病,1998年就到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治疗,吃了半年中药。临走时,得知一位教授从美国回来,带回了一些抗病毒药,用这种药,一个月花9000元钱。 “先不说价钱,起码觉得有治的药,生命就有救了。后来又到佑安医院治疗,用中药后,医院让我看了对比数据,是好的变化。到2003年,国内也能生产抗病毒的药。我想只要好好干活,吃药治疗,生命是有希望的,自己能活着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没想到,这一年,自己给家带来这么大的麻烦,给孩子带来的是伤害。” 小卫觉得现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多余的人,早一天死了,对家人是早一天的解脱,他们也早一天清静。他听人讲,在北京,被汽车撞死,能赔20万元,在他们当地也能赔七八万元。 “前天,临来北京时,我开玩笑问10岁的儿子:要是爸爸被车撞死了,能赔七八万元,就够咱家买房了。小孩一听就哭起来:我不要房子,我要爸爸!” 说到这,小卫眼圈也红了。 “如果老纪哪一天不在了,我和孩子在村里就呆不成!” 老纪家的处境,比小卫家还难。 因为家里没电视机,老纪的妻子当天晚上没看到《新闻联播》。19时刚过,村里就有人跑来告诉她,老纪跟胡主席握手,上电视了。一会儿功夫,他们那个千把人的村子,全传遍了。 老纪妻子说,儿子早晨上学,别的小孩看过电视新闻,知道他爸是艾滋病,骂了他,把他坐的椅子抽走,扔到外头去,不让他在教室里坐。儿子回家说,不想上学了。“我骂了他,学费都交上了,你不好好上学,你不能待在家里。”结果孩子失踪了。 老纪赶回家找孩子,又动员了亲戚朋友帮着一块找。他们去了同学家里找,还去了车站、医院、公安局,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 “天上下着雪,我骑上车子四处找,找不见,急疯了。我想是不是被人贩子拐骗了,以前老听人家说,他们把男孩拐走后,把小孩的肝、肾摘下来卖哩。” 过了一个多星期,孩子自己回来了。说他一直住在村外的苹果园里,夜里睡在人家看园子的小棚子里,饿了,吃树上剩下的苹果。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实在是又冷又饿,熬不下去,只好回家。 “孩子回家后,一句话都不说。”从那以后好长时间,他也不去学校。 老纪还有个女儿,11岁。在学校,下课时间,没有人理她,都是一个人玩。别的小孩子见了她就叫:别碰她,她有艾滋病,碰了会把你传染上。在村里,老师要挨家吃派饭,但从来不到老纪家。老纪去过一趟学校,找领导,越找歧视得越厉害。 今年过春节,女儿一个人在家门口玩,跑过来一群小孩,冲她喊:你家是个艾滋病!你家是个艾滋病!老纪妻子在屋里听到,气得不行。 “我孩子天天哭闹,吵着要转学。” 村里人知道老纪是艾滋病后,再也没人敢跟他家来往。以前,谁家有红白事,都喊老纪妻子帮忙,现在没人叫她。村里人议论她:老纪有艾滋病,还不知道她有没有哩。 “我现在都不敢感冒,一感冒,村里人就说我艾滋病犯了。我谁家都不能去,也没人到我家来。我现在活得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活得太累,活得没有意思,我不想活哩!”老纪的妻子反反复复地叨唠着,她今年才37岁。 我问她:你就不能原谅村里人?他们是害怕啊。 “我不能原谅!”她的口气很坚决。 “他们就好像把我们一家人给判了死刑一样。我跟他们说了,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么可怕,要是真那么容易传染,我和孩子早就传上了。可是怎么说,都不信,还说我在骗他们。” “你有没有好好查查,到底染没染上?” “查过好几次了,没有。” “孩子呢?” “也没有。” 说起生活上的事,她讲今年天旱,一亩地才打了50斤小麦,他家10亩地,才收上500来斤,吃都不够。老纪今年又一直病着,生活压力特别大。 我问她除了种地,可不可以养点鸡什么的。 她说养了也没人要,她家养的鸡只能在院子里跑,不敢出去,村里人不让。“他们连我家的鸡也害怕。现在,我什么都不养,都没有。” “那收费的人,是不是也不敢上门了?” “照收,钱是不害怕我家的,他们巴不得我多交点才好哩。” 老纪妻子的娘家在甘肃,她一个人嫁到闻喜。到现在娘家也不知道老纪得病的事情,她不敢说。自打老纪查出这病,她一直心烦,思想压力大,生怕老纪哪天发病了。 “8年了,我过得特别痛苦。以前,别人不知道,在村里过日子还行,这一年,就不行了。如果老纪哪一天不在了,我和孩子在村里就呆不成!” “可这次,他是真哭,哭得跟老牛一样,‘哞哞’的” 跟踪拍摄小卫和老纪的王天明,今年9月去山西,快到闻喜县城时,收到老纪一条短信:王老师,能不能浪费你一盘带子,到我家好好拍拍,反映一下我家的问题。 “我一看,知道出事了!”王天明说,因为以前,老纪和他妻子一直拒绝拍摄,王天 明直奔老纪家。 老纪家住的是窑洞,里外两间。进门一看,老纪躺在外间窑洞,老婆躺在里间。老纪一看王天明他们来了,放声大哭。 “在我的印象里,当过兵的老纪身上还有军人的风采,是很乐观开朗的人。哪怕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也照样乐喝喝的。可这次,他是真哭,哭得跟老牛一样,‘哞哞’的。” 老纪边哭边说,老婆这次感冒了,村里人就说她是艾滋病犯了,加上没钱看病,老婆说什么都不想活了,已经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他家的窑洞,前年雨天多,塌了,现在住的是别人的弃窑。窑主这两天也来劲儿了,说话叮当地:这是我的窑,我让你们走,你就得马上走!赶老纪一家搬走。 “跟你说实在话,村里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连这么小的小孩,都管我叫艾滋病。快一年了,我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呵!老婆说我为国家做贡献,把自己家害完了。她也是撑不下去,才闹绝食。” 进了里屋,王天明看见老纪妻子躺在靠窗的床上,到处是输液用的器具和瓶子,一片狼藉。她讲,前几天感冒了,村里人就说她也是艾滋病犯了,听了很生气。“最叫人咽不下这口气的是,村委会建厂,没经同意就毁了我家的地,当时小麦都一尺高了,这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她开始输了两天液,没什么效果,去住院又没有钱,后来液也不输,不吃不喝,昨晚上吐血,这次想活也活不成了。 王天明劝她先去医院看病,死活不去。因为有事,王天明离开老纪家。事没办完,就接到电话,说是老纪要服毒自杀,一伙人又匆忙赶回村里。“原来老纪做了饭,让老婆吃,可她还是坚决不吃,老纪没辙了。你不想活了,我也没指望了,我先死球算,老纪跑了。” 老纪一跑,他老婆躺不住,赶紧给小卫打了电话。村北是一条很深的沟,有人看见老纪进沟了。王天明又喊上一些人,进沟里找,找了一个多钟头,跑进去十多里地,才看见老纪。他一脸土,正在沟崖上边转悠着。 老纪回家后,妻子同意去县医院。 “王老师他们来,算救了我们一家,是他出钱,送我去了县医院。”提起这件事,老纪妻子面部僵硬地说。以前她发愁时只是偷偷地哭,一个人闷着、忍着。但那次她说实在受不了,一共饿了五天五夜,胃吐血,头晕,下狠心不想活哩。她想过不知多少次,干脆买上灭耗子药,再做上一锅饭,让孩子吃上,一家人死了算球,省着让人看了烦。“我想死之前,写篇稿,告诉社会,我一家是怎么死的。可我没文化,心里有话就是写不出来。绝食后,现在,脑子也不管用,好多事情都记不住了。” “为了感染者不受歧视,我们站出来,想起到好的作用,没想到,让自己的家陷了进去” 已经晚上10时多了,还不见老纪的人影。这次,他带了当地的7个艾滋病人,到佑安医院,说是参加免费治疗。 “我家老纪,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老纪妻子抱怨道。 有次孩子发高烧,正好一个女艾滋病人发病,给老纪打电话,放下电话他就去了。雪天,老纪走了十几公里,上人家帮忙,自己的孩子他不管。政府有关部门,有事也常找老纪,喊他去做宣传,搞调查,拍片子什么的。气急了,老婆骂他:“你那些人一叫,你跑得比兔子还快,家里有事,总见不到你的面。”在外头忙归忙,可到了吃饭时间,老纪就灰溜溜地回家了。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有的部门这个样子对待老纪。工作的时候叫他,吃饭的时候没人理他。我们那里,吃一碗面,才3块钱,哪怕给他3块钱,让他出去吃碗面也好。去,你回家吃饭,吃完饭下午再来。他们吃饭,还不是花国家的钱,老纪也是工作,却不叫他吃,我特别生气。” 我问老纪妻子,老纪这样参与“防艾”工作,真没回报? 她气呼呼地说:“不但没回报,还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 王天明这次去山西叫她来,她死活不来,好说歹说,才跟来。“我家老纪不让我说,怕对政府不好。我不管,我就要实话实说。我家老纪,对宣传防止艾滋病,做的贡献不少,配合政府做了不少工作,我家有困难,为啥没人帮?” 因为孩子哭着闹着要转学,她没办法,去县上找,但没人理她。“我两个孩子的学习不行了,成绩下降得厉害。”王天明也说老纪的俩孩子长得很精神,这样下去,真是可惜了。 “我惟一的想法,就是能让我孩子离开村子。要是能在北京找下个打工的活,哪怕一个月挣两三百,我就把孩子带出来,我实在不想在村里待下去了。” 王天明介绍说,这些年,老纪和小卫不仅在当地为患者服务,还一直参与全国性的“防艾”宣传活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艾滋病感染到我为止”。当地不少艾滋病人,都是由他俩带出来看病的,向艾滋病人提供咨询,带人家去医院化验、住院。他们甚至跑到一些曾卖过血的人家里,劝人家去检查,看看有没有染上艾滋病。为这,两人还挨过打。 “我认为他俩挺了不起的,对阻止当地艾滋病进一步蔓延是有一定功劳的。现在,有一些做艾滋工作的人,会自我宣传,受到关注多,能拿到海外资金,不露脸,但得实惠。他俩就是农民,想法简单,做实事,光是自己跑北京的车票,就一迭迭的。”王天明讲。 有一次,一家药厂向一个艾滋病人办的组织,捐了30万元的药。捐赠晚会,要有人接这笔捐赠,人家喊老纪去,老纪真的去了,上台接受,抱着一个30万元的牌牌,实际上是30万元的药。电视播了,村里人看了说:看看,得了艾滋病,人家发大财了。实际上,那次的路费,还是老纪自己掏的。 “农村人,傻呗!”小卫评论道。 夜里11时了,老纪才匆匆忙忙地进门。他长得又黑又瘦,嗓子沙哑,可能是饿了,一坐下就抓起桌上的橘子往嘴里塞。同来的7个病人,有两个因为走得急,没带身份证,旅馆不让住。老纪只好把他俩送到北京火车站候车室,在那儿对付一宿。 我跟老纪说:“你老婆刚才抱怨你,说你净瞎忙。” 老纪“嘿嘿”地笑着,说:“我吧,看着这些病人,病得厉害,家里又特别困难,不忍心。起码,我有了一定的艾滋病知识,对病情比较了解,跟医院能联系上,送他们来北京……” 没等他讲完,小卫不耐烦地打断他:“别说官话了,什么他们重要,没有稳定的家,没有老婆的支持,我们能干成什么?你家孩子丢的时候,你怎么不去工作?还不是赶快找孩子去。”不善言辞的老纪,被他几句话给噎了回去。 看老纪挺尴尬,我跟他开了一句玩笑:“看人家小卫,脑子转得多快呵,见总书记时又准备笔记本,又准备鞋垫的,你怎么什么都没弄呵?” 小卫笑话他说:“他本来是想送一只布老虎,结果人家飘飘然,晕乎乎地,签名本忘了,小老虎也忘了。”老纪没理他,说自己因为激动,只知道双手紧紧抓住胡锦涛的手。 我问他记不记得当时说了些什么话? “记得。他说,你们得这个病是不幸的,现在国家免费给你们提供抗病毒的药,有希望的!” 老纪当初也认为,跟总书记握手,社会上的人看了,村里人看了,会觉得总书记都能跟艾滋病人握手,都不怕,肯定没事,所以不会歧视的。 “结果没有想到。对我自己没什么,但我对不起老婆孩子,让他们受到这么大的压力和痛苦。为了感染者不受歧视,我们站出来,想起到好的作用,却让自己的家陷了进去。”老纪沉默了。 我问老纪和小卫,假如重新选择,会同意再上电视吗? 小卫说,如果不做面部处理,他决不接受媒体采访。但他又表示:如果能把家人安顿好,没了后顾之忧,他还会站出来,做反歧视宣传。“我甚至想拍拍我们一家人是怎么生活的,告诉大家,跟艾滋病人正常交往,是不会传染的,现身说法会是很好的宣传。” 这时,小卫的手机响了,是他妻子从山西发来的短信。小卫让我看,手机上显示的是:“老公,别忘了吃药!” 本报记者 董月玲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