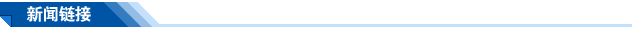《瞭望》文章:力推基层民主制度化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12日09:43 新华网 | |||||||||||
|
发自最基层的民主正受到最高层的日益重视。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此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政策,把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水平。
“当前推进基层民主的关键是贯彻、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 现有法律法规的两大“代表作”,《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均被列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瞭望》新闻周刊从相关部门获悉,国务院法制办已在民政部建议稿的基础上基本完成这两个修订草案,全国人大内司委对此表示认可,并已在今年10月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审议。 制度化链条 1980年,广西宜山县合寨大队(现合寨村)由几头耕牛被盗发端,开展了一场自发的选举,制定出村规民约,实行治安联防。此类基于农民的朴素需求而形成的自我管理方式,拉开了中国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序幕。 徐勇将村民自治称之为继包产到户后的第二次农村体制创新。从合寨大队案例来看,前后不过相差一年。 “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是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呼应的,在基层也是这样。”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对《望》新闻周刊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获得经营自主权后,其权益如何保护,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如何,尤其是“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解体后,公共事务由谁管理、怎样管理,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管理方式。 基于这一新生的需要和管理真空,一些地区的农村群众便通过村规民约等方式,负责管理农田灌溉、防火、防盗等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农民群众尝试的这种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形式,经各级党和政府总结经验,就逐步演变成了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 紧随村民自治之后,城市里也在发生类似的变革。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演进,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许多社会服务性功能,逐步向城市居民生活的社区转移,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功能和地位不断加强,城市社区的基层民主建设工作也就逐步开展起来。 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一并首次写入了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随后20多年,一系列旨在规范和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最有代表性的便是1987年试行、1998年修改后正式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1989年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好经验好做法”上升到“法律法规”,中间还有以文件表达的“成熟的政策”。如在1982年新宪法到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期间,便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86年9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按我的理解,成熟的政策就是指经过试验,可以普遍推广的经验,”刘春说,这体现了中央对基层民主的重视与慎重。 由经验做法而政策再到法律法规,构成了基层民主的制度化链条。徐勇还认为,基层民主理想的目标应是由制度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一样。” 此外,从中央的角度来看,按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的理解,重视基层民主并不仅仅盯在基层,还须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全局来考量其意义。他对《瞭望》新闻周刊称,民主是个大文章,我们党一直在思考、探索民主的着力点,这几年形成了共识,即从基层民主开始,从基层的直接民主开始,逐步发展民主的规模、质量和层次。 中央研究重大问题,除政治局集体学习外,还有一年一度的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等形式,据悉,明年春节后的研讨班也将涉及到“民主”这一“大文章”,而基层民主,自然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四个民主齐推进 民主并不仅仅表现在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同样具有实质意义、甚至是更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农村,“四个民主”都有富有启发意义的基层探索与实践。这也是此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两位讲解老师——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研究员,俱系国内知名“三农”问题专家的理由。 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村民自治在20多年来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以完善“民主选举”为代表的基层试验之路与制度化之路至今仍在继续。 徐勇指出,村民自治从起步就是以组织重建为重心,其相关法律主要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关注焦点长期集中在选举方面。“通过选举,可以暴露平庸的人、不称职的人,乃至坏人和恶人,更可以使优秀的人涌现出来。”叶笃初说,公正的选举是落实民主的基础。 自1987年试行到1998年正式颁布,村委会选举根据各地选举中发生的问题和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得以规范、推广、落实。1998年正式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加了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设立秘密写票处、公开计票、选举结果当场公布等规定,并增加了对选举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和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程序等条款。 此后,以“海选”为突破口的村委会选举发展迅猛,亿万农民开始享受村级民主选举权利。 但“选举”仅仅是民主的部分内涵。随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的暴露,如“贿选”、“罢选”、“撤选”等,一些深化、做实民主权力的探索逐渐进入研究者与决策者的视野。来自基层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好经验好做法大量涌现,有些是对法律法规、政策的细化,有的尽管没有上升为法律法规或成熟的政策,却已是通行的惯例。 如在民主决策方面,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所长张晓山对《瞭望》新闻周刊提到,一些地方采取“议行分离”的方法,使村政村务的决策权与行政权分离,做实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或成立村民理事会,将其塑造成行政村的议决机关,而原来的权力机关村委会则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 在民主管理方面,早在1991年前后,各地农村便纷纷涌现出由全体村民讨论制定出被称为“小宪法”的村民自治章程。据统计,目前,中国80%以上的村庄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建立了民主理财、财务审计、村务管理等制度。 在民主监督方面,村民通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对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等制度和形式,监督村民委员会工作情况和村干部行为。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命题下,公共财政向基层倾斜,大量资源、财富集中到农村,要靠农民的作用,靠农民来约束。”叶笃初说。 两个关键关系 在此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上,胡锦涛强调,要把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从农村多年实践看,完善村民自治,有两个关键关系要处理好,一是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两委关系”,二是村委会和乡镇基层政府的“乡村关系”。 在传统的“村级政治”中,村支书是公认的“一把手”。当村委会地位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里得到明确规定时,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只简单地规定为“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在实践中如何领导、支持,做法不尽一致,由此出现工作难协调等情况。 为解决“两委关系”,基层也有很多可贵探索。比较普遍的就是“一肩挑”。其实现有两个途径,一是鼓励支书参加村主任竞选,一是将村主任推选为村支书。另外,还有山西河曲县的“两票制”:当村支书首先要拿到群众的同意票,才能拿到党员的选举票。 2002年7月,中办、国办曾联合发文,总结基层“一肩挑”经验,对“两委关系”提出过明确的政策思路。 此外,“乡村关系”和谐与否,也直接影响到村民自治的成效。实行村民自治之前,原来的“乡村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而村民自治意味着对这一权力结构的变革,由于矛盾冲突,这一变革过程并不顺利。许多乡村继续维持着很强的行政支配关系,乡镇插手村委会选举,掌管村集体财产,村里还得配合乡里完成各种行政任务。 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曾指出,以往农村基层选举中一些违法违规的情况,有很多都与县、乡政府有牵连。如曾被民政部命名表彰的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市湖北潜江市,在2002年却出现了大面积的村委会成员被乡镇政府非法撤换的事件。 有学者提出,要以法律条文来具体规范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具体划分各自财、事上的权力和责任,从而保证村民的真正自治。 另有学者认为,“乡村关系”变革涉及到乡镇机构改革本身乃至更上层的政府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改革。 与此类似的是,在城市推动社区民主发展时,也面临着如何摆正居委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介入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行为的情况时有发生。 民政部推动社区民主发展时,设立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社区居民委员会与政府的分离。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也指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刘春表示,这个方向很对,但职能边界怎么划分,基层行政事务如何落实,还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深入研究。 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都曾在社区试验过“议行分设”制度,目的是把社区居委会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推进民主自治。 而深圳市从2005年在这方面探索了另一条路,在部分辖区范围内,把社区居委会承担的所有政府职能单独剥离出来,仍然以社区为单位,成立一个政府工作站。 在徐勇看来,这种“行政事务一竿子插到底”的新模式,可以使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真正专注于社区公共事务。(记者 汤耀国)
基层民主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迅速变化,利益多元化和主体平等竞争格局逐步形成,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正在要求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全球化浪潮也大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政治视野和参与冲动。在农村,村庄内部出现多种经济利益主体,村庄已经成为对外开放的社会单位,特别是人口流动为过去相对稳定的村庄生活带来了诸多变量。在城市,社区里的成员越来越不具有“单位”特征,“单位制度”的社会整合能力大大削弱。城乡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流动开放的社会。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本身,使社会管理和利益整合的难度增加。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具有日益深厚的利益基础和能力基础,政治参与正在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的城乡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和自治组织选举中,个人主动竞选迅速增加,“罢免”案不断出现,显示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升。>>>点击详细 来源:瞭望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