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何怀宏:中国很难有陀斯妥耶夫斯基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1日10:41 南方人物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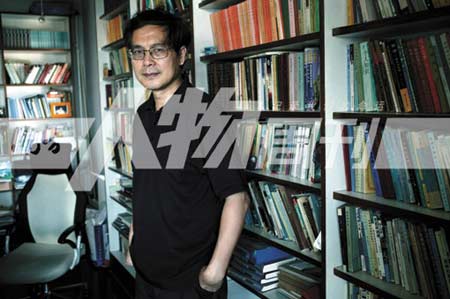 何怀宏 图-姜晓明 人物周刊:您翻译的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非常精彩。关于翻译,王国维先生要“不隔”,严复先生说“信达雅”,您追求的是什么? 何怀宏:在哲学范畴肯定首先是达意。信是转为准确的中文,又不失原意的流畅。我觉得文学作品翻译可以讲究“信达雅”,其他著作“信达”就可以了。“雅”是严复所处时代的特殊要求,那时主要读者还是士大夫,基本都在文言文的世界里,所以严复强调的“雅”其实是带有文学性、尤其是文言文的味道。这个“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翻译的那些著作的传播。他的译作的选材和翻译都是很好的,但是没办法在今天大量重印,就因为他的文言文翻译太雅了。 人物周刊:外语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请您评价一下翻译文体对中国思想界的意义。 何怀宏:不仅仅是开了一扇窗、一扇门,而是让人们走进了一个新世界。因为文言文没办法很细致地构建、分析、推演,譬如先秦著作,《论语》是语录式的,《荀子》、《韩非子》有些推论了,但还是受语言、文体的限制,无形中对思想的约束肯定是存在的。 我们现在借助的工具、概念基本上是西方的,没有这些现代哲学没办法做好。但中国传统中有些概念我觉得很需要发掘,赋予它们一些新涵义,就像我在《良心论》中引入的8个概念:恻隐、仁爱、诚信、忠恕、敬义、明理、生生、为为,这是我的尝试。 人物周刊:您对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好像还有一个不满足:基本上是史的考证,不见问题。 何怀宏:作为思想来讲,中国的古代著作会令人感到不满足。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差异,有点像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中国有一些很美的音乐,像《春江花月夜》,有一种西方人不容易把握的韵味,但相对来说,它的表现力弱,只有悲伤或欢快,但人的不高兴也是有很多种的,这时你会发现西方音乐提供了一个浩大的世界。哲学思想上也是这样。 中国人更表现出一种智慧而不是思想。这智慧在某种意义上是重述的智慧,重就是重复,许多东西是述而不作,或者以述为作,很不容易创立新的概念。比如相对《左传》、《尚书》,司马迁算是一个开创者,他用编年体写史,后人就学他,都是编年体,一直都没有变化,包括《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算是学术史,但基本上是文献的汇集。这个好不好呢?我觉得一方面要理解它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少数本来有开创能力的人,可能因此受到无形的束缚,因为形式、题材、时代的限制,没能开创新的格局。所以中国不容易出现很多种不同观点的、而且是追根究底的思想家或学者。 人物周刊:中国很多学者好像都是先国学,后西学,然后又回到传统中去寻找资源。这好像也是您的路径,您觉得走得通吗? 何怀宏:我现在最喜欢读、读得最多的还是西方哲学。中国的资源很值得开发,但我觉得不可能有一个可以应付现代世界的宝库在那儿。首先量上不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动辄上百万言,老子只有五千言,孔子也不多。我对传统更多的是理解和尊重,也会去学习,但并不意味着我要另起门户,从中开发甚至销售。 中国很难有陀斯妥耶夫斯基 人物周刊:您花那么多精力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不是因为他的问题意识? 何怀宏:对。他的问题意识中最深刻的部分是把时代和永恒、信仰和社会都结合起来了,里面有最切实的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同时也有宗教信仰和精神渴望。这在英美或德国思想家著作里是看不到的。 人物周刊:他预言过俄国大革命和斯大林主义的出现,这种先知先觉您觉得是怎么来的? 何怀宏:文学家的直觉非常好,应该说其他人也有过这方面的思考,但不像他那么……他是非常敏感的。另外他自己的一些经验,比如被人抢劫过、在西伯利亚当过囚徒、终生贫困等等,让他对人性的体验和认识非常深,他也曾经结识过革命者,了解他们的理论,所以这不奇怪。 人物周刊:陀斯妥耶夫斯基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人人为自己,物欲赤裸裸地膨胀——到了今天,这些问题依然没有改观,是不是某些问题永远存在? 何怀宏:对,有些问题是永恒的。对问题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很重要,比如说人有一种精神的渴望和追求,这固然很有价值,但如果抱着对人性不切实际的看法,采取一种错误的形式,比方流别人血的形式——《日瓦戈医生》里描写的俄罗斯的革命就是这样,把以往一些精神的文化的优秀东西一股脑地摧毁掉,就可能付出很大代价。 中国也是如此。像杨显惠写的《夹边沟纪事》,那些人就那样没有尊严地死了,比野兽都不如。这个代价是否值得?我们经过了这一切,人的精神、道德到底有没有提升呢?没有。 人物周刊:您是性恶论的支持者吗? 何怀宏:我没有,我是心平气和。善端恶端都是存在的,对人、对大多数人不能估计过高,要有一种恰如其分的估计。托洛斯基说的“革命之后,教育普及了,每个人都可以是大学生,都可以达到歌德、但丁的水平”,这不可能。一个人也许不能成为歌德,但他有一颗淳朴的心,可能他的精神、道德境界是一个大学教授都望尘莫及的,而且他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不需要看康德,这是可能的。就像我祖母,她的那种善良令我非常感动。 我可能偏向性善论多一点点。比方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善端有恶端,但是善端要多一点点,多一点点就不遗憾了,就有决定秩序的天平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觉到,无耻毕竟是少数,恶人还是要伪装,善还是占上风的。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状态能激发人性中恶的部分? 何怀宏:比如说制度不理想。有时候在理想主义和物欲主义之间不辨方向,理想破灭后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物欲横行,赤裸裸。 人物周刊:革命呢? 何怀宏:容易把人的残忍、邪恶调动起来。因为是革命嘛,为了一个最后、最高的理想,可以激愤、暴虐,可以对别人做突破底线的事,所以“文革”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有的红卫兵冲到盲人学校,把持不同观点的盲人捅死;或者告密;或者是风华正茂的女孩子突然发疯一样把慈祥的校长打死。你说那些打人者就是坏人吗?也不是。但是在那种群体性的气氛中他就可能那样。 最后往往是坚定的温和者取胜 人物周刊:您觉得今天的中国需要哪些思想资源呢? 何怀宏:自由主义我把它看作一个底线,它的涵义是不要强制,尤其是手段的正确,不可伤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但其中也有一种恻隐之心。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激进者和“沉默的大多数”? 何怀宏:我相信许多激烈者的态度是气质或处境使然,他们渴望燃烧地表现自己。而在一个有点昏昏欲睡、甚至死水一潭的社会里,我们也希望听到一些激越的声音,希望思想空间因此而扩大;也正是一些激进者首先冲破限度——我们得感谢他们,虽然他们有时也冲破一些有益的“限度”。 但是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平衡。激烈的左右摇摆或互相攻击常常代价太大,有时甚至动摇了根本。 虽然中国在向新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经济成就和法律成就,但还不是建立在很稳固的基础上。所以是不是应该考虑更多地借重一种中间力量、中间态度?也就是说,应当有意识地让温和成为一种中坚力量,主要的、建设性的力量。 极端的声音是比“沉默的大多数”更能引人注意,但应该有一些坚定的温和者,他们该成为中坚力量——对人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个人行为有坚定的原则并坚守底线:不伤害无辜者,不污辱哪怕有罪的人。他们最优秀的德性大概是坚韧,而坚韧也许是今天最值得推崇的一种品质。他们也有激情,但这种激情更多地表现为长期沉潜的功夫,而不是一时的兴奋和张扬。温和常会让人觉得不过瘾,但许多事最后往往是坚定的温和者取胜。 (感谢董晓丹对本文的贡献)
【发表评论】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