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十年的阅读记忆(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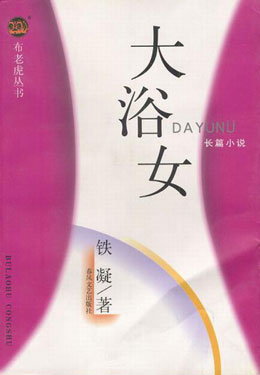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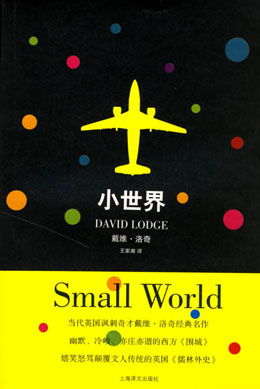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文/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这种零乱的阅读状态中,好像也有一条阅读的主线或明或暗,隐隐约约。它蜿蜒在上世纪90年代的悠闲中,也延续在新世纪的匆忙里。我说的是米兰·昆德拉。
上世纪80年代轰的一声就结束了。我又回到了那座小城,90年代也悄然而至。
铁凝在《大浴女》 中说:“90年代什么都是一副来不及的样子,来不及欢笑,来不及悲伤;来不及恋爱,来不及失恋;来不及倾听,来不及聊天;来不及吃醋,也来不及产生决斗的气概。”有这么多的来不及,我想来不及读书也该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但我生活的那座城市格局小,气候好,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它有效地阻挡着外面的喧哗与骚动,也有效地调理出人们的平静与闲适。所以,我似乎还是读过一些书的。
但我的书却读得零乱而不成体统,一副乘兴而行,尽兴而返的样子。王朔横空出世了,我就读王朔;新写实火了,我就读新写实。有一阵子,张承志饱受争议,张承志的书就又一次走到我的案头;有一阵子,为了写一篇文章,我把《赵树理全集》通读一遍;还有一阵子,我把《张爱玲文集》买回来,计划通读,却只是读了她的一些散文,小说死活读不进去。1993年,为了写一本小书,我读的是卢梭与伏尔泰;1996年前后,我把“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之类的红色经典重读一遍,原因是正在上一门当代文学史的课。1996年春节前夕,我读完《丰乳肥臀》,觉得有话要说,就写一篇长文。我在漫天大雪中把稿子投寄给一份重要刊物,结果如泥牛入海,我却因为这篇文章,生了一场小病。1997年,王小波英年早逝,那一年我似乎就把阅读全部交给了王小波。1998年,我意外地读到了戴维·洛奇的《小世界》,结果他的五本小说和一本谈小说的书就全部买回来扫荡一遍。我对戴维·洛奇并不陌生,读研究生时,我曾托师兄从南京买原版书20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那本书就是由他主编的。只知道他搞理论有一套,却没想到小说也写得这般有趣。
我也开始读弗洛姆、马尔库塞和海德格尔,读那些能够买到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读,大为震动;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读,非常震撼。《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读了一遍,似乎没读懂,却觉得迷人;《伊甸园之门》读过去,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化已尽收眼底。
我似乎还制定过一些庞大的读书计划,比如我想通读一遍鲁迅,通读一遍沈从文,但我还没来得及认真执行,就把上世纪90年代稀里糊涂过完了。
在这种零乱的阅读状态中,好像也有一条阅读的主线或明或暗,隐隐约约。它蜿蜒在上世纪90年代的悠闲中,也延续在新世纪的匆忙里。我说的是米兰·昆德拉。
对昆德拉的阅读,我是先读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又读他的《生活在别处》,从此开始了对他的迷恋。那个时候,昆德拉热在中国方兴未艾。昆德拉是一个流亡作家,他体验过极权主义统治的荒诞,又以小说的形式不懈地开掘着苟活之个体、扭曲之人格的存在状态。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读过五六遍,正是在对昆德拉的不断体悟与玩味中,他度过了精神上的困顿期。我想,许多人可能都会有与他类似的感受吧。突然的变故之后,一些人在读金庸,那是一种逃避;一些人却选择了昆德拉,那应该是痛定思痛般的重新上路。
就在那种暗淡、沉闷甚至苟活于世的心绪中,我开始了对昆德拉的搜集与阅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生活在别处》都是先读后买,前者1989年12月购于济南,后者1991年11月购于长治。1990 年元月,《为了告别的聚会》在长治买到。1992年9月,《玩笑》代购于北京。1993年,《玩笑》的另一译本面世,我又买回一本。1992年10 月,《不朽》托人代购于太原。1992年11月,《小说的艺术》邮购于北京。1993年5月,《笑忘录》在太原买到。1994年11月,《可笑的爱情》邮购于郑州。1996年3月,《被背叛的遗嘱》邮购于上海。1999年4月19日,《本性》在我复试的北师大买下。1999年12 月,《缓慢》购于北师大门外的一家小书店。2000年12 月,《认》购于北京国林风书店。2003年,上海译文推出“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13本,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重译,起初我犹豫着,只是买回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不朽》与《雅克和他的主人》,最后我终于决定把它们悉数拿下。2006年3月,我在新加坡上课,见昆德拉的最新文学论集《帘幕》已被台湾译出,立即决定购买。又看到台湾版的《米兰·昆德拉全集》置于架上,甚是可爱,也想全部背回,无奈囊中羞涩,不敢造次。我只是挑出一本《不朽》留作纪念。而那两本书加到一起,已是45新元,折合人民币200多块。2006年9 月,《帷幕》也在大陆面世,我又把它买回来,这样,对照着读《帘幕》和《帷幕》,就成了我在2007年春节前后的主要事情。
现在想想,如此迷恋昆德拉,我究竟从他那里读到些什么?也许是那种政治与性之间的无限张力,也许是那种思与诗的有机融合,也许是小说中的音乐结构,也许是那种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写法,也许是他所发明或经他阐释又重新闪光发亮的语词概念:意象形态,媚俗,缩减,快与慢,轻与重,存在的被遗忘。有人说昆德拉只是一个二流作家,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我有一个奇怪的观点,衡量一个作家是否伟大的标尺之一,是看他是否有清晰坚定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是否又被他表述成了理论文字。比如,假如没有那些“论文艺”的文章,巴尔扎克就显得黯然。假如没有那些“论艺术”的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够完善。纳博科夫不仅有《洛丽塔》,还有《文学讲稿》。卡尔维诺不仅写出了漂亮的小说,还写出了同样漂亮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诗人奥登说:“绝大多数读者可能都难以接受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里所下的结论,但是,一旦我们读罢这本书,我们就再也不能漠视托尔斯泰提出的那些问题。”这就是理念与理论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所以,如果没有《小说的艺术》 《被背叛的遗嘱》和《帷幕》,我真不知道昆德拉会是什么样子,他还能像现在这样在我的心目中如此重要吗?
当然,我也从昆德拉那里读到了他对政治的形而上思考。昆德拉说:“我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这个时代。我听到我所崇敬的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公开正式地与他的布拉格朋友脱离关系,因为这位朋友即将被斯大林的最高法院法官送上绞刑架。这个事件(我把它写进了《笑忘录》)使我受到创伤: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再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得成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进步与革命。青春。母亲甚至人类。还有诗歌。”
近朱者赤,昆德拉的幽灵开始在我的文章中游荡了。但惭愧的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写过一篇关于昆德拉的像样文章。2004年,香港一位同学欲来北京求学,复试时她说她喜欢昆德拉,并且想以昆德拉作为她的硕士论文研究对象。我大喜,便把她收入自己门下。如今她已经毕业了,论文也做得不错,我感到欣慰。我曾经动过研究昆德拉的念头,中、英文的资料也弄了一堆,但我一直拿不出时间,也似乎一直没有准备就绪。昆德拉心仪拉伯雷、塞万提斯、卡夫卡和哈谢克,对于他们组成的文学传统,我还知之不多。我的学生进入昆德拉的研究领域,于我也许是一种缺憾的补偿。我似乎还在期待着,牵挂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