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牺牲者都会永垂不朽(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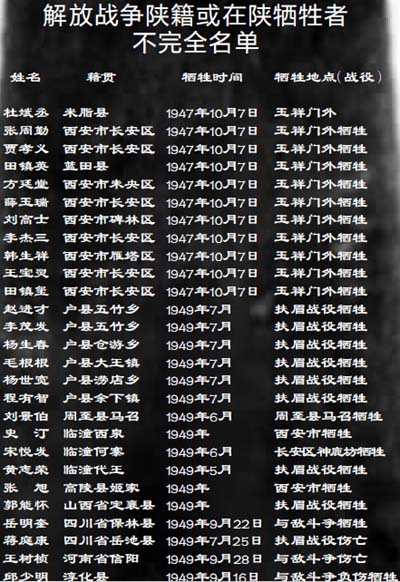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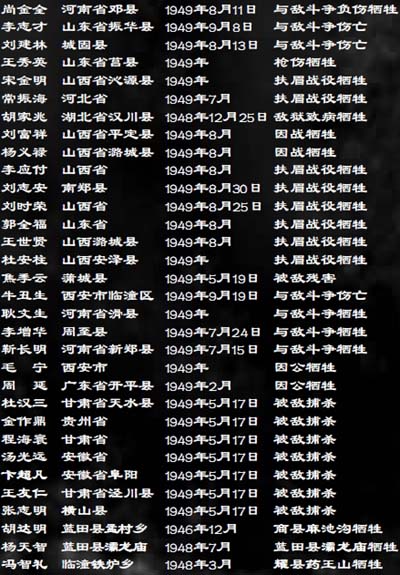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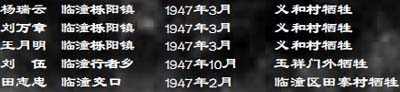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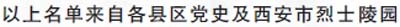 |
 |
受中共西安工委指派,向第一野战军送情报并带领解放军攻入西安的中共党员刘洛克
每一个牺牲者都会永垂不朽。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无疑每一个牺牲者都应该被记住、怀念和感谢。
在黎明的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却奔赴战场、走向刑场,用炽热的心迎向敌人的子弹和刺刀。他们永远看不见自己为之奋斗的黎明,但他们用生命照亮了我们的天空。
特务将他活埋在离家几里的地方
1949年6月21日,周至县马召镇东火村,是夜,年仅8岁的男孩刘建哲和9岁的哥哥刘大勇,紧紧地抱着母亲,不安地东张西望。蔓延在家中好几天的那种压抑的气氛,让这两个孩子委屈地憋着眼泪,却不敢出声。
十几分钟后,家中忽然人来人往,“景伯走了,你们节哀……”虽然一直有预兆,但这个消息真实来袭时,母子三人的哭声还是划破了暗野长空。
年幼的记忆,总是容易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模糊不堪,可那些刺痛心灵的瞬间,却像在心脏中直插进的一支钢针,不知何时就忽然会隐隐作痛。
很悠闲地坐在自家的摇椅上,轻轻地晃着,原任国棉十一厂副厂长,现年68岁的刘建哲,努力用一种十分放松的姿态来回想这段历史。
在当时8岁的儿子眼中,父亲总是形迹神秘。1947年刘景伯回到家乡周至,以当地“知行小学”校长的身份开展地下党活动。父亲总爱穿着白西服,拄着一根黑色“文明拐”,他爱骑马,飒爽英姿的骑姿常常引得地里干活的人们仰头打量。他很高傲,一般不跟常人讲话。他爱吃孩子们觉得难以下咽的菠菜,说这里面藏着金子。
1949年5月30日,周至解放。6月20日,秦岭守备区特务连长仝树林率士兵闯进村子,在邻居家中将刘景伯抓获。“他们先戳瞎父亲的眼睛,再在脸上戳……”说到这里,刘建哲突然捂住脸痛哭起来。特务连夜挖坑,将32岁的刘景伯活埋在离家只有几里的地方。
父亲说他是提着脑袋办事的
父亲张周勤的陵园,就立在街道尽头,长安区马王街办张海坡村76岁的张建国老人每天出门,都能不经意地看上一眼。
张周勤烈士1917年出生。和妻子结婚才三天,就只身一人去了延安。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陕甘宁保卫处派张周勤到西安侦察敌情。父亲一回家就一头扎在书堆里,儿子问时,他只说:“你爹干的是脑袋提在手里的事儿,你少问!”张建国明白父亲干的事很危险,但具体脑袋怎么个提在手上,好奇的儿子无从知晓。
1947年1月,国民党白色恐怖蔓延,张周勤在西安收集西安地区反动组织的人事情况,3月下旬,组织派他到新疆去隐蔽,可就在他起程的那一天,国民党政府下了逮捕密令。
3月29日这天,张建国天不亮就赶往大原村小学读书,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母亲眼睁睁看着丈夫被赤脚抓走,她能做的,只是趴在地上,对着来人不停地磕头。
面对酷刑,张周勤始终泰然自若:“肉是你们的,骨头是我的!”被打得遍体鳞伤,腿骨被压断,几次昏厥过去又被浇醒,死而复苏达五次之多,最终于当年10月7日就义,时年31岁。本报记者王宜墨
离合
战争留下永恒伤痛
逃到四川,全家一贫如洗
西安解放那年,李凤娥才12岁。那时候,她和父母、姐姐住在甜水井附近,5月20日那天,外面“砰、砰、砰”一阵枪声,吓得李凤娥浑身发抖,抱住妈妈的腿,死也不肯松开。
那天,父亲李耀明也在家,他说出去看看动静,就披了一件旧衣服出了门。但没过多久,他回来一边叫妻子赶快收拾东西,一边叮嘱女儿说要逃难了,在路上不许哭。当时父亲做生意,家境还不错,担心解放军像说的那样要“共产”,决定跟随“国军”入川。
一家四口提着包裹,出门就往南跑。为了安全,父母分开走,父亲带着家里的财物,追着“国军”走;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解放军怎么也不会为难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到了成都一家人再会合。
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李凤娥,拉着14岁的姐姐李凤霞,一路南行,从沣峪口进入秦岭。累了,找个干净的地方就地而卧,或找个人家借宿一宿,几天工夫,娘仨完全变成了一副逃荒者的样子。
在逃难途中,李凤娥母女三人遇到解放军,应该是在安康的一个镇子。
一个在树底下的解放军,掏出一个黄铜色的子弹壳,笑眯眯地递给了李凤娥,李凤娥扭头就跑,那战士说:“害怕什么?叔叔又不会吃了你!”
“早知道解放军是这样的话,就不让你爸跑了。”后来李凤娥经常听到妈妈这样抱怨,但父亲已远在四川,一家人总还是要团聚的。
直到1950年春,母女三人才辗转到成都见到父亲。而成都也已在1949年12月底解放。
但家里变得几乎一贫如洗,因为跟随“国军”南撤中,为了在乱军中寻求庇护,李耀明将随身带的财物都“上供”给了一名“国军”少校。
一辈子都在找家的老人
16岁被国民党军队从河北老家“拉壮丁”,到西安解放,再到1981年去世,闫庆禄也没能回到河北老家。
闫庆禄本名不叫闫庆禄,在家乡,他只有个小名,叫“来福子”,在“国军”中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来福子的家在河北阜平县,16岁以前,除了邻近几个村子,没有到过更远的地方。16岁那年,“国军”到村里“征兵”,来福子在旁边看热闹。不想被“征兵”指挥官看上了,“能吃饱饭,冬天有衣穿……要不去,就是犯法,要吃官司坐牢。”
就这样来福子当兵了。打完日本人,又和“共军”打。几年下来,部队频频调防,他稀里糊涂地也就来到了陕西。随便在西安城对着天胡乱放了几枪,来福子就又跟着长官往“大后方”撤。撤到汉中,来福子负伤了。
很快,“国军”“转移”到了“大后方”,来福子和部队失去了联系。伤好后,闫庆禄就在川陕交界处定居下来,娶妻生子。来福子是个小名,自己连姓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自己村里大多姓闫,来福子就决定姓闫,大名也好取,就叫庆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来福子开始寻亲。他只记得村子好像叫土洞子沟。听长官说,是河北阜平县,但土洞子沟在什么乡就不知道了。
通过政府机关给河北阜平县发函,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个村子!”子女们还曾先后两次赴河北,也没下落。
1981年,闫庆禄病逝,在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还是故乡。本报记者 何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