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孺童: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
 |
人民网文化频道7月11日电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听闻噩耗,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秘书长王孺童在自己的博客中忆起了自己三次亲近季老时的情景。
王孺童博文: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
2007年1月26日下午,我前往北京301医院,看望了96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当季老得知我在新浪博客开专栏讲解《论语》,并即将出版《孺童讲〈论语〉》(第一辑),欣然为我提笔题字。这使我在无限欣悦之余,有深感不安。
为我这么一个晚辈的私事,而烦扰身在医院的季老,这是“一不安”。季老是学贯中西、蜚声内外的著名学者,我书中的内容是否能够不辜负季老对后生的提携,这是“二不安”。季老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指出“21世纪是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的世纪”,而且经常勉励青年人,要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我之所以后来能够走上研究国学和佛学的道路,与像季老这样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老一辈学者的人格感召是分不开的。虽然我现在也是以一种使命感,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是否能够真正为中国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一点实质性的贡献,仍有些心头茫然。这是“三不安”。
我第一次亲近季老,是在1998年5月16日。其时正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只身来到季老在北大的家中。给我至今都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在季老会客室的一面墙壁上,从地到顶,整齐摆放的一套《四部丛刊》。在与季老的交谈中,身感季老的平易与谦和。季老指着一幅放在窗前的画说道:“这是欧阳中石给我画的《季荷》。一般大家都知道他是书法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能画画。”其间,我也亲眼见证了,季老对他那只爱猫的宠爱。临行时,季老将他刚刚出版的《牛棚杂忆》一书,签名赠送给我一本。我记得当天回家之后,就把该书一气读完。后将心得写了一篇《季羡林与〈牛棚杂忆〉》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主办的《博览群书》杂志上。
我第二次亲近季老,是陪我外公到北大的季老家中。那是1999年的一天,我外公由于正在改编《聊斋志异》的电影剧本,所以想向季老请教有关“地狱”的问题。季老向我外公推荐了一部中国古代典籍《玉历至宝钞》,可以作为参考。两位老人相见甚欢,在交谈中,季老用手一指我,对我外公说:“小明,可是个作学问的人。”季老这句不经意间的话,使我感到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对我当时,乃至后来从事学术研究,都起了极大的影响。
之后,由于季老年事已高,不忍打扰,故在关注季老各种消息报道的同时,只在过年过节时,给季老秘书打个电话,转达问候。
2006年8月6日,从《新闻联播》中看到温家宝总理给季老祝寿的新闻,见季老仍然思维敏捷,话语清晰,便有了再去看望的想法。国庆节前,我历时7年完成的《比丘尼传校注》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了,这就更促使我想去看望季老了,因为总算有个像点样的成果,能向季老汇报了。
2007年1月26日下午3时,在杨锐老师的安排下,我来到北京三○一医院,第三次亲近了季老。我先向季老转达了我外公对季老的问候,并将《谢铁骊八秩影画集》和《比丘尼传校注》两本书,赠送给了季老。随后,我向季老汇报一下,我在近一段时期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当季老得知我在撰写有关注释《论语》的书籍时,季老对我说:“现在国家在编纂《儒藏》,《论语》是儒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书。”当时,我突发奇想:“是否能请季老给我即将出版的《孺童讲〈论语〉》,题写书名呢?”但又顾及到季老的身体,几经思想斗争,最终硬着头皮提了出来。出乎意料的是,季老欣然同意,并当下提笔书写。
由于怕影响到季老的修养,我不敢久坐。我每次拜望季老,季老都不会让我空着手回去。在我告辞时,季老又将他新近出版的《病榻杂记》和《季羡林论佛教》两本书,签名赠送给我这个“小友”。
《病榻杂记》收录了季老在住院期间,所撰写的近百篇文章。其中最为重要,也是为当前社会最为重视、广为传诵的内容,就是季老的“三辞”——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术)泰斗、辞“国宝”。季老在书中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是何等的“看破”、“放下”、“自在”呀!
为了尊重季老的决定,故我在本文中只称季老为“先生”、“学者”。最后,祝季老福体康健,寿与天齐!
季羡林与《牛棚杂忆》
在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我有幸拜访了季羡林先生。见到季先生的时候,确有一种一见如故之感,因为他那一身简朴的装束,与在电视报道中的一模一样。使我略感到有些新奇的是,这样一位年近九旬高龄的老人,十分宠爱地养着一只白猫,我想这恐怕就是所谓的“反朴归真”、“反婴还天籁”吧。季先生十分平易近人,而且又不失饱学之士的那种深不可测的博大内涵。言语之间,十分自然地就提到了季先生新近出版的《牛棚杂忆》一书,这是季先生注入心血的一本著作,故而说起来季先生也就十分津津乐道,感触颇深。在我告辞之际,季先生向我这位“小友”(可能是季先生对于晚辈的爱称)赠送了一本《牛棚杂忆》。我能够得到季先生亲自签名赠送的《牛棚杂忆》是十分欣喜的,到家后,当下阅读,颇多感想,季先生平直而略带黑色幽默的笔触,使我对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年代有了一个形象化的认识。下面的文字,记述了与季先生的这次谈话,同时也杂以笔者的一些心得。
“心”与“血”的回忆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这是季先生在《牛棚杂忆》一书卷首的祝词,这些平凡的文字所蕴涵的作者的思虑是深邃的,我难以用别的言语来代替和诠释它,只能让看到它的人去心领神会了。在我通读全书之后,我更加体会到这段“祝词”放在书首的意义,它是全书的创作主旨,是全书的构架灵魂,是作者心灵之声的文字反映,更是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之所在。
我和季先生刚一谈到此书时,季先生当即对我说了如下的话:“我写此书的目的不是秋后算帐,不是向某些人进行报复。我觉得应该把那一时期的历史真实地告诉后人,尤其是像你们这样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年青人。现在有时对他们讲起那段历史,讲起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他们会觉得你所说的子虚乌有,全然不会相信。这更使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所看到的写出来,留给后人,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才是我写此书的目的。”我想这段话是一直贯穿着季先生全部创作过程的,也是把握整个作品基调和风格的重要原则。因为过去有很多类似于回忆录的纪实书籍,写到最后就成了“牢骚集”、“大骂集”,丧失了一部作品应有的含蓄性和艺术性。而《牛棚杂忆》则不同,全书没有因自己的不同寻常的遭遇而大发牢骚,也没有因为一些“人”对自己的特殊照顾而“破口大骂”,反而在书中多处出现感谢之词。如在第一节“缘起”中,就写道:“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我居然躬与其盛,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此处为示部旁加一个右字),以至于感激涕零了。”像这样的言语在书中随处可见,难道季先生真是对此“文化之运动”怀念感激吗?非也。我认为本书的成功之处,正是季先生运用了这种类似于“反语”的风格的表现手法,内含悲痛的祗(此字下无一点)谐笔锋,将这一历史事件成功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全书语言平直,用词没有尖锐之处,但使人阅读起来无时无刻不被一种难以名状的茫然和惶恐所笼罩着,使我觉得这段历史在季先生的心中,是最为不想记起而又无法忘却的。此书可以将读者的神识领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可以在读者的心中再现那一幕幕史无前例的情景,这无愧为季先生用“心”和“血”凝成的作品。
这段历史对季先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是触及到灵魂的,这在全书中无不反映出这样的情绪。季先生学贯中西,一生著述颇丰,但好像在他的心中,此书的地位是最至高无上的,是他最能感到对社会、对后人有所贡献的著述。
如 实
同季先生谈话,给我的最大直观感受是,季先生这个人比较如实,就是说,他说话比较直接,有什么说什么,没有任何的掩饰。这正如佛语所说 “直心即菩提”。
当谈起当年季先生的求学道路时,季先生的回答使我感到“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这在他《牛棚杂忆》的附录“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和“季羡林自传”中均有体现。当提到在北大和清华都录取先生时,为何先生选择了清华大学呢?季先生说:“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牛棚杂忆》之“季羡林自传”)这种选择大学的心理过程,我想在当前的年轻学子中也是比较多见的。当问起季先生为什么想出国时,季先生的回答更是出人意料,他说:“就是想出国镀镀金,回国后好找工作。”此语一出,使我感到季先生在那个年代的思想同现在也有相近之处,也可见季先生心智之开明,胸怀之坦荡。
对于《牛棚杂忆》中的内容,季先生说:“我书中所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如果我没有亲身体验过,我是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故事的。”这也正如季先生在《牛棚杂忆》第一节“缘起”中写到的那样:“我在这里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所以我在读完此书的一个感受,就是两个字“如实”,语言如实,内容如实,思想如实。
季先生是本着如实原则进行写作的。书中的“真实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文革”初起的描写。因为季先生当时是在北大工作,其了解到的社会政治情况基本是以北大为中心的,或者说是在北大范围内的,所以季先生在书中并没有宏篇大论地讲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只是从“社教运动”开始,然后由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逐步引入的。其次,就是对“文革”期间种种事实的描写。季先生只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或亲眼目睹的事件进行描述,对于其它事件,哪怕是十分著名、众人皆知的,但由于当时只是耳闻未曾眼见,在书中均基本略去或进行了十分谨慎的提及,反映了他一贯严谨的学风。再次,就是对人物及事件的评价。季先生在整个书中以最大的力量不将个人的得失感情注入到对人物及事件的评价当中,尽可能的以一种理性的客观立场,客观的评价了这场运动。在书中很少能看到“定性”的话,季先生只是将事实摆在人们面前,让读者去评判是非。最后,就是对“事”不对“人”。这一点我想引用季先生书中的一段话来作说明:“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从中可以看出,季先生写此书的目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作为一面“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的镜子,留给后人。
回忆“法”与“非法”
法,是佛教术语,是泛指宇宙的本原和道理。而非法,就是指不符合宇宙本原和道理的道理。我这里当然不是要宣扬佛教的教理,只是暂且借用一下。我所谓的“法”,是指法律,而“非法”是指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季先生在书中,反映出在当时那种是非混淆的时代,在自我观念中的“法”好像全变成了“非法”,反而那些原本是违法的行为却成了社会主导的中坚力量。
我在阅读《牛棚杂忆》时,能够使我发出苦涩一笑的是,季先生多处用佛教中的一些典故和理论,来比喻和描写当时一些事件,从而使文意更加深刻。在第一节“缘起”中,季先生就很自然地将地狱、牛头、马面等和当时的“革命小将”及牛棚联系起来,他写道:“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狱的描绘。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呆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手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从中可以反映出季先生对当时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生活环境的深刻记忆。
季先生在书中运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没有法制可言,可以随便地打人,随便地整人,随便地折磨人。其中,花样百出的手段,无端“莫须有”的“罪名”,以及受害者可悲的服从和可怜的下场,让人读后实是令人发指。其中令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季先生对于“挂木牌”的描写:“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一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地心吸力把钢丝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鲜血直流。”(《牛棚杂忆》之“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像这种惨无人道的描写,在书中还有很多,就不多举。但值得一提的是,季先生总是以一种祗(此字后下一点)谐嘲讽的语气,来描绘这一幕幕血淋淋的画面,足以表达出这位历尽沧桑的老学者,对这段历史的人生态度。
知识分子的劫难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是老子在《道德经》第三章中的话。我想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到了上面这四点,是否能躲过这场劫难呢?
季先生在书中描绘了身边知名的、不知名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悲惨的遭遇。在“牛棚生活(二)”中,就集中记述了七位男、女知识分子的不同经历,我想在这里仅举“附小一位女教员”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有一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教员胳臂上缠着绷带,用一条白布挂在脖子上。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几天一个夜里,在刑讯室受过毒打,以致把胳臂打断。但仍然受命参加劳动。”像上面这种例子在季先生看来只是一些“棚中花絮”,他指出:“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难友们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遭遇,以及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虽是小事,却小中见大,颇能从中窥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点。”(《牛棚杂忆》之“牛棚生活(二)”)
人之最为悲惨的,或是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自杀”了。季先生称之为“自绝于人民”。这一人生最为悲惨的命运,就发生在了有着很深“士可杀,不可辱”思想的知识分子身上。作为对佛学很有造诣的季先生,深知佛教是禁止自杀的,是否他就能超然看破度过此劫呢?季先生没有自我掩饰什么,而是把他当时的真实思想,在书中运用了两节的篇幅,作了真实的描述。
“这难道是一个人过的日子吗?”“我在思想感情中,也在实际上,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进又是刀山火海。我何去何从呢?”“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唯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身后是非谁管得?’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牛棚杂忆》之“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这是季先生当时思想活动的真实写照,我想也是大多数选择“自绝”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人们的思想过程。季先生以个人为例子,以小见大,从而反衬说明当时整个社会这一知识分子的特殊现象。
有趣的是,在书中季先生对于“如何自杀”这一问题,作了细致地描写。如吃安眠药、投湖、卧轨等等。之所以季先生能够想到上面种种方法,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人亲身实践过了。所以书中在这一部分,并不只限于描写自我的思想活动,而是以此为线带出了很多含冤自绝的血的事实。
季先生自称自己“创建了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牛棚杂忆》之“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经过了如此一番精密思考后,季先生也准备“理论联系实际”,但为何又“自杀未遂”了呢?这还要感谢是红卫兵救了季先生。在我读到这里时,我感觉这是十分戏剧性的。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反正性命是拣到了。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牛棚杂忆》之“千钧一发”)
我在前面提到过,季先生在《牛棚杂忆》一书中很少有定性的话,但是在书第二十节“余思或反思”中,对于“文革”却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我认为这是季先生个人以及整本书的立场观点之体现,因为对于一个像这样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总得要有一个评价的标准,否则洋洋万言又所谈何物呢?
我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后生晚辈,在读过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后,实觉受益匪浅,这种受益不光是了解了历史,而且从文学创作角度也受益良多。我在与季先生的谈话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这位学术界的老前辈,对于学术领域以及青年一代,所倾注的关怀和期望,也使我深感《牛棚杂忆》一书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由于季先生谈及该书时的一些话与书中所言相近,又为了尽量使读者能了解本书的原貌,故采取了“引述”的方法,特此说明。总而言之,希望大家都能去读一读、看一看。
(原载光明日报社主办《博览群书》杂志,1998年第9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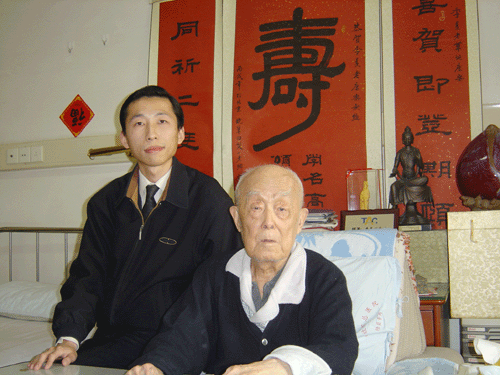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