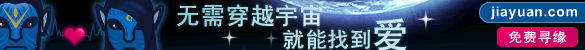盛世北漂陈冠中
盛世北漂陈冠中
撰稿/何映宇
因为《盛世——中国,2013》,陈冠中登上了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在封面上,和他“唱对台戏”的是美国未来学家、《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的大头照片。显然,在《亚洲周刊》编辑的眼中,陈冠中也是一位预言家,他居然能将2012年的下一年作为时间背景来写一部小说,莫非这位波希米亚老北漂也有掐指一算便知过去未来的半仙功夫?
陈冠中当然不是装神弄鬼的半仙,他写这部寓言小说,着眼的,仍然是当下的中国现实。面对金融危机后深陷经济衰退泥沼的西欧和北美强国,身处第三世界的中国变得更自信、更富有、更强大,成功地举办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实力的北京奥运会,又将向世界奉献一次精彩绝伦的上海世博会,东方巨龙毫无疑问正在迅速崛起,因此,不少中国人怡然自得。
但是,现实真的如奈斯比特认为的那样——“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这盛世繁华,需不需要像陈冠中那样,来一点自我反省?作为一个在北京居住了十年的香港北漂,陈冠中似乎更能够深刻地洞察到两种不同社会体制各自的优势与阴暗面。他想要说的,一言以蔽之,仍然是《双城记》中的那句名言:“这是个好的时代,也是个坏的时代。”
《号外》是香港唯一的一份
双城,老陈有这样的资格来评说评说。《盛世》中的老陈在台湾长大,在北京买楼,生活安定潇洒,怎么看都像是长于香港迁居台湾漂泊北京的陈冠中的自况。1976年,他在香港创办《号外》杂志,美国雅皮的趣味加上左翼青年的激进立场,热血青年的文化理想在这份杂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在当时粤语市民文化开始蓬勃发展的年代,理解他的人可真是凤毛麟角。“开始的时候很辛苦,没办法跟广告商介绍这是一份怎么样的刊物,”陈冠中一回忆起这些往事就多少有些感慨,“他们不理解,对这些新兴的文化,他们有时候连题目都看不懂,觉得很奇怪。我们行文之中带入了许多口语,这种趣味在当时的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可是我却错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会很多,因为我觉得自己也不能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我也就是香港一个普通的学生而已,我想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也会感兴趣,但是《号外》刚出来的时候反应确实不是特别好。”
最早的《号外》是双周刊,虽然销量不大,但是喜欢这本杂志的人反应非常强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香港孤独的小众青年正愁自己不够主流无人欣赏,现在突然发现有这样一份特立独行的杂志,自然欣喜若狂,他们立即成为了《号外》最铁杆最忠实的拥趸者,用陈冠中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人都聚到《号外》来了。”
他说,现在回头来看,70年代中后期确实是香港各方面开始起飞的时候,不光是电影这种大媒体,小到现代音乐、舞蹈、表演都开始注入生机。“《号外》就是一个平台,只是说在某些方面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才被读者所喜爱。不过其实它的销路还是很窄的,从来不是大众刊物,发行量也不大。当时还有些人不谈收入地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刊物,《号外》是香港唯一的一份。”
就这样,慢慢地,他们奇迹般地熬过了头五年。之后,广告逐渐增多,《号外》顺利走出生死挣扎。“现在熬五年都亏本的话很难,那时候居然熬过来了。”陈冠中笑着说。广告商开始看到,这些小众其实有消费力,这一代人开始在大学教书,在公司任职,他们的消费力不容小觑,很多新的产品正好也要推给他们,所以,《号外》在商业上很快站稳了脚跟。
混在北京
陈冠中不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人,就在《号外》度过了最困难时期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98年,他们却将杂志整体卖给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陈冠中只身一人来到北京。
该怎么来界定他现在的身份?北京人?香港人?至今他也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有暂住证,他解释说:“住在北京的香港人要到派出所登记,不需要暂住证。国家对于长期居住在内地的香港人和台湾人有一些优待,我们在这里置业,只是需要登记而已。”
是香港人,却长期居住北京。刚到北京的时候,觉得北方的天气太过干燥,多少有些小小的不适应,可是经过十年的洗礼,现在的老陈可以说是个地道的老北京,“现在回香港反而有些不适应了”,他说在一个地方呆得久了,终究会改变一些什么。
不是隐居,胜似隐居。问他这些年都在忙什么呢?陈冠中想了想,两手一摊,“哎呀,什么都没有做呢,写作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这可能是他的障眼法,2004年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他和廖伟棠、颜峻合著的《波希米亚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城市九章》是小开本系列丛书中的一种。不过,写的,确实不多。看这些书的题目,多与城市有关。在大城市中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陈冠中,现在要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一片又一片的钢筋丛林。
现在的老陈在北京生活得很好,并不需要靠爬格子来为稻粱谋,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任何烦恼。比如,北京的交通就让陈冠中头大如斗。“北京的交通实在是让人觉得问题多多。”陈冠中忍不住要抱怨几句,“如果有朋友来,我会和他们一起去798,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北京一张大名片,对文艺感兴趣的人不会说不想去798看看的。书店方面我挺喜欢的是北京西边的一家书店叫万盛书园,那里常有一些别的地方没有的书。但是因为交通不太方便,所以去得其实也不多,如果没有外地朋友来,我一般不会去很远的地方,就在楼下小区里面走走。”
在《城市九章》中,陈冠中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很长,叫“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为什么还在这儿?”是啊,人多,交通堵塞,房价飞涨,不爽,为什么还不换地方?特别是像陈冠中这样的香港文化人,一边写《盛世》这样的小说,一边却还在皇城根底下不挪窝,何故?陈冠中答曰:“北京就是自在。”陈冠中所说的自在,恐怕还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自在,而是艺术和生活方式上的自由。这里有摇滚乐、诗人、各种前卫的艺术家、余华、格非、残雪似的先锋小说家,简直是三六九等应有尽有,正契合陈冠中的人文理想。
“所以够杂,所以能混。”他说。就这么着,老陈混在北京,一混,就是十年。
波西米亚北京
《新民周刊》:您写过一本《波希米亚中国》,您描述了一个波希米亚的北京,您是不是觉得北京是一个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冲击的产物?
陈冠中:那一定是。所有创新都是混杂的结果,或者是把以前遮蔽的再彰显出来。所以现在北京的情况一定和外来文化、改革开放有关。改革开放之前是另一种混杂,是把苏联、马克思和中国的一些传统混合起来,和改革开放后的混杂又不太一样。80年代之后的历史背景,在北京聚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他们为了理想来到北京。我觉得这有点像西方的波希米亚文化,像19世纪的巴黎。我看到的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化族群,正因于此,我想做一本书,描述一下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组群,只是当时我的文章不够,于是我、廖伟棠、颜峻三个人把文章集起来,来描述这种感觉。
北京以前投射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政治中心、高科技中心、经济中心,或是一个老北京——胡同文化的北京、天桥文化的北京、历史文化的北京,这些都有。世界上还没有人注意到,原来北京还有一种波希米亚文化,当然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只是没有被命名而已。一说出来当然大家都觉得,北京这方面其实很厉害,北京的波希米亚文化已经是很大的产业。幸好,我在2003年的时候,勉强把这个现象写出来,加以命名,过了2003年,它就发展太过,根本写都写不过来,你根本没办法把它们包容在一篇文章里。
《新民周刊》:香港也是一个混杂的城市,它表现出来是一种娱乐化倾向,而北京更多的表现为先锋性,像798聚集了很多前卫艺术家。您觉得这两种现象的差别是怎么产生的?
陈冠中:北京作为时尚艺人的首都,现在不仅先锋性很强,娱乐性也很强,方方面面都有了,可能先锋性给人的印象更深而已。香港是另一个极端,香港就是700万人生出来的文化,1949年以后也没受国内的太大影响,主要是流行文化确实没错,这种流行文化很有香港特色,几乎形成了香港的一种身份,比如小说方面也都跟流行文化有关。但是70年代的时候,香港也存在着流行文化之外的前卫艺术,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内地的全是香港流行文化。内地如果有那样的印象当然也没有错,只是不够全面完整,香港也存在其他的,只是它们在80年代没有进入内地罢了。
《新民周刊》:香港的世界主义文化中还有相当部分的民族主义情绪,像黄飞鸿的电影、金庸的小说都是如此,您觉得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如何产生的?
陈冠中:香港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很高。在钓鱼岛事件的时候,在香港商业区曾有一些暴力行为破坏了日本的百货公司呢。但是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是没问题的,你现在问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没有人会否认。
民族主义存在,世界主义也存在,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存在,就是这么好玩。再加上本土主义,这三个价值同时存在,大家可以自由表达各自的理念,我觉得这才是香港最好玩的地方。
《新民周刊》:您觉得大量的新移民会让北京的身份产生变化吗?
陈冠中:北京很明显,很多外来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啊,他们的政策也在影响北京,北京市政府对北京的影响恐怕还不如国家层面上对北京的影响更大。除了完全的移民城市深圳之外,中国不见得还有哪个城市能和北京比。研究一下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一些城市领导因为是外来移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影响有时会相当大,比如1949年之后,很多山东人在上海担任领导工作,上海就会跟1949年之前不太一样。
每个城市的身份建造都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不是说亘古不变的,身份都会构建出来。上海的身份就更明显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上海是吴文化的一部分,中心是苏州。19世纪70年代,上海突然出现北京热,主要是因为上海人想要和苏州人不一样。“京剧”这个词是上海人说出来的,北京人那时还叫“京剧”二黄、皮黄。还有海派京剧的兴起,为什么热的不是昆剧?
广东也是一样,改革开放之初,他们都看香港文化,不看北方文化,以此来建立广东先锋、排头兵的感觉。很多在广东长大的年轻人,他们从来不看新闻联播,都看香港TVB。身份都是如此,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和演变自己的身份。
香港也是,1949年前的香港和广东有什么区别?大家的往来没有限制。1949年之后才出现香港的身份,那也不过60年的时间。
《新民周刊》:2000年之后,很多港台艺人到北京定居、开公司,像罗大佑、李宗盛,您觉得北京对台北香港有这么大吸引力,这是内地经济腾飞、文化振兴的产物吗?
陈冠中:从文化圈我所了解的情况来说,我觉得台湾人来得比较多,香港人不是没有,但比较少一点。
这样的情况当然和中国的经济文化有关系。港台超前大陆落后这样的概念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转过来了,好像北京上海都在前面,港台反而落后了。肯定是在2003年之后,大家才有这样的感觉,之前没有。现在台北到北京的人要比香港到北京发展的多得多,台北2300万人的大城市,它本身的文化产业就比较大。而香港就是武汉,只有700万人口,多不起来。而且聚集在香港的人才大都从事影视娱乐文化这一块,而台北有更多的人才,各方面的都有,他们到北京更能适应这座城市的发展。
《新民周刊》:您买房是2002年,现在房价突飞猛进,您从香港的经验来看北京,您觉得北京的房价合理么?
陈冠中:这是比较正常的比例。但是北京和一些特大城市的房价和国民收入都是脱钩的,因为有很多外来——外省和外国——的投资性的热钱在买房子,并不是自住,所以这种地方的房价就会飙得很高,伦敦也会,香港也会,这样的房价不是当地人能够承担得起。或许当地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买套房子,因为这座城市是世界的。
我2002年在北京买房的时候很便宜,房子也很多,也没想到会升得这么快。上海比北京贵,但是也都没有香港贵,香港人其实挺惨的,一辈子就是做房奴,很多外来的游资投入到香港楼市,把房价托高到一个离谱的地步,当地人自然难以承受。可能香港不再是区域中心的时候,它会降到一个合理的价位上来。
《盛世》:以小喻大,声东击西
《新民周刊》:谈到这本《盛世》,很多人都从中读到了反乌托邦的意味,您自己是不是很喜欢反乌托邦小说?
陈冠中:我没有很喜欢反乌托邦小说,比较喜欢现实主义小说,不过我这本小说会让人联想到反乌托邦小说。我借用了一点点政治小说、反乌托邦小说和推理小说的手法,带点悬疑,各种小说类型都有一点,这种混杂的写法也许可以更好地描述现在中国的复杂性。我希望它是一本好看的小说。
《新民周刊》:书中的老陈是不是以自己为原型来写作的?那么是不是说其中的很多故事真有其事?
陈冠中:我写这本小说不是为了影射任何人,更不是自我影射。不过小说人物当中是存在着一种真实性的。
《新民周刊》:为什么要设计韦国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您是否觉得中国的青年一代丧失了基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陈冠中:在这个人物类型里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定论。不过韦国这个青年才俊、未来主人翁,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深知需要在某些时候说假话,在某些时间要做一些经营的事,并且内化了这套东西。同时他又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好的时代、一个有作为的时代。他们甚至觉得扭曲是正常的。同时他们在面对竞争时,亦很懂得去操作,很知道怎样去得到较好的位置。
《新民周刊》:小宝读了您的小说后说您“很讨厌85后、90后的得志青年”,您觉得这是您的真实意思吗?
陈冠中:小宝何等聪明,多刁钻啊,以小喻大,声东击西。不要只看他写什么,要读出他不写什么。
《新民周刊》:他又说您虽然长期居住在北京,可是您骨子里还是很港台,不太看得起内地朋友,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陈冠中:小宝说的是小说里的台湾人老陈自认为比大陆朋友更懂红酒。个人而言我跟小宝的看法是一致的:法国红酒膜拜完全是法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阴谋。下次小宝来北京,我们只喝红星小二或者常温普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