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背井的文化,能量好得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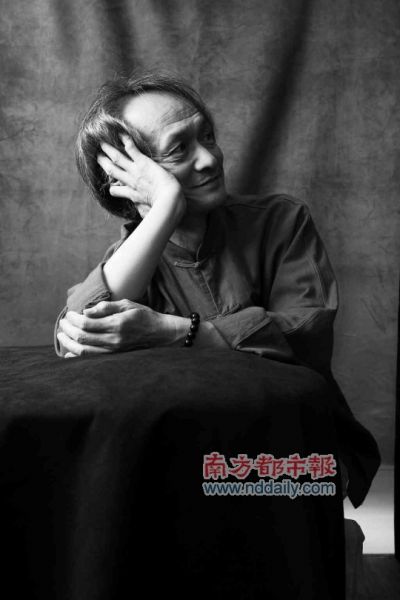
文艺客
台湾民俗文化学者、出版人
黄永松
日前,由《游遍天下》杂志社举办的“为龙正名”的图文展在深圳落幕。策展人之一台湾民俗文化学者、出版人黄永松提出,要为龙“正音正名”。在他看来,西方的龙基本上都是恶龙dragon.而中国龙在西方同样发音Dragon,使西方人一下子就会与基督世界的恶兽龙相联系。从事乡土文化保护已经40年的黄永松在上世纪80年代就把目光投向大陆,着力研究与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个社会都在向前看之际,他坚持要“向回望”,要有反省的能力。在工业化攻陷城市的强势之下,他坚持要有手工精神的传继。他所深爱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心目中的桃花源。
民间文化保护是场接力赛
南方都市报:在40年前,《汉声》杂志诞生的时候,台湾社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是不是也是如现在的大陆一样在面临转型,民间文化在逐步消亡?
黄永松:《汉声》诞生时有那个时代的变化,是人生的因缘际会。40年前的台湾也在转型,但速度没有那么快,这个很重要,一快就祥和不起来。我们在提“安和乐立”。“安和”就是要对自己的追求可以瞻前顾后。当时,台湾很多人出国,但也有一些像我这样农村、半农村出生,在城市好学校读书,但因为怕给家庭增加经济负担,不方便出国,又想做点事情的人。我们碰到了从海外回来的朋友,他们有他们的失落,觉得海外不了解自己的文化,这本杂志前身是本英文杂志,是为了让海外的游子与学子了解中国文化。而“乐立”则是后面的事情,台湾进入了家庭式工厂,代工风起云涌,带动了台湾经济。赚着微薄的利润,忍受着严重的污染,“恶之花”就来了。幸好,有很多人可以反省。这就是当时的民间文化,不是逐步消亡,而是在改变。台湾的转型速度比较慢,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自己采访的人、事、物。
南都:现在,大家提及到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时候,总是认为台湾要比大陆保存得要好,似乎台湾没有断层。很多人很向往台湾的传统文化。你觉得是否如此?
黄永松:不能这样说。大陆是大断层,台湾是小断层。就是因为台湾转型的速度没有这么快,有反省的时间。关于这个向往,也是台湾人的向往,是整个中华民族心中的桃花源。
南都:《汉声》在上世纪80年末的时候进入大陆,那时候应该是大陆城市化进程的开始,在城市化进程之中,原有农耕文明建构下的民间文化在逐步消亡,或者说,整个民间文化生态在改变。“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是否有种与城市化进程赛跑的感觉?
黄永松: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福建闽南人、广东客家人。这些移民特别怀念家乡,把土风俗保存得比家乡还好。以我的名字为例,来台湾的第一代祖先就定下两句七绝诗“生启朝观春毓秀,永承宗泽庆绵延”,我是第八代就是“永”字辈的。我们是从武昌过来的江夏黄(堂号)。20年前,在福建做采访时,碰到一个黄姓小伙子,询问我是什么黄,祖宗诗是什么。这种祖先、宗族文化在两岸都是根深蒂固的。我觉得即便是在跟城市化进程赛跑也要是接力赛。不管跑得多快,都要接力,不能丢掉传统的东西。
背井离乡的移民文化也有正能量
南都:一提到民间文化,总感觉到是存活在农村,那么在城市中有没有《汉声》概念下的中华民族的、活生生的、传统的,民间的文化?
黄永松:传统生活方式在农村中都还在,城市中也还是有的。例如,在北京周郊就有过年祭祀的庙堂,在城市中心则是形成了几个点,集中在那里供大家分享年俗的气氛。我觉得,不要快速度、纯消费心态,就能够回归文化,敦亲睦邻。
南都:那对于深圳这种没有根的社会呢?
黄永松:深圳是个移民的城市,每个人都是移民的时候,都是身在他乡。这里的人要比其他城市人要亲切,不会愁眉蹙颜。它的有趣是有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其实就是城市文化、城市风貌、生活内容。就像在台湾,我小时候过年,山东的老太给个馍馍,广东人给萝卜糕,宁波年糕,这种气氛特别享受。这种离乡背井的文化就看你是否正向看?我觉得这样,能量好得不得了!
南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千篇一律的城市状态下所丧失的文化个性与城市性格。你怎么看待这种人的崛起?
黄永松:这就是到了反省能力来了。这些反省早就有了,散落在周边,现在民族文化从隐秘处到了浅象的。我面对北京四合院被拆除很无力,也很沮丧,在台湾也这样。这个东西就是需要共识。这是我们自食恶果。如何把城市弄好,如何面对农村给我们再生的能力?现在大家都说我们城市好丑,很丑是文化素养、审美教育、生活教育而下的结论。如果素质提高,从政治上层、社会企业、传播媒体等给大家一个共识,才能有好的城市风貌。
南都:那你怎么看待这些人中一部分会以各种方式介入到乡村的建设?例如,有人在安徽某村,搞了一个乡村乌托邦的概念,做一些源流考、激活当地手工业的事情。你怎么看待这些城市人“反攻”乡村?这种外界力量的介入,是好是坏?
黄永松:不能反攻,要如何做正确,乡村也不必封闭,要希望新的人进入,共同经营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否取决与经验。要考虑大家如何一起,善用当地的力量,与当地推动衔接。
保护的善与恶之间的度要把握
南都:记得你在很多采访中都提到一个给你刺绣的老奶奶,那个说“我把身体给你,灵魂留下来”的老奶奶。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民间文化的经济价值,你怎么看待这些被市场化的民间文化?
黄永松:这需要讨论量产的问题,所谓流行就有个问题,就是不会做反思,流行了什么就买什么,是没有头脑的野兽,贪图便宜购买之后,不爱惜,用完丢掉。另一方面,厂商牟利,产生的污染物质、不考虑回收。工业产品的消耗量太大,大量产品原料也在恶性循环下,廉价滥用。而农业社会都是非常爱物质的,它是跟生态合一的,不是这个季节的物质是不用的,是尊重生命的,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我这些年做了很多工艺保护的推动,不是手艺的技术,而是背后的精神。
南都: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把当地的房子拆掉,挪移到其他地方盖。深圳就有一些这样的老房子从其它地方挪移过来的。因为即便不挪过来,在当地也会被拆除,或者烧掉。
黄永松:我是不赞成的,即便他自己要拆或者烧,速度都是慢的。用金钱买的时候,比野火还可怕。拆房子都是古董贩子。保护的善与恶之间的度要把握。但我是鼓励复制的。我去宏村的时候,就发现有售卖古董木雕、窗户构件的。我认为,既然这个有销售的可能性,就应该让这一家工匠选几个构件当场复制,大大方方销售,并告诉人家图案内在的含意,把文化力量分享给其他人。
南都:你一直在思考关于手工精神的传承问题,你认为在工业化的社会中,手工精神的传承点在哪里?
黄永松:第一,让传统的记忆还活着,第二,让文化有传承。妈妈曾经缝个背心,给自己的孩子,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我有个女性朋友,每晚的10点到11点一定要做一个拼布,作为给孩子的毕业典礼。手工的价值就在于此,它不仅在于存留记忆,而是把亲情也缝合起来。很多城市人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事实上,在缝制手工的时候那每一针都是专注的,从养身保健角度来说,静下来、专注就是解压。
采写:南都记者 黄璐
图片:受访者提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