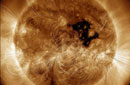柬埔寨新娘在中国:不懂汉语 交流就是瞎比划
 去年11月,有媒体曝出江西省鄱阳县有人做起“介绍柬埔寨新娘”的生意。图为一位嫁到当地的柬埔寨女性在绣十字绣。 刘延珉 摄
去年11月,有媒体曝出江西省鄱阳县有人做起“介绍柬埔寨新娘”的生意。图为一位嫁到当地的柬埔寨女性在绣十字绣。 刘延珉 摄
继越南新娘之后,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柬埔寨新娘。法治周末记者独家探访了一个有较多柬埔寨新娘居住的河北山村及其周边地区,了解到了这群柬埔寨女性在中国的真实生活状况
法治周末记者 高欣
发自河北张家口
位于河北张家口的这个村庄,一排排的平房独院静默矗立,几条家狗在沙石路上嬉闹,天空蓝得干净。因是白天,有人居住的家门并未关上。木栅栏门或木板门,轻推即开。
冬日给这座靠山的小村庄平添了几分萧索,所有的植物都掉光了叶子,披着土黄色的外衣,兀自冬眠。
王嘉和徐贺分别带着自己的柬埔寨新娘回到本村时,这里还是绿阴遍地的凉爽夏日。当时,他们辗转北京、上海、石家庄三地,才终于完成了自己“年龄段内的头等大事”——结婚。
如今,大半年过去了。无论对于王嘉、徐贺还是与他们有着相同选择的邻村或邻乡人,抑或对于那些纵贯半个亚洲嫁到中国的柬埔寨新娘,最初的新鲜都已化为寻常夫妻的柴米油盐。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7.7。这意味着,全国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出生117个男孩。在人口统计学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一般正常范围在102至107之间。
有媒体引述专家预测称,这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将给未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不小影响——“到2020年,中国的光棍将有3000万到3500万”。
在这一背景下,原本就男多女少、“娶妻成本高”的中国农村地区,大龄男青年“结婚难”问题更为突出。
也因此,近年来,越南、柬埔寨等中国周边国家的“新娘”逐渐走进了中国,且愈发受到欢迎。在不少人看来,这些国家的女子大都勤劳、忠诚,与她们结合的婚姻,还算“实惠”。
在王嘉和徐贺两家人看来,对尚未满一年的涉外婚姻是基本满意的。但身处当下、面向未来,一些难以回避的新问题也在逐渐滋生。
交流就是“瞎比划”
王嘉头一次见到自己未来的新娘,是在上海浦东机场。二人通过网上相亲认识,互传照片后,都相中了对方。后来,他唤她“娜”。
近一年多来,在王嘉家附近的几个乡级行政区,陆续迎来30多位柬埔寨新娘。这些新娘的身高多为1.6米左右,年龄从22岁到40岁不等,其中以二十三四岁者居多。
徐贺家离王嘉家不远,他给自己的妻子起名叫“泰”。由于听不懂柬埔寨语,他和王嘉一样,只能通过谐音给自己的新娘取名。
相对于农村大量涌入城市的务工人员,王嘉和徐贺是为数不多的务农男青年。二人的兄弟姐妹都到城里工作或打工,他们则守在家中,照顾父母。
徐贺的父母第一次见到儿媳时,心里直打鼓:“这么瘦,身体会好吗?”
但毕竟儿子总算成了家,公婆还是满脸笑容,喜迎这位远道而来的黑瘦儿媳。
果然,泰的身体并不好。“有时候头疼,有时候闹肚子疼,她说什么我们也听不懂,她就疼得叫。”徐母说。
怕在村里治不好,徐贺的父母专门带着泰到城里医院看病。同时,他们尽量尊重泰的生活习惯。
徐贺家保留着农村一日两餐的习惯,冬天多吃白菜、土豆和面食。来自热带的泰不适应。于是,徐贺家决定“各吃各的”。
“她吃不惯咱们的饭菜,咱们也吃不惯她那种口味。”徐贺说。
泰喜欢吃菜花和蒜薹,还不时下厨自制肉干。徐贺妈带着新奇的眼神打量已经做好的肉干,然后指指炕上的烙饼和米饭说:“烙饼我们吃,米饭是专门给她焖的。”
“只要她好好在家呆着,想干什么就让她干什么。”在徐贺妈看来,23岁的泰远嫁他乡,“没有家人在身边照顾她,咱们就得把这孩子当亲闺女看。”
言谈间,泰就站在旁边,不时笑笑,不发一言。她显然还听不懂婆家人是在说自己。
语言不通,显然是这类跨国婚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半年过后,王嘉的妻子娜已经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比如“没有”、“不”等,发音带着当地的方言味儿。
在王嘉和娜的日常交流中,手势的使用率极高。若有人问王嘉“和媳妇怎么交流”,王嘉的回答总是:“瞎比划!”
比娶越南新娘更容易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坚守在土地上的男青年并不多。与此同时,村里的女青年们则一心向往城里的生活,纷纷出外嫁人、打工、定居。
即使有姑娘愿意嫁给本村或临近村的男子,按照当地习俗,彩礼钱也不少。
“除了彩礼钱,有的还会要家电置备齐全的新房。对一些人家来说,娶个当地媳妇很难。”一位当地女村民对记者说。
这样的硬性物质要求,是不少经济条件欠佳或较差的农村家庭无法承担的。当地甚至有了“娶农村媳妇比娶城里媳妇还花钱”的说法。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而“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更高达206:100。
一大批适龄或大龄的农村男青年因此被“剩”下,而他们又必须想办法完成“留后”的家族任务。
于是,以越南新娘为代表的跨国婚姻,成为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
早在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国内婚姻介绍机构和其他任何单位都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任何个人不得采取欺骗手段或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
几年前,越南新娘涌入中国,婚介机构成为主要推动力。而如今,随着柬埔寨新娘嫁到中国来,虽然仍有婚介机构违法运作的个案发生,这一女性群体自身却已经有了更多的自主性。
她们有的通过网上互传照片相亲;有的主动提出要直接到男方家里见面;有的还因此在来中国前专门学习汉语。
柬埔寨新娘一般持旅游签证入境,在完成婚前体检等一系列法定程序后,到省民政厅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证。之后,到所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机关办理1年的居留许可。
在越南,完成一桩中越两国的跨国婚姻,则需男女双方的单身证明,而男方也需要亲自赴越办理手续。比起越南,柬埔寨女性办理跨国婚姻的手续更加简单——只需要女方的单身证明,并且不需要男方赴柬接受询问。
同时,随着“越南新娘”现象可能在本国产生的社会问题,近两年来,越南政府也对本国女性外嫁他国采取了更严格的审核制度。
于是,柬埔寨新娘成了新的“香饽饽”。
“她没有物质上的硬性条件,只是会抱怨气候、环境没她家那边好。”王嘉说。
水土不服的异国新娘
一天夜里,泰在屋里洗完头发,准备推门穿院,想到正房斜对面的茅房上厕所。公婆和丈夫急忙用手比划着制止:“大冬天的,外面冷,等头发干了戴着帽子再出去。”
不知是因为听不懂,还是觉得没必要,泰不顾阻拦,跑了出去。次日醒来,她指着自己的头部,显出难受的表情,接着就感冒了。
“她那是冻着了头疼。我们赶紧去附近找来医生,给开了药。她家那边儿没这么冷,不知道这里的习惯。”徐母说。
彼时的柬埔寨,平均温度还在零上25到28摄氏度。与泰所在的中国北方乡村,气温相差近30摄氏度。
泰刚过门时,又黑又瘦。嫁到中国后,她不用工作,整天在家。徐贺说,只要泰想吃什么,并且他们能看懂或听懂的,都尽量满足。
半年下来,泰圆润了不少,比起刚入境时,漂亮很多。
但泰的汉语水平依然尚在入门阶段,社交活动也仅限于同村另外几位柬埔寨新娘。在柬埔寨的娘家,泰与其中一位柬埔寨新娘家离得不远,便经常走动起来。
即使谨慎地相互尊重着,但语言的不通和“不知根知底”,还是让徐母偶尔心生猜疑。
“咱们都不知道她家在柬埔寨的什么地方。问她,她也听不懂。徐贺说她身上有伤疤,也不知道之前是怎么弄的。而且她们几个柬埔寨媳妇总凑在一起嘀嘀咕咕,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不会是想走吧?”徐母说。
与泰相比,王嘉的妻子娜性格温和许多。如今,她已有身孕。有时,在家无事,她会画些简笔画。然而,语言的不通还是会给她的新家庭带来一些沟通上的小麻烦。
“比如,她听不懂我们要找什么、做什么,我们也没办法让她明白。只能互相慢慢适应了。”王嘉妈笑言。
相处一段时间后,最初“勤劳、忠诚、实惠”的印象逐渐改变。到头来,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脾性”。在徐母看来,自己的儿媳泰可比王嘉媳妇娜的脾气倔多了。
飘高的“后续成本”
今年冬天,为了让儿媳安然过冬,徐母特意进城,给泰买了条新棉裤。而她自己的棉裤已经穿了好几年。
“就怕她冻着,觉得在这儿过得不好。”徐母说。
然而,毕竟经济条件有限。泰常吃肉和绿色蔬菜的习惯,还是让徐贺家负担起来有些吃力。尤其进入冬日后,新鲜蔬菜的价钱又有所上涨。
除却吃穿成本要比本地媳妇高出一截,国际长途电话费也是一项重要开支。徐贺爸说:“你得让人家隔三岔五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这费用也挺高。”
但只要泰能踏踏实实呆在家里,再“添枚新丁”,徐贺的爸妈还是表示愿意承担这样的成本。
“回头人家要走,咱也不能留啊。”徐贺妈说。
话音未落,一直在旁静静听着的徐贺走到厨房。他掀开锅盖,想看看泰的肉干做得如何。泰默契地挪到一旁,微笑着坐在了小板凳上。
在中国,近年的确有柬埔寨新娘嫁来后跑掉或离婚的先例,不过,也有来了以后不想走,甚至还把自己姐妹带来中国的情况。
对于娶了柬埔寨媳妇的男方而言,最怕的就是“新娘落跑”,最后落得人财两空。
前段时间,临近的村子就闹了一场虚惊。
在看着丈夫下地种田时,一位柬埔寨新娘在乡间路上闲逛。偶然看到一辆乡际小巴,她便上了车。
小巴的终点在县城。“新娘”没带钱,司机好心没有收。下车后,“新娘”慌了神。她对此地完全陌生;问路,也是语言不通。
最终,她幸运地找到了当初办理住宿申请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机关。
民警听不懂柬埔寨语,只能给另一个乡里的村民打电话。因为这位村民的柬埔寨妻子,是所有柬埔寨新娘中汉语懂得最多的。
最终,在“远程电话翻译”的帮助下,民警明白“新娘”只是迷了路,便迅速给“新娘”的丈夫打了电话,让家里来接人。
“新娘”的丈夫后来表示,全家人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人,又着急又沮丧,还以为媳妇呆不下去,跑了。
5年之困
马年盛夏,王嘉和娜将会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个混血婴儿的国籍将是中国,户口也将上在王嘉家。
然而,娜在生产时的住院及其他相关费用,只能全部自费承担。因为作为外籍“暂住人口”,她无法申请或拥有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各类保险。
像泰和娜一样,远嫁中国丈夫的外籍新娘,在结婚满5年后,方可申请永久性居留,继而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在初来乍到的5年间,她们正值一生中的最好年华,没有保险,不能工作;承担着文化融入与生育子女的重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外国人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属于非法就业。
“柬埔寨新娘”们普遍没有取得工作许可或工作类居留证件,同时,她们的去留也是自由的。
附近村庄曾出现过柬埔寨新娘悔婚的情况。男方只能选择离婚,再将新娘送回上海浦东机场。
适应期过后,如今留下的,几乎都是自愿嫁来的。
王嘉听说,前段时间,邻村一位柬埔寨新娘的表姐过来,伺候完妹妹的月子后,作出留在这里的决定。随后,这位表姐嫁给了隔壁村一位年长自己七八岁的男村民。
在公开的现有报道中,只有江西省明确公布过对本省柬埔寨新娘的统计数据。
2013年12月,《江西晨报》一则消息称,2013年在江西省涉外婚姻登记中心登记的涉外婚姻中,绝大部分是越南新娘和柬埔寨新娘,两者总量超过2000对。其中,柬埔寨新娘有将近1200名。而在2012年,江西省柬埔寨新娘的数量仅为80多人。
随着一位接着一位柬埔寨新娘即将成为母亲,村民们开始猜测腹中胎儿未来的长相。“怎么也是混血呢!”一位当地村民笑眯眯地说。
王嘉和徐贺对自己的外籍妻子呵护有加。然而对于未来,他们依然有许多未知。
“孩子和媳妇以后能不能都顺利上户口和保险?”类似的问题,还在将这片靠山的乡村中此起彼伏。
怀有身孕的娜已经决意留下,即使偶尔会因想家而落泪。她的祖国柬埔寨,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那里,还有不少想嫁到中国的年轻女性。
(王嘉、徐贺及两人各自妻子均为化名)
(原标题:柬埔寨新娘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