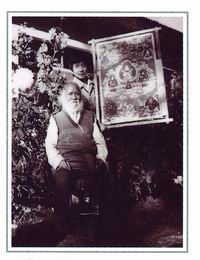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西藏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26日09:38 新京报 | |||||||||||||||||||||||||||
|
青藏铁路、藏文化博物馆将带来新一轮西藏文化热,几代文化人细述独特的西藏情结 今年5月,位于亚运村的藏文化博物馆即将奠基;7月,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将全线开通,在大大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逐渐升温的新一轮的西藏文化热。本报邀请了几位与西藏有特殊情缘的文化人,讲述他们与西藏结缘的故事和对西藏文化的认识与看法。 ■沙龙人物 叶星生:画家、收藏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西藏收藏家协会主席。 于云天:摄影家,原《中国民航》杂志副总编,首届摄影艺术金像奖获得者。 徐剑:作家,第二炮兵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所著《东方哈达》记录青藏铁路的修建。 龙冬:作家,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部主任,著有《一九九九:藏行笔记》、《娇娘》等。 明可:《西藏人文地理》策划总监,出版有摄影集《明可2002西藏》。
雪山下雄伟的布达拉宫,是西藏文化和精神的象征。
陈丹青1980年的西藏组画引发了一轮对西藏的艺术朝圣热潮。
本期沙龙现场。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1983年,叶星生与藏族老师西洛老人在一起,西洛是原十世班禅画师。
藏族人浑身披挂着美,财富都穿在身上。
江孜帕拉庄园里上世纪30年代的西洋画。
拉萨八角街转经的老人。
叶星生与他的西藏民间艺术珍藏。
为了保护纳木错湖,青藏铁路绕了七八十公里。
于云天在上世纪80年代所拍的辉煌的古格遗址。
现在的古格遗址多了些电线杆与民房。
青藏铁路格尔木起点南山口站。
藏族青年衣服上印着蛊惑仔。 (一)西藏记忆 六七十年代的艰苦岁月 叶星生:我应该算是第二代西藏人,1961年13岁就来到西藏,父母是18军的,在西藏待了接近40年了。 我是西藏中学的第一个汉族学生,那时同学们像看动物一样看我。教我们画画的老师是十世班禅的画师,我把他崇拜得一塌糊涂,他一边念经一边画画,可以在半棵青稞上画出三个佛像。 我每天跟在他后边讨好他,当然经常也有马屁拍得不到位的时候。这是绘画上的事。 再说收藏上的事。我13岁那会儿,到山南昌珠寺去临摹壁画,一个老喇嘛很神奇地出现在我面前,说孩子你饿了,把这个“人参果”吃下去吧。吃完以后,那个老喇嘛就不见了,当时装“人参果”的罐子我很喜欢,就留了下来,这个罐子就成为了我的第一件藏品。 西藏以前很艰苦,每天都是点着蜡烛、煤油灯。我们每次坐飞机要带什么东西? 葱、蒜苗、两个苹果。飞机要限制重量,怎么办?军大衣可以藏东西。我们便用麻绳挂着食品,提着鸡蛋,忍辱负重地带点新鲜蔬菜。那会儿西藏什么文化娱乐也没有。所以西藏也锻炼了一批人串门的习惯。我到藏研中心后也有这个习惯,楼上楼下乱窜,门缝里乱看,像小偷一样,被他们笑得要死。在西藏不一样,那真是五湖四海、大江南北来的人,老婆不带来,孩子也不生在这。单位宿舍简陋,铁皮房子,上下左右都不隔音。屋里就一个煤油炉子,没有通风设备,就开着门炒菜,“哟,今儿你吃的好,来!来!来!”大伙就过来了。比较原始、粗犷、纯朴,与藏民族的行为极为相似。 九十年代:文学与文化的西藏 徐剑:我第一次进藏走青藏路是1990年。对一个军人来说,长城、昆仑,是最神圣的地方。长城是一座牢固的城、防御的城。昆仑代表了一种高度,一个军队的高度,一个民族精神的高度,也有一种文学艺术的高度。我当时上青藏是什么感觉呢?首先是恐惧,听说一患感冒就会导致肺水肿,担心自己的尸骨扔在那里。那时候没有青藏铁路,要在两天之内开车过去,沥青路面也不如现在好,坑坑洼洼。如果在途中得了感冒,那真的可能就完了。我就是怀着“风萧萧、昆仑寒”的悲壮上去的。后来我又一次一次走过,还带着女儿走过,觉得如履平地了。因为这条路上不但有文化、历史,还有人文关怀。我跟阴法唐(原18军进藏时的师副政委,前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走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是一公里一个英魂。修这条路时,一公里倒下一个18军官兵,2200多公里,一个一个倒下去把这条路铺到了拉萨。因为当时18军进藏的时候,要求政治大于军事,靠政策走路,不吃地方,补给就得靠路,不能靠牦牛啊。路进去了,才有沟通,才有融合。 作为一个作家,我感觉走进西藏这块土地,走进西藏的历史,就要有文化的层次、思想的涵养和历史的眼光。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更注重这条路上的风情、文化、历史、宗教、民俗,这才是最吸引人的。 龙冬:我不知道诸位去西藏之前怎么做的,我是做了很多案头的准备才进藏的。我的西藏是文学的西藏、文化的西藏。我最先是一种对于异域的向往,那时候也年轻,喜欢海明威的那种东西。为进藏而阅读的东西里面,一定要提两个人,一个是扎西达娃,一个是马原。当时我在北京也写写小说,对马原作品的形式是不怎么接受的,但我对它的内容很有兴趣。扎西达娃的东西虽然没玩什么特别的形式,现在看叙述也并非那么自然,但在当时却吸引了我。于是,我1990年就进藏了,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又去过五回,时间有长有短,长则数月,短则十几天,但几乎都是为写作而去的。 西藏为什么让那些或长或短去过的人魂牵梦绕?首先是自然风光。雪峰、荒山、草地、湖泊、河流,全在一个画面里,对我这种北京长大的人来说,确实新奇;第二个层面和年龄有关,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年轻时去的西藏。去的这些人,都有各种体验和经历。调过头去想,这和他们的青春岁月密切联系着,容易引发怀想;第三个层面就是文化,西藏独特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厚,这就是玩儿深了,谁若陷进去,想跳出来就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了。 明可:我接触西藏文化是在美院读书的时候,叶老师把我骗进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出了一本《西藏面具》的画册。我就用了半个月生活费买了一本,那时的感觉主要是形象上的。以前写生老去藏区,毕业以后有朋友做关于西藏的旅游杂志,我抱着能够去西藏玩、拍片的目的进了杂志社,结果一下子就诓进去了。后来北京创办《西藏人文地理》杂志,我就过来了。 八十年代的艺术朝圣热潮 于云天:我(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美院版画系工作,那时陈丹青在美院读研究生。我跟读研的韩书力一个宿舍,上下铺。他是到过西藏的,老是叨咕西藏如何如何,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康巴汉子之类的。听他说了以后自然是感兴趣,因为神秘嘛。 后来我调到《中国民航》当摄影记者,让报选题,我就报了西藏。我累计12次进藏,但那时是作为记者,主要是拍寺院、民俗风情。 1985年,我走新藏线进藏,后来又走不同线路去过几次,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是西藏热,艺术的回归啊!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引起一大帮青年朝圣般地涌去,尤其是美术界的,当然包括作家,像马丽华、马原,对当代青年都具有绝对吸引力,而且因为条件艰苦,才有了朝圣般的心理。 越是艰苦不容易,大家就越想去感受。当时说是要出《西藏画册》,我就更跑得勤了,甚至连珠峰都去了。那时候很困难,但由于我在民航,最大的优势是能借助民航的力量给我派车,甚至大昭寺、布达拉宫都很大程度地对我开放过。在那个阶段,我拍了很多东西,像山南、阿里、珠峰,我几乎把西藏都走完了。 ■链接 1999年西藏文化展掀藏文化热潮 1999年3月8日至16日,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雪域明珠———中国西藏文化展》。 在短短的9天里,参观人数接近12万。西藏民间收藏展吸引了最多的人群。贡布木酒壶、皮腰包、火镰、骨质马口嚼、图纹青铜锅、鹰骨针线包、斑斓的唐卡……每一件藏品让人们流连忘返。 (二)西藏文化与精神 单纯但不单调,简洁但不简单 ●他们永远有希望,不会感到悲观。 ●它是粗中有细,一招一式都是大作。 ●西藏文化是诗意的,哲学的。 叶星生:西藏人的精神让我感动。我去阿里的途中,看见一片荒芜,简直不敢相信会有人类生存。突然听到一阵号子,啊!歌声响起来了、篝火燃起来了!男男女女围着篝火跳起锅庄,通宵达旦。他们终年都吃糌粑、酥油茶,但我觉得他们比我幸福,活得那么高兴、滋润、自然,他们永远有希望,不会感到悲观。 我说个故事。1999年北京办“雪域明珠西藏文化展”,当时我的捐赠馆也在里面。有一个姑娘从深圳来到我住的宾馆,一进门就跪下,说是代替妈妈来给我磕头的。她妈妈在重庆,曾经走投无路不想活了,本来打算最后看看西藏,到珠峰脚下,了此夙愿。结果在西藏不到一个月,看到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感觉,心就敞开了,和藏民一起喝茶、跳舞、转神山,被他们那种乐观、豁达的精神所感染,感到个人太渺小,得失并不重要而茅塞顿开。回到重庆后,还办了公司,赚了不少的钱。 徐剑:我在人民大学给学生讲课时,有人问我对西藏的感觉,我说:如果你是一个忧伤的人,面对那片净洁的土地,觉得人生可以如此的纯净;如果你是一个傲慢的人,面对昆仑山的伟岸,会觉得人是多么的渺小;如果你是一个迷茫的人,看一看在路边朝圣的信徒,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三步一磕头,就为了心中的一个信仰、一个理想坚定地前行着,你也会找回心中的偶像和精神支柱。 说到藏文化,没想到在德格的康巴,金沙江边,德格土司官寨变成了一片废墟,却有那么大一片印经院,这是全西藏最大的。什么版本的西藏经卷都放在那里,让人很震撼。 明可:这是德格土司的功劳。二百多年前他建了这个印经院后,发动所有的人帮他收集。德格版《大藏经》是错误最少的。所以,它有天文、历算、科学、医学、五大教派的东西,都保护得很好。 叶星生:所以,西藏单纯但不单调,简洁但不简单。它是粗中有细,一招一式都是大作,从工艺品、文物、唐卡可以看得出来。它有一种画叫“一毛画”,就是用一根鼠毛,画的多了,就在米面上,画出五官。 没有放大镜,没有任何科学工具,就凭感觉,不可思议。央视的《鉴宝》搞海选,西藏的宋代木雕护经板,在3万多件作品中得了金奖。 藏民族是个浑身披挂着美的民族。从头到脚,全是艺术。胸前的珠宝玉碎,就是全家的财产,根本不需要带钱。 一个九眼珠,三十多万,就一年不愁。在游牧社会,钱财是炫耀在身上的,便于搬迁,又便于保存,这就是家财万贯。 徐剑:西藏文化是诗意的,哲学的,阿来就得天独厚地写了《尘埃落定》。1998年夏天,我在采访时找了兰州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做翻译,他是个甘南藏族。甘南很出文化人。他给我翻译昌都战役时噶厦政府官员的众生相,一下就把我迷倒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再年轻十岁,我就在这里学藏语。 龙冬:西藏的民歌,无论曲调多么缓慢,它都优雅,快乐。我没印象听过一首悲伤调子的歌。 徐剑: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很多首情歌,留给读者的多是诗意、幽默和快乐。包括他人生最低潮时写理塘的那一首:“白羽的仙鹤,你的双翼给我吧,我不飞往远处,只到理塘就要折回的。”没有忧伤,没有死亡将至的感觉,心里很从容。却暗示下一任达赖灵童会诞生在理塘,谁也没有发觉,后来才恍然大悟。 (三)文化开发与保护 把代价和阵痛减轻到最小 ●应该在尊重、保护历史的基础上来谈发展。 ●千万不要铁路通了后,就人山人海地奔到西藏去! ●文明总是要把文化带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叶星生:我在西藏40年,在2003年是以“特殊人才” 引进北京。北京的平台更大,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将西藏文化发扬。而最根本的是保护,应该在尊重、保护历史的基础上来谈发展。 我打个比方,原来我心目中的大昭寺的感觉是曲径通幽,两边全是藏族建筑,很悠然、神秘地看见桑烟袅袅,金顶闪光。人慢慢地走进去,从身体到心里,有一个把玩、感受的过程。现在广场修了后,就没这种感觉了,一览无余,彻底曝光,全裸了!我觉得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尽可能多保留些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 于云天:我在摄影圈也写过我对西藏的感受,真是说着了。我到了拉萨的感觉,跟北京没什么区别。我在阿里的古格遗址的顶上,都能听到清晰的手机电话。那个古格遗址我最早拍摄过获奖作品,非常原始、荒蛮、荡气回肠的,野鸽子飞在佛塔边,那是我的成名之作啊!这次去,又在原地拍了一张片子,结果是电线杆子、楼房,都在旁边,那么原始壮观给人震撼的景观荡然无存了。这种感觉包括我到了珠峰,珠峰完全成了旅游胜地,跟一个闹市一样,马车队来回接来接去,到处是帐篷。 我们不能拒绝现代文明,不能拒绝西藏的发展。但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恰当的保护措施,让原始的东西还保持原始状态?所以青藏铁路开通后,我在摄影圈里就写到了这种担忧。千万不要铁路通了后,就人山人海地奔到西藏去! 明可:拉萨的八角街,(20)02年之前那是很舒服的地方,我特别喜欢晚上去。 地面上铺的石板路可以让你看得到历史,转经的人不时从身边走过,路上的灯光昏暗,很亲近,可以听到走路磕头的声音,这是从其他藏区到拉萨来朝圣的人。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会觉得特别有气场,随着他们去转经也很舒服。但是后来八角街改造了,把有历史的石板换成了花岗岩,把原有的灯换成了白玉兰形的路灯。我就不想再去八角街转了,觉得像是王府井的步行街了。 徐剑:这和当地领导者的眼光有关。现在西藏江孜的帕拉庄园,是西藏四大酋长贵族之下的庄园,仅次于历代达赖家庭构成的亚奚家族,是谁保护下来的?阴法唐。他当年在江孜当分工委(地委)书记,就把这个庄园保留下来了。我在帕拉庄园看到了西藏过去全套的政治社会生活方式的活化石,他们家有我们的水墨画、工笔仕女图挂在墙上,有英国人的咖啡用具,有从印度买来的沙发,还有农奴社会留下来的各种刑具。它给西藏和整个中华民族留下了解剖当时封建农奴制的一个很好的实物,也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旅游文化遗产。 龙冬:西藏要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尽最大可能多保留一些民族的、地域的、固有的、自然的、物质的、非物质的重要遗产和特色,这也是一切进步的基础。当然现在有这个意识了,但实际操作的时候,要讲科学。像北京搞这类工作都有专家啊。西藏今天的一切还来得及,有内地往日的前车之鉴,也有内地今天的意识和措施。 徐剑:从我们一个文人、作家的角度,当然希望永远保留那片牧歌式的诗一般的生活,将它留在那片高原上,但实际上人类是要进步的,那片高地上的人还是希望过上文明的生活。但是,文明和文化,并不是矛盾的。文明总是要把文化带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如何把这个代价和阵痛减轻到最小,这就是我们文化人的责任,就是科学。 (四)青藏铁路文化与意识 世界级的铁路有世界级的意识 ●这两个女人造成了一种时空的交错,构成我这部记录青藏铁路书的魂。 ●哪个地方有文物遗址,就绕着走。 ●青藏铁路这次把环境保护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徐剑:《东方时空》的记者做节目,一定要让我讲这条路上的文化。我说这条路上的文化太丰厚了。龙冬记得的是两个人,我记得的也恰恰是两个人,一个是仓央嘉措,一个是湘西王陈渠珍。这是我西藏阅读中最感动的两个人。前者是六世达赖喇嘛,后者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个管带,仓央嘉措基本也是沿着今天的唐蕃古道走出来的,他最后可能就是死在青藏线旁边的青海湖边。 我在写《东方哈达》时无意中写了两个女人,一个是文成公主,一个是西原,陈渠珍年轻的藏族妻子。一个是在帝国最强盛的时候从长安走到了拉萨,而到了帝国衰弱时,另一个走出西藏,死在长安城里,埋在大雁塔底下。就是沿着今天的青藏铁路,说是走40天,结果走了7个半月,150人最后只剩下7个人。这两个女人造成了一种时空的交错,构成我这部记录青藏铁路书的魂。 当时18军进藏的时候,带了一个藏学家李安宅,他的辈分比费孝通还要高,上世纪30年代他在甘南搞藏学、社会学研究,很有影响。18军专门为李安宅成立了一个政策研究室,就是李安宅和于式玉(李安宅夫人)。把一个大藏学家、社会学家带进去,专门为一对搞藏学研究的夫妇建立政策研究室,说明我们进藏的党的干部很有文化眼光、人类眼光。 龙冬:我的作品里也多次写到了陈渠珍,他是沈从文、贺龙的老长官。沈从文后来搞古代物质文化研究,就是早年受到喜爱文玩字画的陈渠珍的影响。西原死后,陈渠珍回到故乡,发达后,委托朋友将西原的遗骨从西安运回湘西安葬,就在今天的保靖。西原和西藏,他一生都念念不忘。 青藏铁路沿途经过郑州、洛阳,有文物古迹看,经过西安、兰州、西宁,也有许多东西可看,甚至要经过一个快到青海格尔木的小站,叫德令哈。诗人海子在那里写过一首很著名的诗———《日记》: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你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一些闪亮的文化碎片。 到了格尔木,那是一种新兴的“拓荒文化”,人物都是流动的。沿途而上,都可以用文化的目光去触摸一些点,最后它的终点是拉萨,那就是藏文化的中心啦。 明可:青藏铁路主要开通的就是旅游列车,一般的列车就只从西宁发车了。现在旅游列车初步确定从四个城市出发,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隔日运行一趟,与拉萨对开。 徐剑:青藏铁路的同志给我讲,青藏铁路火车里面,要跟飞机似的,达到一定海拔就密封起来,全程供氧,从格尔木(2900米)就开始了。只要得了高原病、脑水肿,马上就把你放到高压氧舱。很快海拔下了海平面,病情就缓解了。 叶星生:青藏铁路的文物保护就很不错,他们开了好几次座谈会,哪个地方有文物遗址,就绕着走。 徐剑:比如纳木错湖,就绕了七八十公里。青藏铁路为了生态保护,多花了十几个亿。那曲的错那湖也保护得很好,湖边搞了隔墙、种植了草坪。所以,整个铁路和人文还是融为一体的。青藏高原的植被是亿万年才形成的,它比人的皮肤、眼睫毛还珍贵。如果破坏了,亿万年也恢复不好。 这是一个环保的链条,如果植被坏了,冻土温度改变了,出来了冰锥、热融,路基就下陷了,实际上也危及到铁路路基。所以,青藏铁路这次把环境保护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一条世界级的铁路就应该有世界级的环保意识。 整理/本报记者姜妍(感谢于云天、明可、徐剑等提供图片。)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文化新闻 > 正文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