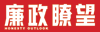我国西部乡镇政权遇发展难题 无权无财难行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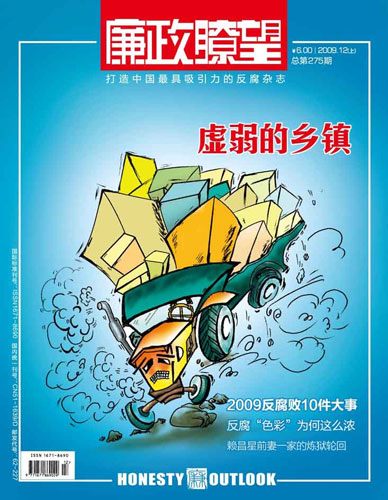
虚弱的乡镇
乡镇政府,作为中国5级政权中最基层的政权组织,直接面对7亿农村人口,事关国家根基。然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镇政权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行政与发展难题。
无权无财,何以行政?无权无财,何以发展?乡镇政权,如小牛拉大车,步履维艰。背负着治理一方和发展一方的重任,尴尬之下,艰难履职,乡镇难作为、无作为、乱作为,严重影响基层政权的执政能力和执行力。
在责任与职权、财权严重不对等的倾斜天平下,是应该使乡镇“强大”,还是将乡镇“解放”,变为真正的服务政府,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乡镇干部的典型性痛苦
◎文_本刊记者 邱祥吉
乡镇干部们都有些什么苦恼?承受着怎样的压力?记者走访了欠发达地区十余个乡镇的数名乡镇干部,本文涉及的5位乡镇干部的困惑,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他们的苦恼,或许可以一斑窥豹。
拿什么来发展你,乡村经济
“改革开放30多年了,城市富起来了,但是许多乡村的农业发展还很缓慢,现在该加大对农业的反哺了,以改变农村面貌。”在川东某贫困乡,当了8年党委书记的薛勇感到一阵绝望,“许多沟渠、道路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已很破损。”薛勇将乡上的各村形容为“经济几乎停滞不前”。全乡10个村几乎没有集体经济,由于地处偏远,加上贫穷,基础设施极为落后,根本谈不上建立和发展企业,招商引资更是句空话。“农民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薛勇叹息。
更令薛勇焦心的是,农村的青壮年几乎都外出务工了,有些村几乎无人务农,剩下的老人小孩也种不了田。“看见田地荒芜,有种很荒凉的感觉。国家在大力发展新农村,但我们这里却没有这种新气象。”薛勇形容,村里人基本都是“386199部队”。所谓“38”指妇女,“61”指小孩,“99”指老年人。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村的一个组,总共有78人,但只有3人在家种田了。“一个70多岁的村干部,就管理包括自己在内的3个人,说起来都难受。”薛勇介绍,“一个乡的几个村小学几乎无小学生,乡上小学几年前曾有800多学生,现在仅300多。在外打工的好多都把孩子带到外地读书了,农村发展后继无人啊!”薛勇摇摇头,“不过说实话,传统的农耕方式确实没有多大价值了。务农一年,可能只挣一两千元,遇上气候不好,收成抵不上打工一个月的收入。”
“而发展最难的是基础设施修建。”该乡一个村今年要修一条通村公路。由于该村地处偏远,人口少,除了国家拨付的资金外,需要当地村民每人筹资300元,但村民收入低无钱筹资,最终每人只能筹200元,还有部分村民收不齐。“本来可修4米宽的道路改成了2米5宽。”该村还算幸运的,还有4个村等待国家的拨钱修建。有个村去年县上打算拨专项资金修条村道,钱已拨付到位,但是县领导再来考察时,觉得该村太偏僻,产生的效益不大,便决定不修了,而拿去修另一个乡镇的“价值更大的乡村道路”。薛勇认为,“国家虽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远远不够,水泥路不通,沟渠老化、堰塘失去功能……还有,农村根本没有懂农业技术的人,懂技术的人也不愿到农村。现在依然是牛耕地的传统方式,难啊!”薛勇一声长叹,“我特别呼吁国家要加大投入,不然部分农村将更贫穷落后,一二十年后,将是一片荒凉的景象。”
拿什么来化解你,矛盾纠纷
过完国庆节,李刚终于松了一大口气,“晚上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李刚是川北的一名乡党委书记,国庆前和国庆期间的近一个月里,他无比焦虑,常常对干部念叨的就两个字:维稳。他在那段时间强调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维稳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
李刚所在的是1万多人口的小镇。相对来说,人口越少,维稳压力越小,但各种各样的上访户和千奇百怪的纠纷把人搞得“每天都焦头烂额”。
9月上旬开始,李刚就在乡党委的多次会上强调上级的维稳要求,干部们都显得很沉重。随后,他带领干部们纷纷下村“抚慰”几名老上访户。干部们带上米、肉、还有其他礼品,陪他们“聊聊天”,“马上就到国庆了,全国都放假了,你们就在家里好好玩,别到处走。”聊完天后就请他们吃吃饭。“能用一点东西加一顿饭,甚至拿点所谓的‘抚慰金’稳住的倒是轻松了。最怕的是收了礼依然要到乡政府来闹,到市上、省上、甚至北京上访。”
9月中旬,对于仍不“稳定”的上访户,李刚请村干部开始了“盯防”,但是村干部人不够啊,他就把乡干部派下去,干部也不一定盯得住啊,乡政府就出钱请民兵盯着。对于个别人,还派人24小时轮流盯防,白天跟着他,晚上就在他住房边“守控”。“我非常厌恶这种方式,这是变相地对被盯防者民主权利的侵犯。但是上面要求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保证‘零上访’,上级只要结果。我们真是没办法。”
撒网式的盯防仍有“漏网之鱼”。9月25日一名被重点盯防的对象竟然从村里“消失”了,“我们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县上打电话说去省里接人,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李刚赶忙派车奔赴成都,“我们好吃好喝招待她,几乎是求爹爹告奶奶,才把她请回来。那个窝囊啊!”
9月29日,一名多次被乡干部从省市接回的上访人在民兵的“监控下”竟消失了1小时,民兵晚上赶紧四处寻找,后来发现此人在另一个村店上打牌。于是民兵便在旁边“看”他打牌。
国庆期间平稳度过后,李刚和10多名乡干部终于松了一口气。“干部们其实心里有怨言,也可以理解,你想嘛,叫他们24小时盯防一个村民,这是什么办法嘛?”李刚无奈地摇了摇头。
过了一段平稳日子后,前几天,李刚给记者打电话:“一个跑了老婆的男人闹死闹活要上访,让政府给他找回老婆,找不到就要给他解决生活困难······你们媒体一定要把我们的压力写出来。”
拿什么来实现你,执法管理
张果然镇长最近很烦心。今年一个小企业落户村上,本来挺高兴的事,不久就让张果然犯愁。几名村民到镇政府反映该企业污染了他们村旁的小溪,会毒死庄稼。“我们赶紧下村去看,小工厂确实排了些废水,造成一定污染。我们告知厂主,要按相关政策进行处理后排污,不能违规违法。然后向他宣传政策。”但是村民依然找政府说,问题没解决。
张果然迅速将此事报告市环保局,过了几个星期,环保局来人一看,对企业做了点小处罚就回去了。但不久后企业又排污了,村民又闹了。“我们在环保问题上毫无执法权,不能处罚企业,但污染要是出了事,村民生病了,或者引起他们上访,后果很严重!”张果然甚至有些愤懑了,“环保局一年也下不了几次村,它哪里知道污染,这种小工厂他们爱理不理的,真要是污染问题大了,上面追究,板子首先打在我们身上。”
类似令张果然头疼的事不少。去年,他的乡上在指标范围外多出现了5名超生小孩,上级让他写检查。张果然很冤:“让我监督和制止超生者,可是我们到超生者家里,除了说‘别生了,生一个好’之外,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法规,没有其它有效的办法。”张果然所说的办法是指制止超生的执法和惩戒权,“如果我们对其强制采取措施,这超出了我们的职权范围,所以我们只能报告上级计生部门,如果上级不能尽快制止,我们是没办法的。在代计生局收超生罚款时,也只能尽量收,对方不交我们也无能为力。”而对于村上外出务工人员的超生情况,张果然更是拿着没办法,“但是依然要你管,本来就没有权力,还能管到外面去?”
环境污染问题,张果然要管;场镇上乱摆摊位,张果然要管;无执照经营,张果然要管;摩的无照营运,张果然要管;有人乱砍乱伐,张果然要管;有人超生,张果然要管……这些事,执法权都在上级相关职能部门,张果然根本无执法权,管不了,只能宣传,但是其中任何一项出了事,张果然都责无旁贷。“我们做的事就像民兵代警察维持秩序,但是我们不是警察。”对于乡镇到底有什么权力,张果然感叹,“几乎没有权力,有的地方,上面放的权多些,乡镇便有点权,收得紧,便没有权。至于乡镇哪些权该有,实际有哪些权,实在是模糊不清,我们都感觉无所适从,有问题只能多向上级报告。”
拿什么来偿还你,乡镇债务
潘明光当乡党委书记1年多了,心里却一直没有舒展过。“乡镇没钱啊,还欠一屁股债。”从县上局里调下来当上一把手,“虽然只是最基层政府,发展思路终于可以实现了,挺高兴的。”过了几个月他才发现,债务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了,谈何发展?
“去年过年前一个月,每天有几个电话打过来,要我还债。有一个村支书和建筑老板天天打。”税费改革前,村支书、还有乡干部,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交税任务,自己先帮农户垫上;税费改革后,不能再收农业税,一些农民便“耍赖”不交,政策规定又不能催收,村干部垫支的钱得由政府还。欠老板的是修建基础设施的工程款。“目前我们乡共欠400多万元,压力很大。”实际上,400多万元算少的了,同县的其他乡镇,欠上千万元的不在少数。
打电话催债“算轻松”的了。年前,“一个退休的村干部跑到政府来,给我跪下,说你先还我钱吧,都10年了,我女儿结婚没钱啊。”这让潘明光非常惶恐。最终潘明光与乡干部开会后,东拼西凑,乡上还了1万元,“还差别人4万元,于心不忍啊。”另一位曾经的乡人大主任退休6年了,政府还欠他6万元,现在他得了癌症,“我们干部想办法,把办公经费拿了一万,先给他急用。”潘明光觉得非常残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真是没办法啊。”
“天天愁这事,欠信用社、银行的钱那还可以拖一下,但欠个人的,太难受了。”并不是所有讨债的人都那么幸运,没办法的时候,只能“有钱钱打发,无钱话打发。”
因为债务,该乡乡长吴峰更是一肚子气。他曾经有个做工程的朋友借他的房产证抵押贷款。后来他调到该乡做乡长,那位朋友不还他的房产证了。“原来我们乡欠他工程款20多万元,他说我不把钱还了,房产证就暂时放他那了。”吴峰的房产证这“暂时一放”就放了4年了。“我老婆还不知道这事呢。唉!”
又快年底了,潘明光和吴峰最近往县上跑得特别勤,他们打了许多报告向上面要化债资金、项目资金。“尽量多还些,免得过不好年。”
拿什么来提升你,乡镇干部
今年47岁的蒋其昌被提拔为副乡长了,这让他感到特别意外。他从部队转业到乡上工作18年了,尽管18年来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只从普通干部干到一部门主任。近年来,他工作也松懈了,“反正是老同志了,把工作混着走就行了。”蒋其昌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我和书记并没有好深的关系,县上也没有领导帮忙。后来我了解才晓得,确实缺乏年轻点的干部担任这个职位,所以我才上来了。有点‘夕阳红’的感觉。”蒋其昌笑言。
“乡镇副职混个一二十年可能能当上,但是镇长书记几乎不可能。”在蒋其昌工作的18年里,据他了解,他所在的县只有一个人是从办事员干到乡镇一把手,后来调到县上做局长。其它的人最多当到乡镇副职。乡镇领导一般“都是‘空降兵’,一个还没听说过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说来就来了,领导我们这些老同志。”
蒋其昌并不是对“空降”的领导不满,而是对乡镇干部的上升之难感到不满。“乡镇干部往往不被市县领导看重,百分之八九十的乡镇干部一辈子都是科员,直至退休。这让我们很寒心。”
因为乡镇干部的提升难,没有年轻干部愿到乡镇工作,即使来了,也是“削尖脑袋想往县上钻。”目前在蒋其昌的乡,共有60个编制,但是在编却只有30个,30个编制还空着。而另一方面,年轻的大学生考入乡镇后,才工作一两个月就被借调到市县,工作一两年就被正式调走,这让老干部也觉得“特别不服”。“他们是有学历,思想新,但我们有经验,我们工作更兢兢业业啊!”
不过,蒋其昌终归还是高兴,不是因为职务的升迁,“副乡长实际是干事的,我高兴的是工资可以涨几百块钱了。还有比我早来的老同志,依然还是科员,每月拿着不到2000元的工资呢。”据了解,除了发达地区的富裕乡镇,乡镇并不设非领导职务,工资增长非常有限。
“芝麻大的官,巴掌大的权,无限大的责任。”乡镇的许多权力被上级各部门抽走,已成了“空壳政府”,却不得不做没有职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