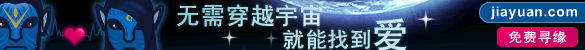政声可否人在时
政声可否人在时
刘洪波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一个相当优雅的表达,既像是敦劝行为的官箴,又像是揭示规律的玄言,或者又是官箴和玄言的合一,很有诗文德教的意蕴。
我最近看到两个“政声人去后”的人物事迹,一个是山东寿光县的前县委书记王伯祥,一个是安徽省机关下派小岗村当党委书记的沈浩。
王伯祥担任县委书记5年半,离开职务已有18年,当地人“依然滔滔不绝地数说他在位时给老百姓办的好事”。沈浩在小岗村任职5年多,这个以按手印分田出名的村子,为他按了三回手印,两次是留他工作,一次是要求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村子里。
这两个“政声人去后”的人,事迹确实感人。政治是民意的体现,可以说,这两个官员就是符合民意的人选。另外,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政声人去后”的现象,例如,美国人也会做“十位最杰出总统”、“十位最平庸总统”之类的评说,以十而论,固然是噱头,但总统身后有杰出与平庸之分,算是“政声人去后”的表现。
当世之雄与身后之议,何轻何重,排序大概依人而论,有人重在“当世之雄”,有人看重“千秋万世”。“政声人去后”,显然不是一种约束,而是一种描述,或者一种劝喻。作为描述,这是真实的;作为劝喻,这是善意的。不过劝喻是否起作用,仍在于你对身后之议有多看重,甚至即使你看重身后之议,也未必一定能够牢记守好生前之行。
我想,任何一个身后有着良好政声的官员,必然有一些佳话可以被讲起。怎样的事情算是佳话,大概也是因社会状况而不同。在中国,一个政治人物的行为,可列入佳话的,大概都体现“感人”的特性,感人而有治绩,这便有“政声”。在别的国家,政治人物的佳话,大概在于他的政见怎样有前瞻性、有洞察力,以及实施上有成效。可以说,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中,政声或者说佳话的基础,分别在德性与政见。
传统政治中的官员,或许真的是无须政见的,他需要道德和执行的意志或者艺术;现代政治中的官员,固然需要政见,但难道无须德性吗?显然又不是,相反他可能比传统政治中的官员更加不可以忽视道德,只是这根本不足以成为他的骄傲,而只是他履行职务的前提。由此,可以说现代政治下的官员,实在比传统政治下的官员更加干净。
传统政治下的官员,道德如果达到社会平均水平,那就足以成为佳话,人们会说,“那么大的官,还能够做到这一点,真是难得”。而现代政治下的官员,道德被要求在社会平均水平以上,普通人可以做的事情,官员做了就是问题。这样一想,虽然无论哪一种政治形态下,都会有“政声人去后”,但政声构成的差别,显示现代政治的政声,实在非传统政治的政声可比。传统政治的政声,重在感戴;现代政治的政声,重在欣赏。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政声是不是只能在人去后才能出现。我想,这可能是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根本区别。权力有当世之雄,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费”,很容易被看成一种坏事,实际上是权力的正途,它表明权力可以对他人进行合法支配,另一方面表明权力有时间上的期限。
当世之雄不受政声影响,乃至可以使政声消失无形,是传统政治的特点,“政声人去后”于是成为传统政治下民意的无奈。与之相对,现代政治下,当世之雄固然权力巨大,同时权力的能动范围与时间期限也明确,而且“政声”是随时产生、不可消失而且不可限制的,人在时有政声,人去后也有政声,人去后的政声,只是人在时的政声的延续而已,甚至人在时政声多有恶评,人去后政声反而抬升。
我并不认为“政声人去后”有什么问题,但我认为不能“政声人在时”是巨大的问题。很显然,当政声不能在人在时出现,那么,当世之雄就无以做到有所忌惮。政声,无非是对权力的一种公共评价,它还没有涉及到公众对权力的选择问题。权力不仅不能由公众进行选择,甚至不能由公众评价,那么公众唯一的作用就是成为权力的对象、承担权力的后果,而只能在“人去后”发出一些回忆。它确实能够说明一个地方的公众需要怎样的权力人物,但其实也说明他们无法作用于权力人物,从而“政声人去后”又变成一种感慨或者希望,但他们的意志对权力仍然是无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