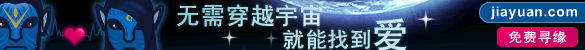药物实验受试者:在金钱与身体之间做选择
实验室的“博弈”
作为从一户贫困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大学生,正读研二的小杨,回想起自己6年大学生活,常常有些心酸。当然,最直接原因还是那个让所有农村孩子最难以启齿的字眼——钱,“大城市的生活沉重得让人难以承受,”小杨眨巴着一双迷茫的双眼,吞吞吐吐地讲述着自己的血泪史,“你不和同学混在一起,那就是不合群。但每次出去玩的花费都抵得上我一个月的开销。”
没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没为自己置办过一件超过200元的“奢侈品”。即便如此,父母寄来的生活费,加上自己微薄的补课的收入,还是让小杨感到举步维艰。“那时,一个医学院的朋友就问我,有个赚快钱的方法,我要不要试试,只要吃吃药就能有钱拿。”
从未接触过“药物实验”的小杨,听得云里雾里的,但半信半疑的他还是决定勇敢地“赌”一把……其实,对于医学院的学生而言,药物实验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一种“谋生”手段,“有人甚至每个月都会接受不同的药物实验,简直把身体赤裸裸地当作药罐子去使。”在与药物实验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在拿到“卖血钱”(补偿金)的那一刹那,小杨丝毫没有欣喜之情。相反,他却由衷地感叹,“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最痛苦的体验莫过于药物实验”。
迫于生计的小杨当时选了一项长达半年的实验项目,这个实验可以算作中长期的项目,收入自然也更为丰厚。于是,对于实验内容不甚了了的他毅然决然地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大名,“当时,完全不懂啥是知情同意,心里只想着吞点药片死不掉!”何况,医生在咨询室像拉家常一样介绍了整个实验的过程和注意事项,胸有成竹的态度,更是让小杨彻底打消了心中的顾虑。
要参加试药,就必须要到医院进行心电图、肝功能等身体检查,还要测量体重和身高等指标。均符合要求后,才能当选幸运的“小白鼠”。然而,小杨还来不及为自己的幸运欣喜,就发现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想象。按照实验协议,他每周定期到实验室报道,在吃了药物后,护士领着他到隔壁的病房内,静静地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就进入了药物实验最痛苦的环节——抽取血液样本,每次都要在手臂上挨一针,左右轮流开工,半年下来,小杨的手臂已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孔印迹。
痛苦却并非一次性的冲击波。医学院的朋友告诉小杨,在药物实验进行的全过程中,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注意“自我保护”。生怕细菌感染,实验的第一阶段的两周内,他始终谨遵医嘱,始终没有让身子碰水,俨然成了不折不扣的玻璃人。“为了避免被朝夕相处的同学知道,自己还要编造一些‘荒唐’的借口糊弄过去。”
在药物实验结束的那一天,小杨终于收获了一笔丰厚的补偿金,面对这巨款,小杨情不自禁地淌下了泪水,窝在心底的委屈在那一刻瞬间爆发了。也许是为了抚平药物实验所带来的隐性伤痛,小杨在网上疯狂搜索着同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同龄人,他方才得知,许多生活在小康家庭的大学生也扎堆各种类型的药物实验中。“有些人甚至两个月内要连续赶四个‘场’,彻底把身体搞坏了。”
药物实验的副作用也是不可规避的风险因素,作为药物实验圈子里的“老江湖”,刘正就曾饱受药物副作用的煎熬。有一次,他参加完一个治肝病的药物试验后,由于该药物的抗凝固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鼻子都经常流血,并且时常虚汗,稍微运动一下就喘不过气来。
对于这群实验室内的“小白鼠”而言,许多药物实验的消息都是从网络上不胫而走的,“有些药物实验更是重金招募受试者,也应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话,这样的实验总是让人趋之若鹜”。
反之,关于药物实验的恐怖之处,也通过网络流传,刺痛着这些“小白鼠”的心脏。一个故事说的是爱沙尼亚一个小伙子看到报纸刊出的招聘维生素实验员的消息,被免费前往瑞士两周、住舒适旅馆及数百美元报酬等诱人条件吸引而应召。结果并没有住进想象中的三星级宾馆,而是被人带到一个摆满床位的无菌诊所,接受药物实验。他对所用药物的作用一概不知,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他不得不在一份用德语写的同意书上签字。尔后在两星期内吞下了大量不知名的药物。
“药物实验更像是我们这些‘小白鼠’同药商的博弈,在金钱与身体之间,你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小杨长期药物实验经历得出的心得。
药物实验这座围城
2007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临床药品试验超过印度,这似乎“表明”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已经悄然成为全球制药行业的头号“实验室”。
可是,2009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的专家报告称,中国临床药物试验上的伦理学问题依旧不容乐观,“无论是在审查监督上,还是药物试验的风险评估,同国际准则相比,差距巨大。”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翟晓梅说道,“这两年的情况虽有改观,但依然处在中低水准之上。无独有偶,于是就有人质疑,是否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为跨国药厂在中国试药设置门槛。”
面对越来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药物和医疗设备消费市场,基于中国药物发展落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属于发展中的状态,完全禁止欧美公司在中国进行药物和医疗设备试验并不切实可行。“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跨国试药的阳光面,尤其是一些在国际上已经成熟的新药,应当欢迎这些企业来中国办实验室。”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曾繁典指出。同时,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立刻行动起来,学习西方的经验,制定有关管理条例,详细审批药物试验申请,积极教育参与试验的病人,懂得自己的权利,不让自己的权利在试验中受到损害。
当然,活跃于中国的跨国试药有着其必然的原因,翟晓梅认为,“在华办理实验的成本低,而且中国人口众多,病种繁多,因此在我国很容易找到合适的受试者,中国病人许多都是贫困者,体内没有其他药物成分,可以取得最理想的试药效果。”但也有专家提出,国外的医药巨头瞄准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欧美进行试药风险极高,甚至追溯20年前的临床试验事故,赔偿数额都达到了数千万美元。然而,5年前被炒作的沸沸扬扬的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药物实验的后续赔偿中,来自河南的艾滋病试药者的赔偿“要求”居然只是10元人民币一天的误工补助。更可笑的是,还有部分受害者提出的补偿是一只母鸡或一斤鸡蛋。
回溯2005年,《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破解我国艾滋药物试验谜团》一文,揭露了中国医学史上最大一起药物实验丑闻,34名艾滋病患者因两年前的一次药物试验向地坛医院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质疑。一时间,药物实验一次成为媒体报道和坊间的热点。
时隔4年,有关药物实验的新闻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药物实验真的就进入了新纪元呢?翟晓梅却给予了否定答案,“尽管,三甲医院的药物实验已经做得非常规范了。但是,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医院,药物实验的不规范之处比比皆是,即使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由于当地人的法律意识薄弱,很少会有村民去有关部门举报,导致这些落后地区沦为了药物实验的重灾区。”
曾经,就有一家国际药厂的研发部门来华招募抗高血压药物受试者,并重金聘请中国医生参与实验。这项为期三年的实验对象针对二期高血压患者,并将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服用该厂生产的治疗高血压二期的新药,另一组则需停下所有在服药物,并做安慰剂对照。“任何有良知的医生都会拒绝这样的实验。因为,对于二期高血压患者而言,三年停药几乎是在宣告死刑。”翟晓梅痛心疾首地说道,“在欧美的发达国家,这项实验是绝对通不过伦理审查的,一些跨国药厂就是利用了中国医生内心的利益驱动,来华进行此类不合理的药物实验。”
药物实验中的利益冲突,往往让一些小医院的管理层在利益与伦理之间,选择前者。翟晓梅告诉记者,之前她在为一些中小医院的领导进行伦理学培训时,就遇到了许多问题。这些医院的负责人告诉他们,每项药物实验,申办方都会给医院一笔钱,“如果他们不做,自有人会接手,何必把钱给别人赚呢?这就是现在普遍的心态。”
当然,药物实验的利益链条是双向的,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出现大批职业受试者团体,他们以获取报酬为目的而参加药物试验。问题总有其两面性,中国的受试者更应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翟晓梅告诉记者,地坛医院艾滋病药物实验中,许多求药心切的受害者完全不在乎《知情同意书》,甚至还有为得到这种药的试验机会,不惜使用假名登记的患者。
翟晓梅说,科学和伦理是密不可分的,脱离了伦理的科学,都算不上科学,如果把药物试验商品化,那就更加危险了。“受试者如果单纯为了获利而参加试验,可能会仅仅出于商业目的提供不准确的个人信息。比如说可能会同时参加多项试验,这都最终损害试验结果的真实性、科学性。”翟晓梅表示,“现在,中国在药物实验上的怪圈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奈若何?”
伦理委员会的中国式困境
无论如何,任何药物,不管是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还是上市,只要是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过的药物,都统称为“新药”。记者了解到,国外的药物到中国来进行临床试验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已经在国外上市的药品,在中国做最后的临床应用实验;二是研制新药,在国外做完了一期二期,在中国做完成第三期人体试验。
国家药监局网站上张贴的《药物临床试验治疗管理规范》中明确指出,任何新药若想在中国上市或是进行试验,都必须在国内重新做临床试验,尤其是新药的试验,必须从一期二期开始,从头再做一遍。而对于药物实验的申报与审批细则,国家药监局也有着严格的规范,申办者必须向省级药监局提供试验药物的临床前研究资料,包括处方组成、制造工艺和质量检验结果,以及试验药物已完成和其他地区正在进行与临床试验有关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资料。此外,省级药监局负责抽取药物样品,药品检验所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检验——国家药监局受理后,由其药审中心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评——审批通过后在药监局备案。
药监局内部人士也向周刊记者透露,每年经药监局批准的药物临床试验有数千个。试验过程中,药监局实行监督,进行抽查。其中,抽查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常规抽查,因为每年几千个临床试验,没法一一抽查,因此把工作重心放在完善规范、加强临床机构资格认定及实验室资格认定上;二是有因抽查,接到举报,或是发现问题后去抽查。
可是,药监局对药物实验套上的金箍,为何还是没能阻挡一个又一个“冒进”的新药品跃上舞台?
“医学伦理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事物,它是纯粹的舶来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审评专家茅益民深有感触,“中国的医学伦理有着很好的章程,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很好地执行。”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审查知情同意书,而委员会中的科学家,要审查上市的药品说明书,它的药学原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文,动物试验和以往做过的人体试验的材料等等。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每个医院对伦理审查的理解各有千秋,翟晓梅介绍,如同许多暴露在阳光底下的三甲医院一样,她所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协和医院的临床药理试验中心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项目是很严的。“我们常常几个小时,只能审那么几个项目。我听说一些我们这里没通过的试验项目,在别的地方审,就通过了。”
问题集中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组成规范。翟晓梅这几年参与了很多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建立与培训工作。以她的实践经验来看,一个健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不应该清一色由医学工作者承担,需要医院或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社会上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律师、非科学家等等联合组成,还可以有所服务的社区的代表。
“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圈子不乏专家,少的是真正能把伦理审查落到实处的实干家。”茅益民总说道,所有这些常识性的规定,如果能够毫无保留地在各级医院、科研组织和伦理委员会中得以执行,或许许多药物实验中的医患纠纷就不会发生。
但是,现实与理想总会有点偏差。翟晓梅总结道,“改善中国医学伦理现状的关键,就在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中心应放在,使受试者的风险与科学利益之比——在科学利益最大化时,把受试者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这里的伦理原则是:科学的利益不能超越受试者的福利。当然,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到这个的,毕竟原来的游戏中并没有这些规则,而且伦理审查做起来又显得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