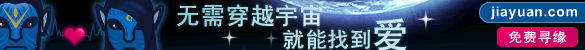数学家谷超豪年轻时因国家需要当地下党
数学家谷超豪:一生因应“国家需要”
时代周报记者 龙婧
他属于20世纪,一生经历了两次大战,见证了中华民国乱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风和雨;在数学王国里,得遇名师的他是中国微分几何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却甘愿为国家需要三次转型。2009年,中国和科学界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谷超豪及其贡献的尊敬—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一颗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
记者们蜂拥而来,却一头雾水而去。
2009年12月25日,在复旦大学为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谷超豪教授组织的新闻媒体群访中,记者们的采访并不顺利。那一天,84岁的谷超豪围着红黑格子的围巾,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眯眯坐着。对每个问题他都有问必答,只不过回答都不超过10个字。
“请你发表下获奖感言。”
“一会把感言发给你们。”
“你会后悔年轻时放下数学,去做地下党么?”
“国家需要。”
“你会后悔你几次转型么?”
“国家需要!”
“谷先生,我们都知道你和夫人鹣鲽情深,两人经常一起手挽手散步,你们平时在家做什么呢?”
“研究数学。”
……
几个问题下来,群访现场便陷入了沉默。
一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记者们纷纷向复旦大学负责宣传的人士抱怨:谷先生的话太少了,没法写稿。而熟悉谷超豪的学生和同事则强忍着笑安慰大家:老师一向都这样。
这场专门安排的媒体群访,源于谷超豪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半个月后的2010年1月11日,数学家谷超豪和卫星专家孙家栋一起,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技奖”奖章。
在数学界看来,这一切实至名归。
爱国和数学交叉的青春
尽管谷超豪依然在从事数学研究,但岁月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的听力变得不太好,几年前摔了一跤后,行动也有些不便。领完最高科技奖的下午,他缺席了记者招待会。“谷老年事已高,医生建议他下午不要进行活动。”科技部官员宣布说。
1926年,谷超豪在浙江温州出生。正值国事云乱之际,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前后、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内战两场战争的那一年代的人,注定饱尝命运的跌宕。
但在谷超豪的青年时代,数学和爱国,成为他生命中交叉的主题。
早在幼年之时,谷超豪就表现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第一次看到圆周率,他就无限向往,因为后面无穷无尽的数字,让他觉得那是一个深邃的宇宙。而在他12岁那年,温州城被炸,全城人集体逃难的经历,让他立下了要当一名革命者的志向。两年后,经哥哥动员,谷超豪加入了共产党。
17岁时,谷超豪考上了浙江大学龙泉分校。由于战乱,学校设在一个山村里,教室里没有电灯,只好点上桐油灯。桐油多烟,每每燃起,整个房间黑烟乱窜,早晨起来洗脸时鼻孔都是黑的。不过他很满足,因为很多当时著名的教授都汇集于此。1946年,谷超豪在已经迁回杭州的浙大里,见到了日后的恩师—苏步青教授。
当时的苏步青先生接管台湾大学任务完成,回到杭州给全体学生做演讲。“只见他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坛,展示了一幅台湾地图,以洪亮的杭州式官话,向大家介绍台湾情况。当时台湾刚刚回归祖国,大家听了都无比高兴和激动。”谷超豪的回忆文稿中如此记录师生间的第一次见面。在那时,只有谷超豪有些失落,因为苏先生没有讲数学。
数学上的天赋,让谷超豪很快成为苏步青的得意弟子。临近解放前,他第一次搁下了手中的数学。“我接到了地下党的任务,让我挽留杭州城内的科学家。”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他跑遍杭州的大街小巷,挨家上门劝说科学家留下来为国效力。
几十年后,谷超豪写了两句诗记录自己年少时的这段经历:“稚年知国恨,挥笔欲请缨。”
三次为国转型
谷超豪的主要研究成果分布在三大研究领域—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
按照最通俗的理解,微分几何,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有着广泛应用。偏微分方程的来源就是应用与需要,比如流体力学、量子力学都有自己的偏微分方程。数学物理就是用数学模型解决物理上的问题,材料特性、电磁学、等离子物理、非线性光学,都会用到。这三个互相交叉的学科,又被数学界称为“金三角”。
于是,“请问谷先生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什么意义?或者有什么重大建树?”成为记者们询问最多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问题每每令受访者哑然。数学王国的奥秘,不是外行人所能理解的。而数学之美,更只有少数人得以窥见。数学家们试图解释这些学科的用途,但拗口而晦涩的专业名词只会让记者们一头雾水。
最终,谷超豪的学生、如今的中科院院士洪家兴结束了这种尴尬状态:“谷先生从事的是纯数学研究,很难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成果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但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科学。”
不同的三大研究领域,意味着三次转型,而这只是因为国家的需要。“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特点:永远把国家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发展之前。他们之后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洪家兴如此评价自己的老师。
1956年,一直跟随苏步青进行微分几何研究的谷超豪被保送至苏联留学。当时,他已是国内微分几何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谷超豪去留学时,苏联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受此影响,超音速飞行和核反应研究,开始成为中国研究的热点。在此情况下,“微分方程、计算数学、概率论”被定为国家计划。于是,根据国家的要求,在苏联进修的谷超豪一边攻读微分几何,一边主动学习偏微分方程。1959年归国后,他主攻偏微分方程,提出要以高速飞行器为实际背景,以超音速绕流问题作为一个模型开展研究。
超音速绕流问题的研究中,最关键的就是确定含激波的流场变。在当时,这项研究已多年未有进展,即使放在现在,也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如今的中科院院士、那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大潜,被选中跟随谷超豪做研究。
李大潜说,转型前的谷超豪在微分几何方面的成就已经很引人瞩目,是当年在苏联拿到微分几何博士学位仅有的几人之一,更多人的人拿到的只是副博士学位。“先生如果继续做微分几何,已经是到了山顶上的人物,做下去会更顺手。”在李大潜看来,谷超豪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投入到一个不知能取得什么样成就的未知领域,不仅仅是考虑一个人的科学能力,更是他的学术追求。
李大潜说,谷超豪带着他们,天天开会、讨论和研究超音速绕流,仅仅过了一年多,他们便获得了可以“确定含激波的流场变”问题的双曲线方程。这一突破性的结果具有相当的先进性—15年以后,美国一个数学家才发表了类似的研究结果。
上世纪70年代,根据国家需要,谷超豪再一次转换方向,主攻数学物理。这一次,他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共同研究规范场理论,再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结束合作后,杨振宁称他的研究为:“好像站在山顶上,能看到全局。”
“文革”中的非正式研究员
“文革”中的谷超豪陷入了事业的低潮。由于所做的研究大多属于理论研究,不能立即转化为生产力,他被全面否定了。
“靠边站”的情况,让他的学术才能无从发挥。这对一个痴迷于数学的人来说,精神上绝对无法忍受。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数学家束星北,就曾因为这种不能发挥自己才能、不能为国效劳的精神上的痛苦,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其才能最终被埋没。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寻找机会做研究。”谷超豪回忆,当时国内的一些航天研究者向复旦数学系提出能否请他帮忙研究一些问题,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他被允准参加一个研究小组,研究“超音速弹头附近气流计算”。不过由于政治问题,在小组中他的身份只是“从旁协助”,不是正式成员。
“从旁协助”的非正式成员谷超豪实际上领导了这次研究。究竟做了多少努力,谷超豪已经记不清了。他唯一记得的是,当时复旦数学系有一个“719”计算机,大而笨重,占据了整整一个房间,一秒钟只能算几万次。更要命的是这台计算机没有自动保存的功能,如果题目做了一半停电或机器故障,资料就会全部作废。为了能在电源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研究,谷超豪只能带着研究小组成员半夜去用计算机,“一算经常四五个小时。”他说,那段计算时间是大家最难熬的时光,个个提心吊胆,就怕出问题。
埋头研究的谷超豪并不知情的是,当时中国正在试验远程导弹,需要知道由于烧蚀影响,弹头在飞行过程中是否稳定。而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远程导弹型号的设计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的学生说,谷超豪对数学的热爱发自内心。出差时,他在火车上看的差不多都是数学,有时候走在路上,也会突然跟他们讨论一个数学上的问题。而最让洪家兴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和谷超豪一起去香港出差,买冰淇淋时,谷突然脱口说出了前阵子两人探讨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谷超豪也笑言,他的好些研究成果都是在睡梦中想出来的。
门下十院士
研究和育人,对谷超豪来说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离。1999年,他受邀出任温州大学校长,待到2006年离开之时,竟是分文未取,将温大支付的140万元薪资全部捐给了温州大学,说是给贫寒学子设立的奖学金。
而他自己带的学生中,已有3名成为院士;得过他指导的学生中,则有7名成为了院士。
已是复旦大学副校长的陈晓漫印象最深的是,在他读研究生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谷超豪尽管非常忙,但还是利用晚上的时间给数学系开了一门“规范场理论”的课。这是他和杨振宁合作研究的一个内容,在当时是最前沿的课题。
“不管你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任何人都被允许来听这门课。每个礼拜有两个晚上,谷超豪会亲自讲课,每次都讲很长很长的时间。他把最前沿的东西,一点点讲给学生们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更多地理解数学,真正爱上这个领域。数学美啊,真的很美!”陈晓漫的声音里充满了回忆色彩。他说,当年的自己,正是在谷超豪处领略了数学的那种美丽。
恩师的严谨作风,则令李大潜油然而生敬意。曾经有一位博士生的论文写得不错,答辩也很精彩,只是在空气动力学的章节上略有瑕疵。放在一般的导师,很可能就会放他通过,谷超豪却让他延期半年毕业,理由是他必须重新将空气动力学读一读。这种严谨的作风深深影响了谷的弟子们。周羚君回忆,谷的学生、她的老师洪家兴院士,若因事无法授课,必会另外安排时间给他的研究生补课。
周羚君也是谷超豪及其妻子胡和生的共同弟子。她说,跟许多著名学者的弟子很久见不到导师一面相比,她是幸运的。两位先生会定期与她谈话,了解她的学习科研状况。数学院每周一次还会开一个讨论班。讨论班最早是由苏步青教授创立,大家坐成一圈,交流研究进展或学习所得。谷超豪在复旦任教的几十年岁月里,只要不去参加会议,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参加。前几年,他摔了一跤,行动不便之后才改为隔周参加。
“我们最怕的就是谷先生开口提问。”谷超豪的关门弟子谢纳庆说,讨论班上有时他会将自己读到的科技论文中的一些问题以及理解提出,供大家讨论。但有些东西实在太难了,偶尔他想忽略或糊弄过去,但只要他一开始“混”,谷先生就会很快打断他,将他企图蒙混过去的问题重新拎出来,要他详细解答。每次让他下不了台。
“虽然很多思想是老师提出来的,但除非他确实参与了工作,否则决不肯在文章上署名。”谷超豪的另一名学生周子翔教授说:“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和老师共同署名的文章只有一篇。他提出思想,我们共同进行了计算。”
而对外人,谷超豪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10年前,一个贪玩的高中生溜到复旦大学教学楼里玩。正当他在楼里乱窜时,一位老者叫住了他。因为当时复旦大学刚刚遭窃,老者有些严厉,问他在楼里干什么。发慌的少年撒了个谎,说是来复旦应聘保安。老者的脸色顿时缓和下来,给少年指点了去处。少年刚要转身,老者又叫住了他,表示自己正好要往那边走,可以带他一程。
这位少年稀里糊涂地跟着老人走出了教学楼,他只记得当时旁边有人唤他谷教授。少年名叫徐灿,10年后已是一名记者的他,在电脑上看到谷超豪获奖的消息后方才突然记起,当年耐心给自己指路的老者,正是谷超豪。
在数学中收获爱情
一生在数学中遨游的谷超豪,也在数学中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妻子胡和生是中国数学界唯一的女院士,也是第一位走上国际数学家大会NOETHER讲台的中国女性。
1950年,24岁的谷超豪遇见了生命中的爱人胡和生。这位美丽的姑娘同样从事着数学研究,也是苏步青在浙大的弟子。
有一日,胡和生在数学系的图书馆里遇见了师兄谷超豪,于是向他请教论文中的几个问题。但胡和生忘记带上自己的材料,只好返回大约10分钟路程的宿舍去拿,担心师兄等得着急,胡和生一路猛跑。
当少女气喘吁吁地拿着作业跑向谷超豪时,青年的心弦在那一刻被拨动。7年后,他们在共同执教的复旦结成了夫妻。几十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两口,依然手挽手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在校园里散步。
有着美术功底的胡和生总是把丈夫打扮得精神帅气,这也让谷超豪赢得了“最优雅教授”的称号。
在外人看来,夫妻两人的生活是单调的。谷超豪自己也说,他们夫妻在家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做数学研究。但谷超豪并不认为这很枯燥。在他看来,解决数学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她做的事情讲给我听,我能听懂;我做的事情讲给她听,她也知道。”在复旦大学提供的录像资料中,谷超豪边说边笑:“每逢我做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她就不太关心我;重要一些的工作,她就会对我重视一些。为了得到重视,我只能做更重要的工作。”
两年前,由于身体原因,谷超豪不再担任博士生导师,但他没有中断自己的数学研究。每周二,他依然会出现在数学讨论班上;每一天,他依旧会伏在桌上慢慢计算。只不过,他又一次更改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次是广义相对论。
2009年10月20日,一颗国际编号为171448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谷超豪星”,科学家们用这种方式,来表彰老人对数学界和数学界人才培养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