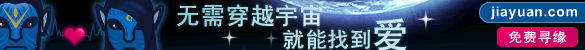黄松有曾认可遭通辑者收购我国最大烂尾楼
“中国最大烂尾楼”的盘活和原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倒下
“中诚广场”系列执行案第三次债权人大会1月14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时,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河北廊坊中院受审。赶到广州等待最终债权分配方案的178家债权人,也在同时等待来自另一场审判的结果。他们总算多少有所了解,谁在他们多年的受损中分了红。
这些18年前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各地前往广州购置中诚广场的业主,都是些小有成就的生意人,也是内地第一批商业地产炒客。
主笔◎朱文轶
随着中诚广场被最终盘活和黄松有案宣判的结束,这起秘而不宣的案件被更多地揭开。人们发现,在这栋烂尾楼被贱卖的背后,除了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牟取了暴利,身为债权人城建总公司律师的陈卓伦和身为大楼最初开发商诉讼代理人的许俊宏都参与了分赃。为他们牵线搭桥的,是时任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和在背后支招的黄松有。那些被套在这座著名烂尾楼里的资金,几经周转悄悄地流入了他们的腰包。
烂尾楼的盘活
当得知黄松有被判无期后,中诚广场的债权人们都认为,拖欠18年的债务应该了结了。
1月14日的中诚广场系列执行案第三次债权人大会上,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有8.5亿元案款可供执行分配。据一名参加会议的记者介绍,经广州市中院统计,此案需要支付变现款的债权总额为11.447亿元,其中广州城建总单列的债权总额4.9亿元,返还购房债权人购房总面积为49534.42平方米,中诚广场的最终变现款为9.24亿元。如果一切顺利,广州中院将在农历新年之前率先启动房产部分的分配,有“中国最大烂尾楼”之称的中诚广场,在屡次延期交付,久拖十余年之后,终于有望交付给当年买房的业主。
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第六届“广州全国运动会”概念下诞生的写字楼项目,从一开始,中诚广场就被所有人看做是一桶“金子”。
“一名叫钟华的湖南商人,看中了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周围炙手可热的商务区地段,找到了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想以港商身份合作这个项目。”身为债权人之一的香港人方文超对本刊说,“我们有人打听了,这家公司的先期投入只有2000万元,而楼的造价高达20个亿。但我们认为,钟华的合作方是广州城建总,项目背靠的是政府。”几年后,这场合作宣告破裂。经过广州市政府协调,城建总退出,钟华独立运营,并支付城建总全部股权转让费,由其以交付中诚广场项目相应建筑面积的房地产给城建总的形式进行。几年后,仅完成主体工程的中诚广场陷入资金困局,停工烂尾,留下广州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这个最大债权人,和将近200名未能获得清偿的债权人。总额达到20亿元的债权包含了购房款、银行抵押贷款、工程款和其他债权。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是如此漫长的“烂尾”。当时拿了100多万港元到广州购房的方文超,为了抢到中诚广场的楼花,甚至给了售楼小姐5000元的红包。“它太抢手了,大家都这么做。”他说,“当我们第一次被告之开发商无法按期交楼时,都没当回事。当时想,有政府背景,退一万步,即使出了问题,一定会有人来接手。”
他们一直在等待救星。2002年,这幢旷日持久的烂尾楼和一群被它绑架的债主翘首以盼的“救世主”终于出现了。
想吃下中诚广场的是一个叫范骏业的小商人,这个早年靠“批文生意”起家的潮州人背景暧昧。没人了解他注册的广州骏鹏置业有限公司账下有多少现金流,但他的实力显然和这幢大楼完全不相匹配。公开注册资金仅为1000万元,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地产项目的“骏鹏置业”以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撬动中诚广场20亿元的巨债。
他还拥有另一家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国家经贸委机关服务局大院的北京金贸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骏鹏”一样,“金贸”空有其壳。
“2003年5月,范骏业准备向广州民生银行贷款10亿元。但此前他在该银行已有1.9亿元的贷款未偿还,所以新的贷款项目未得到批准,他的朋友、广州市开发区东区公司原董事长陈楚原动用国有资产4000万元为骏鹏公司偿还银行贷款。仍没有达到获贷要求的范骏业又找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白云支行原副行长凌敏,以假冒公章开出商业承兑汇票的形式,从天津农信社骗取资金1.955亿元。这样,他才得到了这笔贷款作为启动资金。”身为中诚债权人之一的香港人刘文宪曾在范骏业资金链断裂之后帮其在香港物色买家,他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说。
对范骏业说,除了启动资金,要想拿下这个大项目,还需要傍上通向这个果实路径上的“大人物”。
黄松有和“政法黄埔军校”的朋友们
陈卓伦是个“大人物”,他是广州赫赫有名的大律师。他的律所也是广东律所中的“老大”,拥有超过200名律师。他和黄松有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这所被称为“政法黄埔军校”的高校毕业生,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占据了全国检察院、法院系统的半壁江山。
作为西南政法大学广东校友会第一届副会长的陈卓伦在广州律师界内的崛起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涉及金额达8亿元的深圳贤成大厦行政纠纷案。他行事张扬,以低管理费吸引律师加盟他的律师事务所法制盛帮,这对同行形成了打压;他从不掩藏他跟同乡杨贤才的过密关系和友情。曾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的杨贤才是广州高法法官中的强硬人物。“陈卓伦的业务能力和他过硬的司法关系,使得在他手上败诉的案子几乎为零。他一直在淡出一般诉讼业务的范围,而转向一些由政府主导的非诉讼业务。”一位知情人对本刊说,“以至于,后来只要是看到陈卓伦出面的案子,一定是标的上亿元的。”
知情人介绍,黄松有和陈卓伦有许多相似点,他们出身贫困,业务出色。他们都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学届相差4年,一前一后,在读书时并未谋面。但不大的司法圈里,以二人的名气,他们迟早会注意到彼此。“后来,经过杨贤才的介绍,二人得以结识,并成为好友。”知情人说。
他们的组合,本身构成了司法灰色地带的巨大资源。一切麻烦似乎都能迎刃而解。检察院的指控材料中显示,黄松有共分5次收受了390万元受贿款,前4笔分别是30万港元,30万、20万及10万元人民币,行贿人分别是广东的4位律师。最大的一笔受贿款项是300万元,行贿人就是陈卓伦。广东一个合同纠纷案,当事人上诉到最高法院,陈卓伦是代理律师,找黄松有帮助协调,最后案子调解结案,陈卓伦给黄松有好处费300万元。而他们更大的一次“合作”就是中诚广场。
商人范骏业的另一身份是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和全国青联委员,巧的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二级法官的黄松有,同时也兼任全国青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副主席。仅此,并没有实际的作用。陈卓伦和杨贤才为二人从中牵了线。
2002年,范骏业像一个推销商向这几位司法界“大佬”们介绍了这个被拖入无穷尽的债权处理纠纷之中的“大麻烦”:中诚广场。他们都对它感兴趣。
看上中诚广场
中诚广场是个“好项目”。它资金短缺,债务缠身,亟待盘活;它标的庞大,涉及资金之巨可以掩盖一些小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这栋楼本身就问题重重。“它原来就有窟窿。”知情人说,“中诚广场第一次烂尾表面上是祸起亚洲金融风暴,实际上是因为开发商法定代表人钟华在海南陷入一起2000万元的资金纠纷,时任海南省高院执行庭庭长马升亲自批示,派人来广州查封了中诚广场。几年后马升因受贿和巨额资产来源不明一审被判12年,他很可能是第一个向这幢烂尾楼伸手的法官。”
已经有人在里面捞过一道,如果再去伸手只不过是让这个黑洞更大,不会引起更多的注意。这幢显著的烂尾楼,把黄松有和他的这些老朋友“召集”在了一起。
黄松有早就尝过司法拍卖的“甜头”。在刑事司法上已经得到较好践行的“审执分立”,在民事司法上却一直难以获得认同,背后的障碍正在于执行背后巨额的部门利益——从事后公布的材料看,黄松有显然是这个争议领域的既得利益者。
据本刊从廊坊中院得到的审判书显示:1997年,当时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允许开公司、办企业,湛江中院也有个“三产”,专门承担法院的拍卖项目,由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承包经营”。当时,湛江一个拍卖公司通过关系找到黄松有,要求“承揽”法院的一个重大拍卖项目,经黄松有批准,这个标的过亿元的拍卖项目交给了这家拍卖行。成交后,这家拍卖行给湛江中院“回扣”近千万元,经中院党组研究,将其中的308万元给“三产”,名义“支持下属法院”。这308万元被黄松有和承包“三产”的另两名法院工作人员分了,黄松有从中得到大头:120万元。
“1997年,黄松有调任广东湛江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仕途蒸蒸日上的他这一年又遇到了人生一次绝佳的表现机会:案值达110多亿元的‘9898’湛江特大走私案。”一名曾在黄松有手下办事的法院工作人员接受本刊采访称,“在业务钻研上一直很下工夫的黄松有抓住了这次机会。他当时一边在准备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博士的考试,一边要审阅130多名走私人员和涉案官员的案卷,的确极为辛苦。这次审判任务的出色完成使他被广东高法授予个人二等功,并在事实上拿到了进入最高人民法院重要位置的‘门票’。”
“湛江中院三产案”尽管只是个不起眼的插曲,却集中反映了司法拍卖和执行环节的所有问题,在未来,这些问题将更为频繁地引出纰漏。法院拍卖甚至成为拍卖行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其中,强制拍卖更是在拍卖行包括公物拍卖、银行不良资产拍卖的三大业务中比重居首。
“涉讼资产处置均由法官指定拍卖机构进行,这一司法介入市场的地带形成了巨大的漏洞。”资深拍卖师宋海阳对本刊说,“拍卖标的最早就是来自于被罚没的公物,拍卖业从一开始恢复就是堵塞灰色交易的产物。而估价和拍卖的获取利润均是按照标的物价值来按照百分比收取佣金,越来越多的拍卖公司为了获取业务和拍卖中的灰色收入就要想方设法取悦拥有选择权的法院法官。”惊人的利益输送由此而来。黑幕中一个约定俗成的分配原则是,拍卖行所得佣金按照“4∶3∶3”的比例会在参与小团体内部进行切割:40%给承办法官,30%给拍卖公司,30%用于各种成本开支以及各方打点等。“这个困局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化解。问题是,即便‘审判权’同意撤出执行领域,谁又能保证接手的行政机关就一定比审判机关更清廉呢?”宋海阳说。
2002年,黄松有和他的律师朋友们的联盟,顺理成章地再一次去“攻击”了这个漏洞。比起湛江中院的那个“三产”,中诚广场是数百倍于前者的“大肥肉”。
出手
当杨贤才把这个想法向黄松有和盘托出时,他们都认为面前几乎没有什么阻拦。
杨贤才在2002年初唯一的障碍,是中诚广场的处置最初不是由广州中院执行,而是在贵州中院。而这只要通过黄松有,就几乎不成其为任何问题。“黄松有直接从最高法,一层层压下来,最后指定由广州中院来执行。”知情人说。
这等于把中诚广场直接送到了杨贤才的面前,这位当时58岁的“中国第一执行局长”,向来以案件执行力度上的“铁腕”风格著称,他一年前(2001年)刚刚坐上广东高院执行局局长,正处于中诚广场执行流程的核心位置。他分管此事,操控全局,却可以和黄松有一样安全地隐居幕后。接下来,“黄松有们”要做的看起来就再简单不过了,他们只需要把发生在类似“湛江三产案”那类司法拍卖里的内幕交易如法炮制。
但市场却给志在必得的黄松有出了难题。中诚广场并不是道“冷菜”。这幢一度试图打造广州地标建筑的烂尾楼,虽然命运多舛,却质地优良——它位于广州天河北商圈、体育西路的黄金地段,只要有资金续力,它就绝不缺少咸鱼翻身之机。“当广州中级法院要对中诚广场公开拍卖的消息放出去后,竞争者接踵而至。”宋海阳回忆说,“当时包括保利地产及广州城建集团等本地地产公司都表示愿以加入角逐,以高价盘下中诚。”
这对黄松有、杨贤才和他们的关系户来说,实在不是好消息。一旦任由资本介入,财大气粗的地产商会主导游戏规则,局面就不由他们所掌控了。
于是,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游戏”本身。黄松有在北京再一次向广州施加了权力影响。“广州中院申请拍卖中诚广场,但得到的答复是:高院和最高院不同意,批示直接变卖。”接受本刊采访的知情人称,“按照法律规定,肯定是要先拍卖,再变卖。一步马上变卖,完全不是正常的处置资产程序。”
知情人称,不仅如此,“广州市中院接连收到来自最高院的数封函件,要求指定由名为北京金贸与广州骏鹏的两家公司收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广州官员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广州市中院院长吴树坚今年初在广州市“两会”分组讨论中曾间接谈及此事,她说,她个人认为“该案件不是按程序执行的”,但广州中院“是按照上级法院的批示执行,院长也是具体办案的,上面怎么批下来,我们就只有怎么做,因为下级服从上级,理所当然要执行”。
到这里,范骏业的两家公司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台亮相了。北京金贸国际投资公司和广州骏鹏置业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中诚广场3/4权益,作价9.24亿元。2002年11月22日,这份收购合同被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一年后,2003年12月9日,广州中院正式发文,认可金贸与骏鹏联合收购,协议双方为此收购还成立了项目公司广州金贸房地产开发公司。
让背后操盘者和范骏业始料未及的是,最初让范得到启动资金的那笔贷款成了所有方案百密一疏之处。那些使用假印章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捅了娄子,它们正好撞上了这一年公安部打击金融票证犯罪的集中行动。“范骏业在2004年被天津、广州两地警方立案后,他从程序上已经失去了购买中诚广场的资格。”刘文宪说。
黄松有显然在这一关键时刻又推了一把——处于通缉期间的范骏业竟然在此时重构了一份收购方案,他在2004年11月26日发出请示报告,抬头直送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由金贸公司单独收购中诚广场,并提出要求将此前已涉案的3.5亿元收购款项脱离与骏鹏的干系,划为金贸收购款,试图彻底摆脱“广州骏鹏”涉嫌金融票证犯罪的阴影,完成这场几乎就快接近胜利的收购。“这个问题一目了然的收购方案竟得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知情人对本刊说,“2005年2月,金贸公司提出的独家收购申请获得许可,涉嫌骏鹏诈骗案的3.5亿元资金甚至被洗白继续用于收购。”
很快,金贸公司低价购得中诚广场后被转卖,售价13亿多元,这笔倒手生意的“利润”高达4亿多元。但“中诚”的命运并没有得以改观,开工没有几天,它就再次搁置了。
2006年高价购入中诚广场A座的中石化集团总公司最终将烂尾十几年的中诚大厦盘活了一半,并将其改名“中石化大厦”,B座则由一家收购了金贸公司80%股权的地产公司接盘。
发生在这幢烂尾楼背后的一系列内幕交易,在接续而上的新资金中被清洗得毫无痕迹,直到2008年时任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因涉嫌犯罪被处理,中诚广场拍卖的全貌和隐藏其中的黄松有才得以浮现。
还有一个仍然无法回答的悬念是,被黄松有和范骏业们共同吃入的4亿元差价,将以何种方式兑现给受困将近20年的债权人?很多人当年购房时用的是港元,如今汇率逆转,类似资金损耗无以计算。刘文宪说,他们并不抱有期望。从法律的角度,这4亿元差价可以认定,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被认定为“黑金”。■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