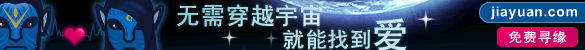猎书人唐诺

猎书人唐诺
咖啡、可乐、电影,如果一个社会只有2000个人需要,通常不会成立我喜欢出版这个行业,是因为只有2000个人需要时它居然是成立的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实习记者 丁一 发自香港
唐诺
本名谢材俊,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长期从事图书出版工作,现为自由读书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自称“专业读者”。著有《读者时代》、《阅读的故事》、《文字的故事》、《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球迷唐诺看球》等。
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说,“一个人日后会成为怎么样一种人,端看他父亲书架上放着哪几本书来决定。”
这么说起来,谢海盟——唐诺和朱天心的孩子小时候一定很为难,因为她父亲书架上摆的书太多太杂了,时不时还要堆在地板上,不太容易挑。
在《阅读的故事》中,唐诺把找书比作狩猎(有趣的是,朱天心2005年出版的随笔集叫《猎人们》,果然有夫妻相)。他的猎场,有英国伦敦的查令十字街,有日本东京的神田神保町。近些年,也延伸到北京、上海,以及网上的亚马逊。但他自称没有冷僻的喜好,看的都是一些人家也会看的书。
他把阅读想象成旅行。“旅程中尽管不免始料未及的风险,也可能就此一去不返,但这毕竟不是阅读者最原初的心意。对那个比较差比较单薄贫乏的眼前世界的思索和不服气,仍是这一切之所以出发的起点,能够的话,也希望是这一切的终点。”
在真实的日本旅行经验中,他和朱天心最喜欢的寺庙是唐招提寺。当年鉴真东渡,因海风长期侵蚀双目失明,凭着口述记忆中的形象,建成了这座安居于古都奈良一隅的仿唐寺庙。后来邓小平访日时说了一句宛如招魂的话:“老和尚该回家了。”如今鉴真的坟墓还在寺后,骨殖却已安葬在他曾任方丈的扬州大明寺。
除了是“专业读者”,唐诺也是在出版界浸淫20年的“图书推销员”。格雷厄姆·格林、翁贝托·埃科、劳伦斯·布洛克、约翰·勒卡雷进入台湾的书店或多或少跟他有关。埃科的名作《玫瑰的名字》是他在《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上勾出来的,后来成为一个系列的开头。至于曾获20多次提名而终未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格林,最初台湾辅仁大学出过一套书,把他列入了天主教作家,读者面非常有限。唐诺觉得可惜,后来乘电影《爱情的尽头》(格林同名小说改编)在台湾上映,与出版社合作,顺势又推了一次。
唐诺曾非常乐观地说服读者去买书:“一个人类所曾拥有过最聪明最认真最富想象力最伟大的心灵,你不是极可能只用买一件看不上眼衣服的三千台币就可买下他奇迹一生所有吗(以一名作家,一生十本书,一书三百元计,更何况这么买通常有折扣)?”但最近几年他开始忧心台湾所谓“文化产业”把书纳入过于利益导向的秩序,使过去最富人文底蕴、勉力维持的那些书萎顿甚至消亡。
他的名字在大陆频频出现,最初是在外国文学新书的护封上,作为荐书人。作为作者,则延至年初的《文字的故事》,虽然早在两年前这本书就和《阅读的故事》一起排上了出版日程。
唐诺把自己的写作当成一种报恩,“某种文字共和国公民的应尽义务”。老朋友吴继文曾不止一次劝他“说自己的话”,把文章中引用的“他者话语”冲干净,他却对人要有一己“创见”的说法不以为然:如果别人就是讲得比你好很多,为什么非要坚持用“自己的话”来说呢?有时他甚至有意识过度引述——“渴望有些好的名字、好的话不断会被看见,放一个叮叮作响的美丽声音在也许哪个人不经意的记忆角落里,就像太多人为我做过的那样。”
干脆成全他好了,把《阅读的故事》中出现最多的名字列出来——文学家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格林、纳博科夫、阿城;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难以归类的本雅明。
小说家像火耕者一样不环保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你不时来大陆,你会对哪些现象感兴趣?
唐诺:整个发展过程,社会、经济、政治层面,每一样我都觉得好玩。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人走路,到北京就发现被惩罚了。这是一个不能走路的地方,紫禁城的空间距离不是为生活设计的。这才知道当年大臣获准骑马或者乘轿进去是多大的恩宠。
人物周刊:你很喜欢步行?
唐诺:我是很会走路的人,尽管这个年纪了。2008年去高雄,4天走了17万步,120多公里。因为在城市坐车太快了,看不到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路。如果我是在日本,一天大概要走4-6万步,所以我浑身最贵的东西是鞋子。
鞋子可以买得好一点,因为它们很难变成夸耀的物品,除了女明星那些不是为走路的鞋。好莱坞有部电影《白宫夜未眠》,总统爱上一个女人,追她的时候狠狠赞美她的鞋子。女孩子都喜欢这样,你连鞋子都注意到了,就代表你什么都注意到了。
人物周刊:除了琼瑶、古龙那种通俗小说,在大陆并不怎么能看到现代台湾文学。
唐诺:我一直想说,如果台湾有一类经验,在华人世界、在大陆有意义的话——讲得夸张一点,就是在一个被逼迫的过程中走上目前这条路的经验。
台湾是一个没有死角没有纵深的岛屿。民进党爱讲台北和高雄、南部有什么不同,我跟你讲没什么不同,台湾就那么大。这里有一个全世界诡异的生态,它的cable普及率是97%,有线电视跟无线电视根本没有差别,所以你完全曝晒在那种高速的资讯网络里。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来说,独特性只能来自适度的区隔。台湾则是完全没办法区隔。所以,个人的经验不断贬值,台湾老早就没有故事可写了。
其实不是城市没故事,而是——用本雅明的话讲——走过一个街角线索就断了,就被别的东西取代了,追踪不了。这种情况下,台湾作家被迫用更细的网去捕捉那些精细的东西。可能是现代化过程使得小说的整个形态苍老了。拉美好不容易发生了文学爆炸,但你不会想到一代人就把那些东西写尽了。我常常讲小说家像火耕者一样,完全不环保,他在一个地方放一把火,把几百年的森林烧掉,灰落下来,化成沃土,他种个三季就走了,这个地方却沙漠化了。
欧洲、美国、拉美、非洲、日本,很久没有好的小说了。台湾的经验可能就是它较早碰到这个“渔场枯竭”的状态,所以台湾小说家的书写就非常非常辛苦。
人物周刊:从你读到的大陆小说来看,这几年大陆有没有“故事讲完了”的征兆?
唐诺:一般来讲大陆作家的书在台湾的读者面不算很广。如果从严苛的文学角度来说,这几年我所接触到的读过的人,评价的确在变坏。
比方说莫言过去那样的书写方式是台湾所没有的,高密那种传说故事讲个没完,张大春和我每次讲到他简直羡慕死了,在台湾一个都没听过人家满地都是。我对他感情还蛮深的。但这几年,他试过《檀香刑》这样用声音来表达的,用《四十一炮》处理上半个世纪的显学符号学、文字学。你可以明显看到他突围的那种努力。
能简单说出来的一定有它的限度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开始,台湾的出版变得比较自由?
唐诺:其实还算早。当初很简单,只要跟共产主义不相关的大概都不是政治问题。跟共产主义相关的,台湾闹过一些笑话,因为检查的人可能是军职的,文化水平比较有限,《马氏文通》和《毛诗正义》都曾经被查禁过。以前台湾有个从政者叫毛松年,大家说他什么官都可能去干,但绝不会干到什么什么主席,因为那样就会变成毛主席了。
其他是技术性原因:资讯的匮乏、跟世界出版状况的隔膜。台湾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本作家”的传统,好像很多作者都只写过一本书。很多人以为巴尔扎克就写过《高老头》,托尔斯泰可能就是《战争与和平》。一个名字永远只和一本书连在一起。前些年还做出版时,我编过一个“一本书系列”,出的大概都不是作者的“那一本书”。作者最有名那本书,也许是他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或者评价最高的,但如果一个社会一直停留于此,那就太不对劲了。现在台湾的出版基本上没有禁忌了,如果做不了什么书,不是因为不能出,而是因为没人看。
人物周刊:普通台湾人喜欢看什么书?
唐诺:就是所谓流行类的东西吧。趋势是对影像的热衷一路加强,对文字的不耐不断发生。这几年台湾的价值逃散很厉害。在我们那个年代,即使自己没能力看,也假装看过假装喜欢。当然虚伪,可假装久了,不小心就会变成真的,而且始终认定那是好的,看不懂是自己所学还不够。现在的读者会说我看不懂一定是这个作者胡说八道,为什么没有写得让我能懂?
人物周刊:他们认为,好应该和简单共存。
唐诺:好东西不一定简单,而能简单说出来的,一定有它的限度。比如说《国家地理》杂志或Discovery频道,再枯燥的学问都能够讲得很迷人,但只是在某个阶段。所以你会发现小孩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他就像天才一样,什么样的恐龙什么样的汽车他都懂。但我开个玩笑,全世界的侏罗纪专家,99%终止在12岁之前。好玩的东西到那个阶段讲完了,你要往下去,像卡尔维诺说的,就会碰到沉重的一面。你会知道恐龙世界里不只是几头摇来摇去的大东西。你要碰地质学、生物学、化学,都是枯燥乏味的东西。所有小孩都是天文爱好者,但往前走一步,到天文物理学就头破血流了。如果你对它没有一点崇敬之心,不容易驱使自己走下去。后面有一个部分是要咬着牙的,你要挨过那样的时光。
日本最厉害的是它的生活美学
人物周刊:近些年来台湾出版了很多推理文学,是不是受到日本影响?
唐诺:推理作为这么重要的一个类型,总会进来的,过去也陆续有人介绍,但在我们这一代像詹宏志他们才较为正式地做起来。但其中有一个假象,很多出版社以为推理很好买,莫名其妙就加入了,现在绝对是供应过度。
日本推理在台湾占不正常的比重,不完全是因为台湾有日据的经验,而是因为在台湾日本式美学很早就被几乎不抵抗地接受了,包括漫画,包括百货公司的样态,包括颜色。漫画进入台湾的出版界时,有好多人说,既然日本漫画(版权)的争抢那么厉害,为什么不引进美国的?《超人》、《蝙蝠侠》、《绿巨人》好莱坞天天都在帮它们宣传。可是虽然电影卖得那么好,所有人都知道,漫画来一部死一部。有人做过,不是没有。因为台湾人习惯的颜色线条是日本那种粉彩模样的。
我觉得日本最厉害的是生活美学这一块,这是它最有创造力的部分。亚洲美学有相当一部分被日本操控了。他们的包装、设计、色彩的处理,真的有一套介于创造和商业之间的、非常圆熟的方法。但日本这一代推理作家其实是没什么创造力的,完完全全向商业投降,甚至他们的文学也已经荒败很多年了。
人物周刊:村上春树怎么样?
唐诺:对不起,我这样说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在台湾已经得罪过很多人了,但我一直借用写《拇趾P纪事》的日本女作家松浦理英子说的话,“我觉得村上这样写小说是犯罪行为。”我不喜欢他的东西,评价非常低。
人物周刊:你认为村上受欢迎是为什么?
唐诺:村上的情调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我觉得几乎是普世性的。他那种日本式的淡淡的粉彩色的美学,在台湾完全没有障碍。村上很松软,符合一些人的预期。你觉得应该读一本“好小说”,又不想太用力时,可以读村上。
他早期还写一点60年代的记忆,只是把这反叛的记忆弄得比较轻灵,那时我还可以看一点。但到《海边的卡夫卡》,一个流浪汉——我知道日本流浪汉有点不同,但也太过分了——煮红茶,讲那些东西。我受不了,那种耽溺没有道理。我对卡夫卡的评价虽没高到有些人那种地步,但也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海边的卡夫卡》那样写卡夫卡真的是犯罪行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卡夫卡?
唐诺:在我看来,卡夫卡的叙述是最像噩梦的。他的作品很奇怪:A可以导到B,但是B导到C的时候,C和A是没有关系的。这经常是我们梦境的构成方式,因为梦境好像没有记忆。我认为这是卡夫卡的基本笔法。他小说中的“失忆”清醒的人不应该有的,理论上正常人是不能这样控制的,但他可以这样写,而且文本还不会破碎。
人物周刊:台湾本地有人创作推理小说吗?
唐诺:很早就有,但一直失败,到现在全球化现象蔓延,就更没法对抗了。因为要对抗的不仅是欧美、日本的推理小说,还有好莱坞的影像。以前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接触一些广告公司,每次我都劝他们做汽车、手机广告,千万别去拍未来拍明天。他们用2000万台币拍一个广告已经竭尽所能了。可是看他们广告的人也看好莱坞,习惯了那样的东西。
就像我们以前看琼瑶的小说,里头多金的公子,住在阳明山,家里有汽车,带你出去吃西餐、喝咖啡,已经不得了了,好像为了这个要干什么都可以。可是现在进来的格局是石油巨子,开过来的是飞机,送来的是爱马仕、宝格丽这些东西。世界化的程度使原来那些纵深守护不住了,里头的挑战是非常惊悚的。台湾的某些经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时候其实是不得已的教训,有些事情“早了3天被惩罚”嘛。
满足2000个人一本书就能成立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台湾图书业景气吗?
唐诺:在我看来这几年的变化是不祥的征兆。在台湾——大陆需要换算一下数字——一部新书卖到2000本就勉强成立。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奇迹。你从市场规律来看,咖啡、可乐、电影,如果一个社会只有2000个人需要它,通常不会成立,因为它不到一个经济规模。我喜欢出版这个行业,是因为只有2000个人需要的时候它居然是成立的。
另一个角度来看,它的自由度、冒险性就高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现在台湾拍一部电影可能要5000万到1亿台币,要收回这个成本,相对要有多少张票,这个换算非常简单。台湾只有3个电视台的时候,有一个主持人叫张小燕,她的节目收视率曾经非常好,后来掉到21个百分点,节目就取消了,因为以台湾的标准说,你应该满足500万人的需要。但书只需要满足2000人,很特殊的东西就可以出来。换算成台币,一本书的代价是30万。一本都卖不掉,直接拿去销毁,也只花掉30万。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书籍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维护一个多元的世界。
唐诺:对。如果你有个古怪念头,千万别想着直接拍成电影,那样你可能会倾家荡产,但写成书你就有机会出版——这是我作为出版者最感兴趣的一点。
但近些年最大的变化是,过去可以卖2000本的,一下子萎顿到500,偏偏这些书是所有编辑者最富人文底蕴的一组书。我有点担忧这个2000本的部分会消失。
最畅销的书可能差别并不大。像《大萧条的孩子》里说的:萧条来临,会先破坏抵抗力最弱的外围。1930年代的大萧条,一半人回忆那段时光如在地狱;一半人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次金融危机,我问加州的朋友:你们那儿怎样?他很努力回想,然后说,喔,东西都变得很便宜。你就知道他属于没有被剥夺的那一半。
文学创作者也一样,朱天文、朱天心可能暂时还没有问题,舞鹤就很难说了,而且久了都会被波及。这是我对台湾出版业的忧虑。
大陆将来可能也要面临这个问题。交通、互联网、通讯器材,种种信息传播的发展都会使得死角消失。过去台湾的流行歌里离别都是在火车站,到火车站就觉得这一生不会再见面了。现在坐高铁从南到北就一个半小时,你哭个什么劲,待会儿又见面了。大陆继续发展下去,这个日子很快也会来临,不是吗?
(本文未经受访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