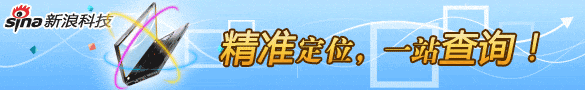我国GDP世界第2带来贫富困惑 尚无法称经济强国

GDP世界第二带来的贫富困惑
“二”的纠结
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国人未狂喜。
GDP没让中国人膨胀,人均GDP时刻提醒我们自身的处境,中国成了这个世界“最穷的老二”。
我们由此产生的纠结与困惑是——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的关系,这是属于国家的纠结;拜金与仇富、物欲与爱情、金钱与幸福、梦想与生存的矛盾,这是属于个人的困惑。
GDP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存量财富的增长,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
中国需要与世界第二相匹配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否则数字上的繁荣,随时会烟消云散。
GDP的20种中国纠结
GDP排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自省——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文/黄俊杰
在世界GDP竞速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我们在2005年超过了英国,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第二季度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了全世界GDP第二名。
不过,中国用来超车的,是一辆里头人挤人的公共汽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均GDP才只赶上日本的1/10。《富饶的贫困》作者白南风说中国的改革有一块“变心板”,这块变心板如同公共汽车车门的踏板,车下的人想车上的人往里让,好让自己挤上去;车上的人冷着脸,大声嚷嚷:“里面没地儿啦,别挤啦!”
在中国,有90后炫富女在网上发手捧钞票的炫富帖,称下等人才挤公交。这就是人人都想挤上这辆跑得飞快的、叫做财富的公共汽车的原因。油钱大家都有份给,凭什么唯独我跟在时代的车轮后吃尘——我们开心,因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们有些不开心,因为人和人也拉开了差距。这就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纠结:国家与国家差距缩小,人和人差距却被拉大了。
这种纠结对于国家,是为十大纠结:纠结于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纠结于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纠结于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纠结于开发力度与环境保护,纠结于资源垄断与市场开放,纠结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纠结于中国制造与创意立国,纠结于西方价值与传统文化,纠结于外交战略与国际压力,纠结于功利的现世与持续的未来。
这种纠结对于个人,也是十大纠结:纠结于快节奏与慢生活,纠结于拜金与仇富,纠结于攀比与知足,纠结于家庭与事业,纠结于物欲与爱情,纠结于梦想与生存,纠结于金钱与幸福,纠结于物质化的友谊与理想化的纯真,纠结于一线城市的成功学与二线城市的安居梦,纠结于价值迷失与身份焦虑。
GDP排到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反省。事实上,除开GDP排世界第二,中国还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马球衣销量排第二,结核病耐药率全球排第二,税赋负担排第二,超级计算机性能排第二,人体器官移植数排第二……这些第二名排列起来,描述的是一个说不清的中国。
中国人没有外国人想象中激动。至少,中国人面对GDP的纠结,早已有正确的共识: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贫富困惑与身份焦虑
有人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这4元堪称中国工薪族的魔幻现实主义。
有评论分析中国人收入现状,引用了两份报告——一是北京政协主席会议上一份调研报告,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二是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薪水成为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成本,广州要128万、杭州要178.2万、上海要200.82万、北京要202.8万、深圳要208万。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有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
这种焦虑也体现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学者张维为曾写文章《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 “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成年人在焦虑自己是社会名流、伪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焦虑则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了“富二代”与“穷二代”的身份焦虑——王朔在《致女儿书》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安徽省灵璧县今年曾被曝存在“贫富班”,交3000元钱的孩子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有空调、彩电、DVD,不交钱的孩子只好去挤百人大班了。
“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感慨,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实的差距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GDP增长是解决贫富分化的前提。“没有GDP就是穷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块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决好分配,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个轻重,不要看错了,以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话,那就是穷平等。”
“穷爸爸”好,还是“富爸爸”好?
一个爸爸说贪财乃万恶之源,另一个爸爸说贫困是万恶之本;一个爸爸努力存钱,一个爸爸不断地投资;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并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爸爸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一个爸爸说顺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个爸爸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
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描述了两种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们经历的社会环境比作爸爸,这与中国30年的观念之变何其相似。祖国已是“富爸爸”,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富二代。关于国家,过去我们想的是,让穷爸爸变成富爸爸;现在我们想的是,让富爸爸继续当个好爸爸。
当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围观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也许亦怀有“捧杀”的想法——《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联合早报》说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个从未享有过的地位;《朝日新闻》说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金融时报》说世界将会适应一种新方式。
“赶超”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1957年,中国就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然后终于在1995年实现了目标。但这次,中国人对GDP排名世界第二,则是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 “骄傲的GDP它噌噌地长啊,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是网络流行歌《郑钱花》的歌词。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家的态度。
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毕竟,有的GDP,我们是应该拒绝的——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马路不断开拉链带动的GDP,实则是一种退步。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关于GDP的一切纠结与反省,或许皆能让我们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为让公民生活更美好。
中国年轻人在世界的哪个坐标点上?
国际化的青春期片段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期。全球化下的中国青春,与王蒙在《青春万岁》里的青春截然不同。
文/春树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香港制造》这部青春悲剧电影的结尾,在青山荒冢之间,广播里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播放着这段毛泽东在1957年对青春学生的讲话。激昂的励志语调配上悲凉的故事情节,让初次看到这部电影的16岁的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那时我就开始经历和思索着自己的青春期以及“世界”这个概念。
整整十年狂放的青春期,我的每本小说写的都是北京城热爱地下文化和摇滚乐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其中有好些黑暗的东西,好些挣扎、苦痛,当然,亦包含着青春所特有的激情和欢乐。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期,我小说里描绘的青春生活,与王蒙在《青春万岁》里写的青春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年的生活,让我感觉到,国家除了关心GDP以外,还应该有更多需要关注的东西。比如关注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因为青春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年代,都是纯真、神秘、狂妄自大、迷茫、自我挣扎与理想主义的,因为青年人代表着国家的未来。然而我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处境并不乐观,甚至这些年,在大陆的文艺创作都没有出现更多更真实的描写年轻人的作品,尤其是在电影方面。青春是艺术里永恒的题材,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缺席了?一个国家的青春期都被忽视了,那些少年心事难道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有何区别?我们处在世界的哪个坐标点上?难道我们有与他们竞争的能力和实力吗?只有数字是最重要的吗?这都是我感兴趣却无法确切地给出答案的问题,我也在寻找这些答案的路上。
下面,我试图用几个小故事来勾勒一下不同国家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
一
我和美国摄影师David在伯克利小镇的一家典型的美国式餐吧吃饭,这里都是木制的桌椅,柜台前的大彩电里播放着运动节目,服务员是来自于附近大学的学生。我点了一份墨西哥的食物,分量十足,为了避免浪费,我只好告诫自己“北朝鲜的孩子们还挨饿”。David告诉我,以前美国父母教育孩子别浪费饭菜时会说“吃完它!中国的孩子们还在挨饿呢”。
二
前几天,我刚作为中国年轻作家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中俄青年文学之夜”的活动,认识了几个同龄的80后俄罗斯作家。几天后,我一个人去俄罗斯青年作家们住的宾馆找他们玩,我们边喝着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伏特加边用英语聊天。他们看起来比参加活动时放松多了。他们纷纷问我关于中国作家、中国年轻人、中国社会等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1984年出生的男作家瓦列里·别切伊金问的:“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中国年轻人染绿头发?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那么相似?”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噎住了。我说,我原来就染过绿头发。不但如此,北京还是一个音乐重镇,各种风格的乐队应有尽有,punk、skinhead、说唱、重金属、电子、迷幻……最后我告诉他们,因为你们没有去正确的地方。来参加文学之夜的文学爱好者又同时是摇滚乐爱好者的人,几乎没有吧。在中国的主流观念里面,好像染绿头发、红头发就都不是好人似的、就没有资格喜欢文学似的。实际上,文学与音乐都是艺术,完全应该交流和共融。
我们又谈到了各自的阅读。中国老一辈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对苏联文学和苏联作家们推崇备至,而新一代俄罗斯青年作家们则表示,他们不想背负那么大的压力,文学除了吸收经典文化外,还应该向前看。
的确,在交流上面,语言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都不会说对方的母语,只能通过英语交流。不过,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年轻作家和俄罗斯年轻作家有许多共性。
三
我在纽约学英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来自于五湖四海,而内地的学生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上海女生。
有一次我和班上的日本同学一起去逛中央公园,我发现他的英语还没有我的好,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但是他很自信,如果对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不急不恼。这是种良好的心理素质。他告诉我,有一次他跟美国人说英语,对方听不懂他的话,便问:“您还会说什么语言?” 他说:“英语。”
他也比较有钱,一方面是本身家里就有钱,另外就是他在纽约打黑工。他说并不太担心被发现后遣送回国,反正日本人来美国比较方便,停留时间也更长。这给了他们自信。
很快我就发现,班里的韩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最有钱了,他们经常在学校的食堂里点那种不怎么好吃却比较贵的点心来吃;其次就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同学,他们一般不提自己是中国人。
四
我在纽约有个朋友在一家摇滚乐俱乐部工作。每次都有人问她,你是日本人?韩国人?每次她都大声地告诉他们,她是中国人。她曾被这些提问困扰多年,没有人相信一个中国女孩能在纽约的摇滚俱乐部里工作得风声水起。
我去那家摇滚俱乐部玩时,也遇到陌生人问同样的问题。我说,我来自北京,来自中国。他们立刻就说,哦,我知道北京,办奥运会的地方。
五
在柏林时,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男孩驾车一千公里来看我。他是我的读者,买过我的小说的意大利版。他说从来没有来过德国,于是我邀请他来柏林玩。我帮他找了一家青年旅馆。青年旅馆的大厅坐着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只有一张看起来鹤立鸡群的亚洲面孔,但不用问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大陆人。德国的中国人很少,到处旅行的中国人更是少之又少。
他住的房间有四张床位。第一天,只有他一个人住。第二天,房间来了一位亚洲客人。他问我,那位亚洲客人是不是中国人?我说,基本不可能,应该是日本人吧。他后来去问,果然,对方是位日本旅游者。
从硬件上来说,中国年轻人也许没有足够的旅费,签证也是困难重重;从软件上说,大部分中国年轻人缺乏那种非功利性的、主动的独自或结伴去旅行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旅行的中国年轻人少之又少的原因了。
如果有一天,中国年轻人不再津津乐道买了什么名牌包而是打起背包去旅行,我就觉得我们的年轻人有希望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