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后我国大规模立法回顾:民告官开始有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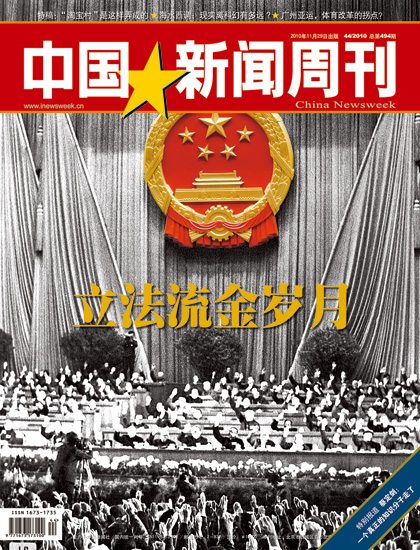 中国新闻周刊2010044期封面:立法流金岁月
中国新闻周刊2010044期封面:立法流金岁月
立法流金岁月
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十年文革梦魇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痛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人治的无穷祸害,毅然决然地与既得权力、利益切割,拥抱法制。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为期十年的立法流金岁月开始了
本刊记者/章文 申欣旺 文/舒琳
2010年10月18日,彭冲逝世,享年96岁。
新华社讣告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
13年前(1997年4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另一位杰出领导人彭真,彭冲的昔日上司和搭档,先彭冲而去了。两位老人远去的背影,勾起人们对上世纪80年代那段立法流金岁月的回望。
生前低调、离职后已多年不露面的彭冲,去世时也是静悄悄的,除了几篇新闻报道外,没有引起社会的太多关注,这和他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巨大贡献很不相配。
在年近6旬的许海星眼里,父亲彭冲一生淡泊名利,有八个字可以形容:儒雅、豁达、淡定、从容。父亲给他留唯一一幅字,上录庄子哲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昔日部下程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研究室主任)的心潮却被掀起,在随后不到两周内,连发两篇纪念文章,深情缅怀这位担任过10余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上司。
程湘清回忆说,2003年,88岁高龄的彭冲接受媒体采访,语气中掩不住自豪:“现在人大目前的基本的程序、制度都是那时候搞的。”
彭冲所说的“那时候”,在尚健在的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王汉斌看来,指的是1979年2月——1988年3月。那10年中,在彭真主导、彭冲和王汉斌等人的配合下,全国人大起草和制定了百余部法律,为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基石。
这三人,在文革动乱中都遭受过冲击。其中数彭真遭罪最大,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关进上世纪50年代他在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时修建的秦城监狱。
1979年复出回到“黑据点”——全国人大时,彭真已垂垂77岁了。此时的彭冲比他年轻,但也64岁了。两位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却被历史再次赋予重任: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副委员长。彭真还兼任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
彭真和彭冲等人刚恢复工作,就立即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无法无天状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中国的法律体系。
“他们一拍即合,两人理念很近,这也是缘分。”许海星评价他父亲彭冲和彭真的关系。
一拍即合,铸就了其后十年中国立法史上的流金岁月。彭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订逮捕拘留条例。文革期间,从国家主席到元帅,包括他本人,都被随意抓起来。
彭冲一上任,便向中央写报告郑重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国徽,而不应是领袖画像。彭冲的建议,中央很快就接受了。
早在建国初期,针对新中国成立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彭真就认为,为适应这一历史性转变,必须把法制建设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从1954年起,彭真连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提供了宪法和法律规范。
接着,彭真又提出要先起草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到1957年,刑法草稿已出了22稿,提交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征求代表意见,大会授权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到1963年已修改到第33稿,并经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同志原则审查过。刑事诉讼法草稿到1963年4月起草了初稿。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还着手研究起草民法。
然而,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一切搁置。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时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保护,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10年过去,从秦城监狱走出来的彭真更加坚定了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信念,他相信只有确立宪法法律的地位,才能防止那种糟糕局面的重演。他再次提到了“历史性转变”:文革结束后,随着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家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劫后重生的他更加清晰地看到,“管理国家,靠人治还是法制?一定要靠法制。”
这些在建国之初就萌发过的意识,由于十年动乱带来的切肤之痛,使得中共领导层认识到了人治的可怕,也使得彭真主管的立法工作快速运转起来。
1979年3月到5月,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全国人大加足马力制定了包括刑法、刑诉法在内的7部法律。年迈的彭真和彭冲等人,像年轻人那样拼起命来。
在旧部顾昂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主任)的回忆中,彭真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在大会堂的办公室、会议室,几乎晚上都亮着灯,连大会堂的服务人员都非常感动。由于过分劳累,彭真发高烧住医院期间,也没停止工作。医院的病房在很多时候就充当了办公室、会客厅等多种角色。
已过6旬的傅洋犹记得父亲当年的忙碌,“他工作量之大是你难以想象的。比方说明天有一个会要开,他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前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那个事。我们回去以后尽量避免跟他谈工作,陪他打打麻将,松松脑子。那时我想给他提点意见,又怕他太累,只好写封信放在我妈那里,让我妈在他不那么累的时候再给他。”
在其后的十年立法岁月中,彭真反复讲,中共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中共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中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针对有人提出“是法大,还是党委大、首长大”的问题,彭真毫不含糊地回应,“我看是法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是主导那个年代立法工作的另一条原则。彭真早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对这一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1982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彭真同志反复强调,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认任何人有任何特权。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在预定的时候宣告完成,现在和当初彭真、彭冲们面临的问题不同,不再无法可依,却时常面临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的困局。
许海星曾在香港工作多年,回到国内看到不好的现象,小心翼翼地和父亲彭冲讲起,未曾料想被骂了一通。许海星认为,父亲虽然不说,心里还是担忧,“父亲那一代人从枪林弹雨中打过来,条件艰苦异常,却从未退缩过。我觉得他始终是坚持民主自由这样一种信仰,从未改变过。”
许海星说,“父亲觉得光发展经济是不够的,要成为强国、大国,还是要有民主法制作为基础。”
对于1979年后大规模的立法,当时许多同志心存疑虑,担心制定了的法律不能执行。彭真在许多次讲话中,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首要的一条是要把法律交给全体人民掌握。”
他进一步阐述说,我们的法律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一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运用这个武器,监督国家机关和任何个人依法办事,对违法行为进行揭发、检举和斗争,就可以有力地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
30年过去,这段话在形式上已经略显老旧,但并未过时,其中真义值得现在的人们深思。 ★
为了人的权利——立法实践点滴
无论是《宪法》,还是《刑法》《刑诉法》《行政诉讼法》和《民法通则》,上世纪80年代制定这些法律时,是为了保障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而这与当时中共领导集体对文革浩劫的深刻反思密不可分
本刊记者/申欣旺 章文 文/舒琳
彭真复出半年后即被中央委任为“两案”(林彪和江青)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这实在令人感叹命运之变幻莫测。当年正是因为这些人,他被关进秦城监狱。现在这些人中,有不少将在这座监狱度过余生。
不过不同的是,当年彭真是遭受政治迫害,如今他却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这次,他希望是在法律的轨道之内,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任何犯罪嫌疑人包括曾给他个人造成极大伤害的“两案”主犯的合法权利都能得到保障。
不能再肆意抓人
“彭真出来后第一次找我,就对我讲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他说,我们没有法制思想,国家主席、委员长想抓就抓,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发生,就要健全法制,制定法律。”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项淳一回忆说。
11月初,彭真儿子傅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父亲复出后,不止一次痛切地感慨,社会主义法制早就应该抓紧搞。可是,我们建国后长时期内没有这个认识,总觉得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方针政策,迟搞几天不要紧,结果贻误了事情。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就很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也得不到可靠保障。
局面纷繁芜杂。彭真选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订了逮捕拘留条例。“在刑法制定之前,为什么先搞这个呢?因为文革中间太多随意抓人,从国家主席到元帅,包括彭本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和程序。”傅洋如此解释父亲的举动。
这个条例开宗明义地宣布,根据宪法“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接着明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但这仍只解决一个不能任意抓人的问题。要系统地保障人权,彭真认为矛盾的核心是要制定刑法等基本法律。
其后从1979年3月到5月,短短的三个月间在彭真的主持下全国人大制定了七部法律,其中刑法、刑诉法、法院和检察院组织法,为1980年的“两案”审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于刑法的制定,争议不大。文化大革命前,在彭真主持下已经修改过33稿,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过的草案可以作为基础。即便如此,彭真仍不满足,他要把“文革”的教训写进去。
但对于刑事诉讼法的认识就不那么统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主任顾昂然回忆自己向彭真汇报刑诉法起草情况时的情景,“彭真同志对我说,过去我们强调实质问题,不大讲程序,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所以要重视程序,刑事诉讼法可以从程序方面保证刑法的实施。”
草案原来规定,刑诉法的任务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 在具体审议草案的时候,彭真提出增加“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傅洋说,彭对证据问题的重视贯穿这部法律起草始末。比如,他把“搜集”证据改为“收集”证据,在证据前加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这些细节闪耀的是对人权保障的光辉。曾长期在彭真身边工作的顾昂然在回忆录中认为,这些思想在当时非常重要,说明彭真深刻总结了“文革”教训,真正在依照法治精神来主持制定法律。
比如1979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这句话就是彭真提出来的,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严格限制逮捕条件,不能再像文革那样,不讲规矩,不讲条件,肆意抓人。
顾昂然回忆,当时有人提出草案仍不成熟,在政治局讨论两个草案的时候,邓小平表示,刑法、刑诉法草案比较成熟,肯定还不完善,以后可以根据实践进行补充,不要等完全完备了再制定。
受文革冲击、有着切肤之痛的决策者们就此达成了共识。傅洋说,实际上,这七部法律大概可以分为几大块。一块是政权重建的法律依据问题。文革期间,在“造反”和“夺权”有理的号召下,法律被废弃,政府机构被砸烂,无政府主义盛行。一系列的组织法,包括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首先解决政权机构恢复的燃眉之急。
第二大块是人权保障。“文革期间,刑事逼供,捏造陷害,什么都出来了。所以文革后刑法、刑事诉讼法抓得特别紧。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打击犯罪不准确,人民也没法保护。更不能对人民肆意迫害。”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更多关于 立法 宪法 的新闻
- 部分人大委员建议完善立法严惩渎职侵权 2010-10-28 07:30
- 中国物权立法历程:从未如此曲折 从未如此坚定 2007-03-22 14:34
- 中国2004年民主与法制建设 催动国家劈波向前 2005-03-06 12:53
- 法治在线特别节目:我们身边的法(图) 2004-12-06 14:51
- 蔡定剑其人:把宪政文本变成一种现实生活 2010-11-25 1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