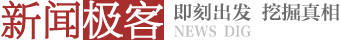阿培从4岁起便经常在白天犯困,一天可以睡上15个小时(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
阿培从4岁起便经常在白天犯困,一天可以睡上15个小时(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当阿培告诉亲朋,这么多年她随时随地都可以入睡,其实是一种病时,没有人相信她。
在国外,这种病被称为“Narcolepsy”,翻译成中文叫“发作性睡病”。不可抗拒的短期睡眠发作是它最明显的特点。在美国,它的发病率约为1/2000。
虽然至今仍原因不明,但这种疾病早在1880年就被发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理解,能睡觉难道还是病?
“我的朋友常和我开玩笑说,我的生命里1/2在睡觉,剩下的1/2,一半时间在丢东西,一半时间在找东西。”
阿培说,她从别人眼中读出的是耻辱感。
“发作起来,地上有把尖刀也会倒下去”
 为了避免误事,她会抓紧一切时间“补觉”(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
为了避免误事,她会抓紧一切时间“补觉”(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
22岁的阿培,身高1米72,皮肤白皙,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主修商科。在一些老外和中国留学生眼中,她是才貌兼得的女神。
很少有人知道,阿培是一位发作性睡病患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瞬间睡去。
这是一种至今仍原因不明的罕见病,在美国,发病率约为1/2000。最主要的症状一共有四点:白天嗜睡、猝倒、入睡前幻觉和睡眠瘫痪。这些也被称作发作性睡病四联症。
白天嗜睡是判断是否患病的基础。调查显示,100%的患者均存在白天嗜睡,65%—70%有猝倒,12%—50%会出现睡前幻觉,以及15%—34%存在睡眠瘫痪。
这四种症状阿培全部具备。最初的记忆来自4岁。
每次坐摩托车时,父亲都会用带子把她在后座上捆好,因为她睡着后会跌下来。家人和阿培想尽一切办法,喝咖啡、掐胳膊,大喊大叫,所有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她入睡。
小学、初中、高中,阿培几乎都是睡过来的,同学叫她“特困生”。每当惹事、犯错老师向她走来时,她都会因为害怕而感觉全身无力。
“这就是猝倒,也就是比较典型的情动脱力。当你情绪发生变化时,你的肌肉会失去张力。感觉就是所有的神经冲向你大脑最外层的皮膜,一下子顶住,然后你的身子就不听使唤了。”阿培告诉新浪《新闻极客》。
在上下学的路上,她几乎不能一边骑车一边听同学讲笑话。在欢笑中,她必须停下车来,扶着车把支撑身体。“你的意识是清醒的,但身体完全不受控制,如果不能支撑好,即使地上有个尖刀,你也会倒下去。
 每次醒来阿培都要思考哪个是梦境,哪个是现实(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
每次醒来阿培都要思考哪个是梦境,哪个是现实(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比猝倒更让阿培觉得恐怖的,是四联症中的睡前幻觉。
因为会瞬间睡去,马上进入快速眼动时期,发作性睡病的患者,经常会在梦里出现几秒钟前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开车时很恐怖。你觉得你仍在开车,其实你是在梦里,在现实中你已经睡着了。”
“如果是一些恐怖的梦。因为环境和入睡前的现实没有任何区别,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醒来后,阿培也常会伴有幻觉。“明明是梦里发生的事情,但因为太过真实,你也会在醒来后,觉得已经在现实中发生过了。”
“这尤其会让小孩子感到崩溃,会尖叫、发怒,醒来后击打东西。因为他分不清哪个是现实,哪个是梦。”
尽管如此,阿培一直都不知道这是一种病,直到在南加州念到大三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那也是我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一天要睡15个小时。当时课业压力很大,有很多事要做,但闹钟响了,我就醒不了。闹钟就在身旁,但和我的距离就像不在一个世界。”
阿培告诉《新闻极客》,这种俗称的“鬼压床”,就是四联症中的睡眠瘫痪。
“其实我的大脑已经醒了,但身体就动不了,怎么挣扎都不行,必须要等上30分钟或1个小时。好几次我都急哭了。”
 床有时候对她来说,更像个牢笼(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
床有时候对她来说,更像个牢笼(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寻找“觉主”:中国或有70万发作性睡病患者
为了解决“嗜睡”和“鬼压床”,阿培做了包括颈椎在内的多种检查,但结果均无异常。
“一位美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得了narcolepsy(发作性睡病)?”
在朋友的提醒下,阿培查阅了相关资料,结果让她崩溃。“我哭了,因为我是四联症患者,每一个症状,每一个字都是我,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在脑袋被连接了无数仪器后,阿培在医院睡了一晚和一个白天。做了详细的整夜多导睡眠监测和白天多次小睡试验。
14秒钟入睡、31秒钟做梦,监测的结果让医生感到吃惊,“他说我的好多项数据,都破了医院的记录,之前没有谁的大脑能像我这么快入睡。”
那位医生同时告诉她,因为病因不详,目前发作性睡病只能通过药物抑制,并不能根治。
2014年年底,阿培假期回国。她把自己患病的事实告诉给家人和朋友,却没有人理解。
“我严肃地告诉我父母,他们觉得就是神经衰弱,我带着尝试的态度给朋友普及,被当成笑话。本来想畅快地抒发下,却搞得内心一片伤心委屈。”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阿培开始寻找病友,“我很想知道他们在哪,按照1/2000的发病率,中国至少应该有70万发作性睡病患者。”
但她很快发现,国内仅有的几个维系病友的QQ群中,充斥着医托、骗子和负能量。
“我X,这怎么能忍。明明没法根治,国内却有不少中医大夫,保证药到病除。一个疗程就1万多。”
阿培的质疑,得到了病友的支持。也正是从那时起,她开始以美国名牌大学病友的身份,进入了中国的发作性睡病患者圈。
 在中国确诊的发作性睡病患者仅为4000余人,不足发病率的1/100(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
在中国确诊的发作性睡病患者仅为4000余人,不足发病率的1/100(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我后来了解到,很多病友都因为嗜睡影响了生活和工作,过得都不是很好,情绪也很失落,好多人更是病耻感严重,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有病。但其实我们怎么了,又不是什么得了绝症、传染病。”
事实上,国内的大多数发作性睡病患者,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虑症状。
为了能传播正能量,阿培和病友们将自己统称为“觉主”。
“我们不想称自己是患者。也不想强调它是一种病,最开始起了‘特困生’,‘秒睡君’、‘睡神’什么的,但还是有些贬义,最后定了就用‘觉主’”。
此后的几个月里,阿培拿出了原本用来创业的1万美金,制作了两个视频,在几个主要视频网站上推送,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发作性睡病。并开始制作网站,在微信、QQ建立新的联络群,还抽空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公益选拔赛。
她希望能尽快搭建一个发作性睡病互助联盟的平台。“让大家在精神上相互支持,心态上相互开导。”
随着群内成员的不断增多,2015年8月中旬,阿培决定组织一次线下聚会,面对面的和大家交流。
 即便做节目化妆时,她也会睡着(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
即便做节目化妆时,她也会睡着(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我们的CPU太强大了,所以电池老不够用”
 聚会现场,阿培组织各位“觉主”发言(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
聚会现场,阿培组织各位“觉主”发言(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出发那天,阿培特意穿了一条红色的超短裙。
她希望展现出性感、健康的一面,能带动起大家的情绪,“希望聚会能充满正能量,并能通过大家传递出去。”
一位朋友为聚会提供了会议室。算上家属,“觉主”一共来了7位。
简单的寒暄后,他们开始了自我介绍。
在大家的怂恿下,来自河北的霍先生第一个发言。
“他已经被憋坏了。”一位觉主笑着说道。
霍先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公司里负责技术支持。他坦言自己有很多话想说,因为除了病友,大家对他的病情总是“一笑而过。”
霍先生5岁时发现自己有发作性睡病。在中国,2/3的发作性睡病患者的起病期都在儿童时期,比西方要早7—8年。
在农村长大的霍先生经常和哥哥一起去看露天电影,但每一次他只能记住开头,因为很快就会进入梦乡。
“直到今天,我都不能看连续剧。”他笑着说。
因为白天嗜睡严重,霍先生在高中时,成绩出现了明显下滑。“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老师刚才还在黑板上讲第一道题,我一睁眼就发现已经到最后一题了。”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了老师对于好生和差生的区别。我以前都是尖子生,后来成绩不好了,老师就……”霍先生叹了口气。
他还记得高考那天,自己还曾短暂地睡去。“不然根本坚持不到最后。”
 聚会中大笑让阿培感到无力,不得不用电脑撑着脑袋(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
聚会中大笑让阿培感到无力,不得不用电脑撑着脑袋(摄影:新浪图片王丹穗)和阿培一样,霍先生觉得这一切算不上灾难。
“你说这是老天对我们不公平吗?我觉得不是,因为初中时,我给过好多同学讲题,发现怎么讲他们都不明白,他们没有睡病,但不也一样很痛苦吗?”
霍先生的猝倒并不严重,但有时候情绪激动时,会出现短暂地面瘫。“那时我就捂着脸,低一会儿头,等情绪平复了再继续说。一开始,领导老以为我在做鬼脸。”
如今,霍先生每天7点—8点都一定要在公司的班车上睡上一觉。“如果坐公共交通,我一定从总站上车,必须要在椅子上睡。”
坐在霍先生对面的刘小姐,也同样有自己应对睡意的办法。
“我就是每次上公共汽车,就往后面钻,因为后排的两座之间,后轮上面的位置,有一个空地,我就两手抓着座椅扶手坐在上面睡。”
刘小姐来自黑龙江。她10岁左右就发现自己很能睡,买了很多雀巢咖啡都不管用。
大专毕业后,她曾被分配到富士康工作,每次想睡时,便以上厕所为名,跑进去睡上一会儿,“那地方没有坐便,我就靠在墙上睡。”
刘小姐告诉大家,在上学期间,她甚至走着走都能睡着。醒来后,总是有强烈的饥饿感。“就是你别让我看到吃的,看到就一定要吃掉。”
刘小姐说,那时她的体重开始以每年10公斤的速度增长。事实上,大多数发作性睡病的患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发胖。“所以,我刚看到你就想,怎么还有你这么苗条、漂亮的觉主。”刘小姐羡慕地对阿培说道。
“我可能是个例外。”阿培也笑了。
“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聚会。其实我在来之前,还有担心,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医托的局?”一位5岁患者的小姨告诉大家她的担心。
“你不用担心他,我的小儿子现在也有睡病的症状。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聚会结束后,霍先生特意走到了她的面前。
虽然没有研究证明发作性睡病具有遗传性,但部分患者发现自己的家属中,也有类似的病状。但霍先生坚信,自己儿子的生活,不会被疾病拖垮。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CPU太强大了,所以电池老不够用。”站在那位女士的对面,他微笑着说道。
图片故事—“我被‘睡神’附体了:http://slide.news.sina.com.cn/s/slide_1_65716_88287.html
(新闻极客谷力北京报道)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标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或个人不得全部和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