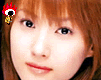| 解密:宋庆龄是否冤枉胡适--谁对开除风波说了谎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11/02 18:29 中华读书报 | |
|
1932年12月18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成立宣言,成员还有杨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随即开展了一系列营救政治犯的活动。1933年1月17日,上海分会成立,宋、蔡、鲁、杨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杨铨为总干事;1月30日,北平分会成 翻开《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3年第2期,读到邵建的《胡适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始末》和陈小雅的《宋庆龄开除胡适》两篇文章,拜读之后,不禁为两位作者的大胆而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胡适当年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的历史真相,本来是很清楚的,并不存在什么争议,可是在两位作者的笔下(两位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也大体相近),这事显得扑朔迷离,而更惊人的是,他们居然认为这事是出于宋庆龄对共产国际的“亦步亦趋”,而由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一手制造的假材料所造成,令人大跌眼镜。 两位翻案者认为:当胡适和杨杏佛等视察了北平陆军反省院之后,上海方面民保总盟发表的一份据说发自北平陆军反省院的政治犯的控诉书,却说那里有严刑拷打的现象,这份材料有伪造之嫌。当胡适指出后,宋庆龄的解释与胡适“对不到一起”,之后,上海方面的蔡元培、杨杏佛实际上向胡适承认了错误;当胡认为同盟不应该以“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为宗旨时,宋等即指责胡公开反对同盟章程,并开除胡适。其中,史沫特莱指手画脚,甚至有“领导宋庆龄”的腔调。翻案者认为,今天看来,胡适“对于民权运动‘性质’的界定是科学的”,如果同盟能够正确地吸收胡的观点,并调整与胡的处理方式,或许同盟的命运就不是短命的半年了,甚至“中国也早已不会是这样的中国”,这真是从何说起!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如果二位说的是实,则无论我们如何客观看待,如何转换视角,而宋庆龄冤枉胡适违反同盟章程的结论,是铁板钉钉,无可辩驳的了。何况还可能有弄虚作假之嫌,更不用说种种极“左”之病了。这已涉及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及杨杏佛等历史名人的人格,故更不能不细加辨析。 一,谁说了谎? 翻案者认为:胡适在1933年2月3日和5日收到两样东西,从而认定上海方面发表的所谓“政治犯”的控诉信是“捏造”,这一判断是可信的。这两件东西,一是韩麟符的求助信,“他已经在反省院关了两年多了,如果有拷打,他在信中完全可以以实相告”,二是《世界日报》转来的李肇音的信,居然假借胡适的名义,显系伪造。因而,上海总盟发表的控诉信也是伪造的。造假的人究竟是谁呢?陈小雅认为,有可能是同盟“自己人”所造,而史沫特莱造假的嫌疑最大。其根据是什么呢?是对史沫特莱给胡适的信与“托名信”作的“亲子鉴定”,认定:“李肇音的‘托名信’与史女士的信具有类似的性质——它丝毫不理会别人会‘存疑’,一如她丝毫没有考虑别人读她信的想法;它忽视胡博士的‘名誉’,一如她忽视‘程序正义’;她客观上是要把发表的名誉‘强加’于人,一如她要把发表的‘结果’强加于人”。由于她的“道德胁迫”,逼反了胡适这位同盟中的“卢俊义”! 这些说法,委实武断得可以!由史沫特莱受同盟的委托写给胡适信中的口气比较强硬,居然可以得出与李肇音的“托名信”具有类似的性质!她的信口气再不妥,也完全不存在虚假的问题,李的信再假,也不等于强加于人,怎么能扯到一起呢?况且,反省院政治犯的控诉书,由史向同盟提交,也并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因为,史沫特莱当时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由她提交完全正常,由她出面写信也完全正常。她提交会议的时候(25日),胡适等还没有视察反省院,根本不存在造假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写此信的实有其人:是刘尊棋(见《人民日报》1981年度报告所载刘尊棋:《庆龄同志,感谢您的救援》。胡适自己在给人的信中提到视察时所见的“刘质文”就是他)。其信为1月10日所写。虽说刘尊棋后来的说法有些细节(如说杨向他核实情况)难以确证,或者说某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却也没有更有力的证据来推翻他写信的基本事实。至少,这信是他所写,已无可辩驳。这就有力地打破了“伪造”的指责。时过70年,翻案者明知结果,却来讨论此信的真实性,真不知是什么意思。 其次,即使是李肇音的信,虽说假借胡适推荐的名义显然愚妄,但不等于其信的内容不真实。从“实证”的角度看,可以从两个方向假设:一种可能性是捏造,从内容到寄信人、地址全都是假的,胡适和现在的翻案者都持此看法;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李信的内容是真实的,但倘就以他本人的名义要求《世界日报》发表,该报未必肯发,如果他为了争取刊登,而假借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会长胡适推荐的名义,以图顺利发表,也就不奇怪了。因此,不能因为假借了胡的地址,就认为一切都是假的了。 诚然,当时总盟也认为李肇音托名信的出现是严重的事,所以会有紧急的长时间的讨论。很显然,同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但讨论之后,还是取得了共识:上海方面在没有与胡适等视察者沟通的情况下发表政治犯的信,可能未必尽当,但胡适的反应也显然过分了,尤其是他把矛头直指宋庆龄,还诬枉宋庆龄及史沫特莱“以一二人擅用总会名义”,是有悖事实,也是同盟所不能接受的。但鉴于胡适当时的情绪,也不宜遽加指责。为防僵化,所以才决定由蔡元培等出面向胡适婉转地作了解释,并表示“故此文若不宜由本会发表,其过失当由本会全体职员负责,决非一二人之过,亦决非一二人擅用本会名义之结果”(2月13日蔡元培、林语堂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87页),翻案者认为这就是认错,其实,是误解的。这封回信的措辞是很有分寸的。首先,它说的是“若不宜发表”,并不等于认定不宜发表;其次,它着重强调的是:发表这信是同盟总部“全体职员”的集体决定,决非胡适所指责的那样系“一二人擅用总会名义”。蔡等这样说,显然是出于缓和关系的考虑。事实却并不一定像胡适所说的那样,也不一定像翻案者所想象的那样。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这封信是真实的;第二,总盟不想把内部矛盾暴露出来,希望维护团结。如果说,总会委婉地表示了“不宜由本会”发表,也不等于确认它是假的。蔡、杨是顾全大局,不纠缠于小节,才这样表示,而宋庆龄面对胡适显然诬枉的尖锐指责,也没有作出强烈反应,这都是“君子风度”的表现。而胡适,人常以“君子风度”誉之,但这回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君子风度”,不但不接受蔡、杨的解释,反而借题发挥,发表了与同盟宗旨相悖的言论,似乎有心要把事情搞僵。 其实,当时监狱究竟有无酷刑,不仅鲁迅,蔡、杨等无不认为当然,即使是胡适,他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我一查《胡适来往书信选》,却就有了令人吃惊的发现:就在当时,他收到的信,并不是两件,而是有好几件。除了韩麟符、李肇音外,至少还有四封,却是每封都明确说有酷刑!人们来看几封:1月24日,千家驹致信胡适说: 近数年来,国民党执政之结果,青年冤死与莫须有之“反动”罪名下者不可以数计。在狱中有十三四岁的青年。惨遭种种非刑的拷打,度着比地狱也不如的生活……(中册第158页,黑体为引者所改,以代着重号,下同。) 2月2日,被关押在北平军事委员会军法组的北大旁听生杨韶秀致信胡适说: 学生……十二月九日晚,因政治犯嫌疑被捕,一周之中展转三处,严刑加身,强迫成招。……(中册第173页) 如果说,这还都不是讲反省院的,那么下面这封却正是讲反省院的。胡适等视察反省院后五天,2月4日,被判无期徒刑、关在反省院的周默秋(他是胡适在视察时与胡适谈过话的)躲在被窝里写信给胡适,说: 自从那天和你见面之后,即想写信给你,可是我们是不许有笔墨的,……如果我们在监房里被搜出了笔来,我们是要受严重的处罚的。……先生,你得救我呵!非人的生活,真过不下去呵!受审时,我捱了三次酷刑,……看看吧!每天十二时,何时不有青年学生被拷打的哭声!那个刑场里不有青年学生的热血?(中册第175-178页) 信末还特别关照:“如有来示……绝不要公开寄反省院”,可见其恐怖,也可见视察时周根本没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还有一封未写明时间的(应在此前后)署名关仰羽的来信,长达六千余言,详细记述了他本人被关北平宪兵司令部十三天中遭受“酷刑拷打,惨无人道”的经历,并请求“设法拯救无辜,保障民权”。(中册第193-202页) 这些信极其明确地指明了北平的监狱和反省院中确有酷刑!奇怪的是,胡适收到的同类信大多明说有酷刑,他何以偏偏只选了李肇音的信大做文章,而却不拿出千、杨、周、关等人的信来呢?谁能料到,当胡适义正词严地指斥揭露反省院酷刑是作伪的时候,他家里却还藏着好几封揭露监狱、反省院酷刑的信!究竟是谁在说谎呢? 其实,就是韩麟符的信,也说:“不过在匆忙中,特别是这样的环境下,可惜不能说个痛快……”(中册第160页)这说明,胡适等与犯人的谈话是在怎样的氛围中进行的,犯人的自由度有限得很。另外,韩本人身份比较特殊,他固然未必受到酷刑,但却不能排除别人受到酷刑的可能性。 最后,即使反省院确实较少酷刑,其他监狱却多的是。这一点胡适是清楚的,他为什么要抓住同盟发表的材料大做文章,几至否认所有监狱的酷刑呢?也许是因为说的正是他刚刚视察过的反省院,使他难堪了。但倘如此,便已经有失“君子风度”。其实,胡适的过度反应是有点耐人寻味的:他不是感觉被监狱欺骗而是感觉被同盟欺骗。如果胡适是站在同盟的立场上,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首先据此追问当局有无隐瞒以欺骗视察者(当局知道胡适等次日要视察反省院,当夜或次晨紧急布置,乃是易如反掌。后来杨杏佛揭露,正是如此)。而不应该轻信视察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胡适指责同盟轻信控诉信,事实证明,是他自己轻信了当局。韩麟符的信也可以表明,犯人与视察者的谈话不可能“说个痛快”的。如果胡适真的是“执著于‘责任伦理’”,抱持“程序正义”,那么他应该懂得,自己没有看到的不等于没有。这也是考据学的原理。再说,即使他确认该反省院没有酷刑,也不必做出类似“窝里反”的举动。胡适的反应显示,他虽然不满于当局的一些方面,但却不能容忍当局受到不公正指责,而对民权运动虽然表示赞同,对同盟却不那么宽容,令人觉得他是抓住同盟的工作漏洞,有意激化矛盾。 二,胡适是否叛盟? 翻案者认为,胡适反对同盟提出“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没有错。一方面,在此之前,同盟并未正式提出此一口号;另一方面,这个口号本身是错的,胡适反得有理。同盟如果不是在宋庆龄出于对“第三国际”亦步亦趋,从而与史沫特莱“擅断”从事,就不会那么短命。 这也可谓匪夷所思。事实上, 在同盟成立之初,就公开发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载《申报》1933年1月18日),其中提出三条宗旨: (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 (二)予国内政治犯与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 (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这里再明白不过地提出了“释放政治犯”,虽然没有用“无条件”和“一切”的用词,但看总的精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无条件”和包括“一切”政治犯的含义。一则因为“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到之处习见。甚至青年男女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政治犯”已成为当权者滥施淫威、压制舆论、任意抓人杀人的借口。二则《约法》规定的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力已被无形剥夺,很多被捕者就以此被捕。其实,即使是“合法”逮捕的“政治犯”,也得不到法律保障,因此,惟有给以人生、言论自由权,方可论是非。
|
| 新浪首页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