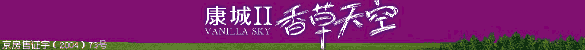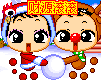| 竺可桢日记探秘:原子弹的故事应从1952年讲起(2)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12/30 15:32 中华读书报 | |
|
(三)雷称与竺“谈了三个多钟头”。竺记谈话是在晚间进行的,按日记正文,竺当日上午是在院内遗传育种馆陪苏联专家,直到下午两点才回到院部。三点钟又参加陶孟和副院长的检讨会(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因此他接待韦、雷,应该是在晚饭后。他当日晚间还要回家写自己的检讨发言稿,不大可能与雷谈上三个多小时。 (四)竺可桢是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不是原子物理学家和流体力学家。雷英夫所列 雷的回忆写于1990年10月20日,似为编写《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撰写的回忆史料。 199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中称,1952年5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军委领导人在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酝酿过发展特种武器问题,并征询过有关科学家的意见,从各方面进行准备,积极创造条件”(见该书上册第26页)。书中似在原则上采纳了雷英夫的忆述,但未录其细节,把雷文中模糊不清的“原子导弹”之类改称为“特种武器”,将雷文中的加了书名号的《五年军事计划纲要》文本表述,改成了加引号的“国防建设五年计划”的一般表述。其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1年2月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后,1952年国防方面将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是《兵工五年新建设大纲》,而非《五年军事计划纲要》。 据史料翔实的权威性文献《周恩来年谱》,其中与本文主题相关者,只见1952年5月21日记有周恩来“和聂荣臻、李富春签发中央兵工委员会《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决定》同意中央兵工总局提出的《兵工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基本同意《兵工五年新建设大纲》”。(第239页) 近代中国的语汇中,相延以“兵工”指称国防工业。国民党政府在军政部之下设“兵工署”。1951年1月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之下设“兵工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兼主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兼副主任。 直接大段引述雷英夫忆述资料的出版物,有1994年出版的《开国总理周恩来》,文见该书第402-403页,与雷文相比,此书中只是把 原子导弹 分述为“原子弹、导弹”,删掉了“核潜艇”。 竺可桢与韦明、雷英夫之间进行的是一次保密的谈话,他应该遵守保密的要求。但是,坚持了几乎一生记日记的竺老,不可能不在日记中留下痕迹。他没有将谈话内容写入日记正文,只在天头处以Sunbuist做为“原子弹”的隐语。从雷英夫问及“防护措施”和竺可桢提及专门人才钱三强等线索来看,谈话的中心内容只应该是围绕原子弹的。这次谈话的起因,也只能从与原子弹相关的线索去寻找。 1952年3月,大的历史背景是,朝鲜战争已经打了将近半年,中国领导人已经从战争实践中深刻意识到了提高军事现代化水平的紧迫需要。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中国必须从长远战略上做出回应。 一个具体的契机,有可能来自法国科学家约里奥 居里。据《钱三强年谱》(葛能全编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1951年10月记述:“放射化学家杨承宗由法国回国并至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离法前,约里奥会见杨时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杨回国后即把这些话先后告诉了钱三强和中央宣传部科学处联系科学院工作的龚育之。钱请丁瓒报告了中央有关领导。” 约里奥 居里是核物理学家,法国共产党党员。钱三强赴法留学期间即在其实验室工作,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经钱的推荐,杨承宗于1947年初到居里实验室工作,担任约里奥 居里夫人的助手。杨承宗回国后,来到钱三强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钱三强还与丁瓒二人分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正、副局长。丁瓒在党内担任院党组副书记,对上可以直接与领导中国科学院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实际归口于中宣部)副主任陆定一和秘书长胡乔木对话。 综上所述,约里奥 居里向毛泽东提议搞原子弹的进言,似可理出较为清晰的通道:约里奥 居里→杨承宗→钱三强→丁瓒→陆定一或胡乔木→毛泽东和周恩来。其中的中间环节也有另一种可能:杨承宗→龚育之→陆定一。据葛能全先生告诉笔者,龚育之等人当时曾在近代物理研究所调研过一段时间,杨承宗是在那时将约里奥 居里的话转告给龚育之的。 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兵工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指派韦明和雷英夫于1952年3月27日拜访竺可桢。相约晚间一谈,表明了任务之急或是保密之严。竺可桢提供了个人意见,以凝聚人才、资料设备和经费投入三项为筹划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必备条件,被周恩来赞为“内行话”。 四个半月之后,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主要任务是与苏联通报中国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就此与苏方交换意见,争取对方的援助。代表团成员和顾问中,除中央财经系统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之外,来自军队方面的人员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可以想见“兵工”在计划草案中所占的分量,其中当然会包括在原子弹研制方面的要求。 没有竺可桢日记中的那一行字,雷英夫的那一份回忆材料将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谜团;没有雷英夫的回忆,竺可桢的那一行字将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两者相互印证,则为我们破解了共和国历史上有关原子弹研制事业发端的一个秘密:中国最高领导层关注筹划原子弹研制的时间,是在1952年。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