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风流:侯宝林最腻味别人当面叫他侯宝林儿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01/06 17:04 科学时报 | |
|
“林儿”字的伤感 侯宝林是最腻味别人当面叫他侯宝林儿的。这一“儿化韵”在他看来“轻蔑”的意味更多于“亲昵”,总是与“小”、“贱”一类侮辱性含义相关的,甚至还表现出对相声这种“艺术”仍然当做“玩意儿”、对他这样的“艺术家”仍然当做“说相声的”或“臭说相声的”错误看法。每每遇到这类情况,他那极好的情致就会一落千丈,使自己与对方都陷入极 七八十年代之交,他曾两次到北大、南开讲学,并被北大聘为兼职教授。去北大我是陪同,来南开我是接待。两次都做“助教”为其板书。在北大小礼堂那个多国元首和世界名人曾经讲演过的讲坛上,他侃侃而谈说古论今,从俳优谈起中国讽刺艺术的源流。台下正端坐着我的老师朱德熙、林焘等先生。我为他也为相声感到荣耀。来南开也在小礼堂,我曾组织学生观看他的“白沙撒字”,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此之前校长们曾去住处看他,谈笑间也请他表演一番,我想这绝不是恶意的。没曾想他却正言厉声地说:“我是来讲学的。”言下之意:听相声可到剧场买票。好在校领导旨在寒喧,并未察觉。事后我曾向他解释。他说:“我明白,但还是得强调说相声与作报告的区别。”实际在他的报告始终,都串珠般地连缀着妙语与雅谑,是他的任何相声表演都无可比拟的。尤其是他的学唱,在“文革”十年绝响之后是那么绝妙动听,仿佛把曾经遗失了的历史文化和民众生活,都一下子在其惟妙惟肖的叫声小调中寻找回来了。 送别他时,侯宝林说:“‘文革’的创伤无论多甚,都不及一个‘林儿’字伤害深。”接着,他又告知我:“牛虻”做小丑的那种心情你理解吗﹖我明白他是指那本《牛虻》小说。他还说:喜剧演员的内心深处总有严肃的东西,伟大的喜剧大师无不如此。是的,侯宝林从来都是一个严肃的人。惟其如此,他才以一生的追索为把相声由“玩意儿”擢升为“艺术”而努力;为把自己由“说相声的”变为“艺术家”而奋斗。他说:“说了一辈子相声,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最需要的就是一点尊严——一点做人的尊严、一点艺术的尊严,人老了尤其如此。” “一户侯” 七八十年代之交,侯宝林对书法突然发生兴趣,每日挥毫不止。求墨者众,侯对日益长进的书技也是自鸣得意。于是,便有吹捧者生,说是笔墨如何气势如何,比得上谁胜得过谁,云云,溢美之辞不绝于耳。我提醒侯:“你可是‘名人字书”,绝不是‘字书名人’”侯宝林笑笑说:“我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我还暗示他:“当今说好话吹捧你的,或是当年以恶语伤害你的,虽然不是同一个具体人,但却是同一种人物类型。”侯宝林说:“我知道整人者总整人,被整的总挨整不是﹖”侯宝林兴奋地在一沓题字中逐张指给我看:“我不是为了写字而印章,只是因为印章而写字。”这时,我才看见一副闲章印文为“一户侯”三字。“怎么样﹖”侯宝林神采飞扬地问我,并从抽屉里取出那枚由鸡血石刻的随形章。“字是请别人刻的,词儿可是我自己出的。”我连连点头称是,说:“好‘一户侯’对‘万户侯’妙极了!‘万户侯’已成‘粪土’,‘一户侯’或可永存﹖”侯宝林泰然地笑了。 记得1966年春天我与侯宝林等人去上海体验生活,在下厂前的欢迎会上,上海宣传部门请我们看文艺节目,内中有后来成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清唱片断,演唱者是侯宝林熟知的童祥苓先生。我就坐在侯宝林旁边。侯附耳问我:“你对他印像如何﹖”我说:“唱得很好。”侯说:“我是问你他的性格﹖”我思索了一下便说:“这个人高傲吧﹖”侯说:“对极了,何以见得﹖你看,他、你和我在鼻沟下都有两道深陷的傲纹。”我看看他、他看看我,我们同时都笑了。那时的侯宝林虽已是“知天命”之年,但仍有追风揽月的盛气,以为凭他超凡的禀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他总是极其清醒地看到别人的长处和短处,并把它们迅速地转化为自己的财富:或是引以为戒的镜子,或是出奇制胜的法门。“好风送我上青云”,他已经飞入云端了,或许还能够扶摇而上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和他的民族陡然跌落了下来,由座上宾而阶下囚,没有因由也没有道理,极其轻易和随便,这不是劫难又是什么﹖而在劫难面前,人的一切又是何其微不足道,封侯又如何,万户又如何﹖还是“一户侯” 好,一是平实二是自由,虽是毫末与草芥,但却尽享春华秋实的天年。因之,他从干校回来就变了一个人。按理说那勒着肚皮省下的补发工资,大约是五位数字,足可以积蓄备老。他却在顷刻之间浑洒而尽了,满屋子的破桌子烂板凳,还说是价值连城的硬木家具,到处都是砖石瓦片残铢旧币,都把它们当成古玩玉器收藏了起来。我深知:他不是待价而沽,也不是传给后代,而是在挥洒中宣泄一种逸气、寻求一种尊严,获得一种“一户之侯”的自主和自得。 摘自《一户侯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7月版 (编辑:燕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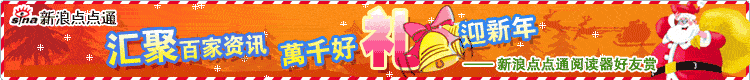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