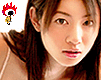后来又让冯雪峰和林迂道两个人搞一本文类辞典,这是个闲差事,没事干就编吧,十年、八年地编去吧。他们在四楼,我在三楼。每到中午休息他就叫:“牛汉,中午到我那儿休息一会儿,聊聊天。”这样谈了不少事情。
冯雪峰其实是个重感情的人,他内心非常非常单纯,到死都有他非常单纯的一面。我认为他不适于做政治工作。
他的起点是1921年晨光社诗人,后来和应修人、潘漠华组成湖畔诗社,到晚年他也说:“我最看重的是诗人的头衔。”其实他就是个诗人。现在诗坛没有给冯雪峰的诗以应有的地位,而是主要侧重他的文艺理论方面。我觉得他的诗写得不错,诗品很高。当然他的诗结构上有弱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但他写得很真实、很诚恳。
1958年以后他写字也有些困难,所有表态的大字报,都是我代他写的。他说:“你的字写得好。”我说:“就说让我给你劳动就行了。”1958年反铁托的那个时期,大概是让说体会吧,他写,非他写不可。他想回到党内。我俩有时聊起这件事,都坚信事情迟早会搞清楚的,迟早会恢复的,不会颠倒黑白一辈子,不会冤枉一辈子的,就是我们死了,将来后代还会为我们平反的,但是材料要写好。
“文革”中我和冯雪峰一起睡大通铺,他睡边儿上,我稍靠中间一点儿,两个人合用一个一头沉的办公桌,他开玩笑地把他的景泰蓝烟灰缸往中间一放:“我不侵占你,你也不要侵占我啊。”他要写的材料特别多,几乎天天有人找他写外调材料,每一份材料都要一式三份,外调人员一份,交本单位造反派一份,自己留一份。用复写纸写三层,使劲写,右手写得都僵了。有一次,冯雪峰又表现出了他软弱的一面。当时造反派分成两派,以前交的材料只让其中的一派占了,分出的一派也要他交材料,这样就成了一式四份了,写起来更费劲,更困难了。可能是1967年的二三月吧,我记得造反派来了一男一女,都是二十多岁,他俩是另外一派的,来了就让冯雪峰把所有的外调底稿都交出来,逼他拿出来。我在旁边对他说:“不能交。”冯雪峰也对他们说:“这个材料不能交给你们,因为里面记着好多事,经常有重复的就照抄了,省好多事。我也没有精力再重写了,写起来太困难了,你们就多体谅我吧。”很诚恳的。但是那两个人一直坚持:“不行,非交不行。”后来就要上来抢,没办法,冯雪峰最后还是交出来了。交了以后,冯雪峰当时就号啕大哭起来:你们这样逼得我怎么办呢?什么都交出去了,如果再要重要材料我记不清楚,前后不一致怎么办呢?该说我说假话了。我得有个根据,要体谅我这个,可是他们一点儿也不体谅。冯雪峰在性格上就是这样。当时不能交出去,交了也不用哭,有什么好哭的呢?而且是号啕大哭,我就不哭。这点上我比他野得多,我不哭。冯雪峰就是这样一个人。普通人的感情。回想起来特别感人,那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坐在那儿,哭得都哭不出来了,哭得真难受。
冯雪峰的习惯是后半夜睡觉,前半夜工作,大概到二三点才睡觉。集中起来关了牛棚以后,他就不习惯了,十点以后灯就关了,连电闸也拉了。他睡不着。我是一躺下就呼呼大睡了,他就推我:“醒一醒,醒一醒,我睡不着,真想读本书。”有时也像开玩笑地说:“我真想喝咖啡。”他喝咖啡不加糖,越苦越好。我说:“我到哪儿给你找去呢?”他苦,睡不着觉就那么干瞪着眼,后来就在晚上和我谈好多他的历史上的事情,好多事吧。
(摘自《口述历史》,王逡义、丁东主编,2003年9月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上一页] [1] [2]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