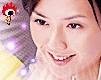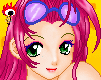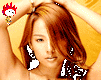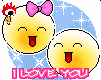张绪山
“学术腐败”在目下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花样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正如同孙悟空七十二变,那根尾巴无法隐去一样,“学术腐败”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特征就是“私”字当头,无视学术道德。形式之一,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不择手段地将他人成果攘为己物。
人们谈及时下的“学术腐败”,
每每摇头唏嘘,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学术腐败行为如果不是“古已有之”,至少也是“源远流长”。且举半个世纪以前的几个小事例为证。
十数年前,我读到一位吴祥麟先生发表在《中央亚细亚》1943年第2期第1号上的一篇论文,题作《古代希腊人关于中亚和中国的知识》,印象十分深刻,对作者的西学修养和文章的逻辑力量由衷敬佩。据文章末尾的介绍,这位吴先生是当时北京一所著名学府的教授。我当时的心情真是欣喜和惊讶共生,遗憾和惆怅并存。欣喜和惊讶的是,几十年前就有人做出那样出色的研究成果来,感到前辈学者的学问真是了不起;遗憾和惆怅的是自己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无缘向这位先生求教,这样好的文章大概自己一生都写不出来。可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却完全击碎了我心中的这个印象。我在国外读书时读到英国学者赫德逊1931年出版的《欧洲与中国》(G.f.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 1931)原文时,总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将带在身边的这位吴先生的文章复印件对照来读,发现竟是赫德逊著作第一章的翻译!这位吴先生拿别人的著述翻译出来堂而皇之地充作自己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典型的学术腐败行为。
无独有偶。《季羡林文集》所收季先生1946年写的文章里也为我们保存了类似的例证。据季先生说,当时读到一位姓丁名福保的大学者“著”的一部几十册厚的佛学字典,怀疑不是作者的个人著作,经过对照知道是翻译日本人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词典。但这位丁先生并不承认是翻译他人的作品,因为他自己也加入了一点内容。有意思的是,为了达到让天下人有机会一睹其风采,这位丁先生还在书中插入许多个人不同时期的玉照,可谓为出名挖空心思矣。一位在剑桥大学任教的德国汉学家发现这位丁先生“制造”大作的奥妙后,将结果告诉在德国留学的季先生,使季先生也为这位同胞的行为蒙羞。季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到另一位学者。此人翻译了日本人写的有关鲜卑和匈奴的几篇论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后来被人查出来写信去问,他不得已声明因时间仓促把作者的名字忘记了。其实,翻译别人的作品而忘记写上别人的名字,这其中是怎样一回事,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很类似一个人从商场里“拿”东西被人抓获后声称自己忘记付钱一样滑稽可笑。
我所读到的吴先生“大作”和季先生文章所谈到事情都出现在上个世纪40年代,想必不是个别现象。季先生当年的文章也说,“像这样的有勇气的人,在我们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后的春笋还要多。”可见当时这类行为并不少见。不过,上个世纪40年代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读书人的日子不好过,读书做学问的条件也不好,所以攘袭他人作品除了读书人本身的名利心作祟外,也不能完全排除“为稻粱谋”这个现实因素。
然而,近些年那些虽不是“大富”但已是“小康”有余的读书人,乃至文化圈内的所谓“名人”,有此类行为者也着实不少。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哲学教授涉嫌抄袭他人著作而大出风头,北京一所更著名大学的一位少壮派教授抄袭他人作品,也暴得大名。他们何以置明显的廉耻标准于不顾而甘为鸡鸣狗盗之事呢?以前想来想去,总是不得其解。现下我忽然间似乎有所醒悟:抄袭他人作品不被人捉住,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名,被人捉住打一打笔墨官司更可以出名,而且是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多么好的出名捷径啊!要知道,在一个道德多元化的时期,出名——不管是好名还是坏名——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因而这出名也就是变成了目的,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现在的学术体制对学术腐败是如此的宽容,不仅证明了在这个时代作弊者本身的道德趋向多元化,而且也证明,在当前传统道德制裁体系崩坏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制度上和道德上的制裁体系。既然作弊不受惩罚,如丢饭碗之类的危险,人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