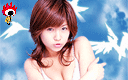淮安“行走学校”:“魔鬼教育”的内情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06日10:31 周末报 | |
|
【周末报报道】侯晨的第一天“我不想留在这里,我要回家。”3月31日,来自河南驻马店13岁的侯晨和妈妈张丽丽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整整一下午。侯晨胖胖的,一双小眯眼看上去十分可爱。得知自己要被留下来,两行眼泪立刻顺着他红扑扑的脸颊流了下来。当着妈妈的面,侯晨把头撞在教室外的水泥柱子上。“你不带我回去,我就撞死在这里。”可张丽丽坚决不答应。儿子已经上小学六年级,注意力不集中、不喜欢读书的问题一直困扰了她好久。在最近的那次期末考试中,侯晨的语文和数学分别考了30分、20分,排名班级最后,这让 行走1000公里 记者在向淮安教育局、物价局、工商局等相关部门采访关于这个工作室的情况时,接受采访的人都称这个工作室为“徐向洋行走学校”。其实,徐向洋工作室并没有专门的文化课补习。用徐向洋的说法,叫“工作室”就是表明和一般学校的不同。其中,意志力训练(长途行走)是他最得意的一招。按照“一千公里定人生,人生必须这一课”的口号,每个学生的行走时间长达几个月,距离都超过1000公里。徐向洋是江苏淮安人,原来是江苏省农垦职大的老师。1996年,徐向洋的儿子徐根上小学六年级,徐根上的是全市最好的学校,而他却是全班最差的学生,数学只考了10分,同学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徐十分”。开家长会回来,徐向洋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清晨,他作了两项决定:辞职创办“择差录取制”学校,徐根停学,在家跟自己读书。徐向洋带着徐根学完了最基本的知识,又学乐器。为训练儿子的注意力,徐向洋每天让徐根拉琴5小时。为了惩罚儿子,徐向洋对儿子动过戒尺、罚过饿、站过桩。没有想到,这种特殊的教育方法竟然使徐根慢慢发生了变化:他的吉他水平已达到了7级,钢琴和长笛也演奏得像模像样,原来不爱学习的毛病也没有了。如今,徐根已经是南京晓庄学院的大学生了。后来又陆续有“问题孩子”送过来,结果每个孩子在他的调教下都变好了。徐向洋就这样慢慢出名了。在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的孩子基本有三类:一类是送来吃苦的,想改掉娇生惯养的坏习惯;一类是迷恋上网,学习成绩太差的;最后一类是喜欢抽烟、喝酒、打群架的。按照办公室主任韩迪民的估计,“第一类占了10%,后两类各占45%”。而行走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意义是独特而深远的,几乎每个孩子都说自己从中受益。来自沈阳的张恒健形象而幽默地描述了行走中的艰辛:“在家苹果一盘都不吃,行军中一个苹果吃得连核也没有,桔子连皮也吃了。馒头冻得硬邦邦,在卡车上敲得当当响,敲碎了狼吞虎咽。”“行走的条件极其艰苦,让学生懂得了珍惜。”管带郭丽评价说,“有孩子边走边哭,说对不起父母,反省以前的过错,表示今后要好好上学。不少孩子之前连棉花长什么样都不知道。通过千里行走,也大长了见识。”根据记者的了解,经历过行走考验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体会:一般三天连续走,第一天没感觉,第二天疼,第三天满脚是泡,疼得没感觉。” 竹戒尺让孩子“心服口服” 除了千里行军外,惩戒教育也是工作室的一大“特色”。惩戒教育,其实就是打。来自南通17岁的周渭清初中毕业后就在父亲的公司工作,但不好好干,一次拿了家里4万元和女朋友在苏州短短几天挥霍一空,竟然还骂父母“一对狗男女”。2004年11月15日,在行军途中队伍走到河南南街村的时候,他逃跑了。结果被抓了回来。徐向洋亲自出马,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扇了很多耳光,打得他嘴角流血。但奇怪的是从此周渭清服了老徐。“徐向洋打人的确有一套,什么时候打、怎样打都掌握得很好,打完后还跟我说话、讲道理,知道我喜欢抽烟,就给了我一包烟抽。”说到徐向洋,周渭清的眼神出人意料地亮了一下。徐向洋自己显然能够掌握“惩戒”的精髓和火候,但是管带就未必有这样的能耐。徐向洋一直认为惩戒教育只可意会不可言表,“如果言传,那管带就可以随便打人了,这是不允许的。”记者观察了五天后发现,尽管徐向洋三令五申,“打”却还是管带的重要招数。集合慢了要挨打、和管带顶嘴要挨打、动作不到位要挨打、吃饭说话要挨打、不写家信要挨打、逃跑被抓回来要挨打、和家长说了不该说的话要挨打……更有一些孩子经历的挨打是莫名其妙的。工作室有专门打人的竹戒尺,孩子们怕被打,四处藏匿戒尺。张龙17岁,来自上海。由于工作早,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成熟。有一次在石家庄练站桩,他的眼睛微微瞟了一下,就招来管带的拳头和耳光。“我没有站稳,脑袋就往墙上撞去,正好撞到一颗螺丝钉,血就顺着右眼眶流下来了。”张龙并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挨打了。刚来的第二天,他就因为没站好,被戒尺打了两下。他想不通,把戒尺按住了。“这时5个管带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我立刻倒在地上,只觉得鞋底疯狂地朝我头上打,后来迷迷糊糊了。30多分钟后,我求了4次饶,他们才停下来,又给了几拳。”那次挨打,张龙左眉处缝了5针。“脸上全是肿的,头也不能动。嘴疼得连粉丝都不能吃,只能喝汤。”对于打人,几乎所有的管带都这样解释:“孩子太难带,有时候必须对他们采取一些强制的手段才行,见效明显。不然无论你怎么说都不行。” 逃跑成了家常便饭 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穿衣、戴帽、洗衣、叠被,饭前一支歌、吃饭不允许说话、有事喊“报告”、唱军歌……整个训练都像部队一样,有着严格的规矩。记者随意走进位于学校三楼西面二中队的寝室。寝室放了14张高低铺,洁白的床单,叠得像豆腐块一样的墨绿色被子整整齐齐,床下放着每人的迷彩包,包上统一贴着标签。打开迷彩包,里面的衣服、生活用品一律竖着排成一列,衣服方方正正非常挺。在最里面的床上,挂满了十多个绿色军用水壶,旁边的架子上,十几条被褥和大衣对折叠起来,有棱有角。整个房间干净整洁,和部队的营房相差无几。但也正是这种严格的管理,让从来没有远离父母的孩子们感觉受不了,尤其是刚来的。而孩子们最直接的反抗,就是逃跑。按照徐向洋的话来说:“到这里的孩子,100%都想家,90%孩子有过逃跑的念头,10%的人曾经有过逃跑经历。”记者了解后发现,其实比例更高。一中队目前20人,7人逃跑过,其中5人被送回来;二中队24人,逃走后被抓回了5个,最多的一个孩子逃跑过7次。张家乐来自河南平顶山。他的逃跑经历在孩子们中间广为流传。张上初一,迷恋上网,而且慢慢地和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搞在一起。1月20日,家长骗他出去旅游,把他从平顶山送到徐州。“一到徐州马上开始行走,第一天就走了50多公里,我受不了,第二天就想逃跑。”但是行走路上,工作室一直派一辆白色面包车跟在队伍末尾,张家乐找不到机会。到了淮安后,开始驻训。1月27日傍晚,趁着大家洗脚时间,张家乐谎称去解手,从二楼爬了下去,一脚踩空。“就这样平着直直地摔下去了,有6米多高,当时下身疼得几乎没有知觉了。”3月31日下午,张家乐盖着绿色军被,躺在床上,小声地向记者描述逃跑经历,“我当时就跟自己说,数5秒绝对可以起来,一定要逃跑!”但“不幸”的是,管带坐的士把他追了回来。这次逃跑使他第五节尾椎“压缩性骨折”。医生在诊断报告上写着:“卧床2月,最好住院治疗。”关于逃跑,《家长须知》中明确说“学生擅自离校所造成的后果与本工作室无关”。家长表示,其实这是不合法的无效条款。但是徐向洋仍执拗地认为,工作室并不是监狱,逃跑完全是学生自己的事情。“逃跑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回家,所以即使跑了,也不会出问题。” “择差教育”引发的种种争议 从工作室成立起,家长和学生对择差教育的种种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孩子在这里几乎与外界隔绝。学校的大门紧闭,旁边一直有人看守;教学楼的铁门,在晚上8点后也被紧锁。学生不能携带任何通讯工具,甚至连钱也必须得存到学校代为管理的账号。刚开始的三个月,家长不能来看孩子,他们和孩子主要联系方式,就是和管带发短信询问情况……作出这些规定,学校的理由都是为了配合训练。记者听一些孩子反映,他们写家信的时候管带都在现场,再交给管带,统一封装。管带对此的解释是“帮助学生把把关,纠正错别字”。可孩子们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这侵犯了我们的隐私。学校还规定不能在信中写想家、让家长来接、被打等负面内容,不然管带会当面把信撕了,让你重写或者干脆不给你寄。”在工作室,11名管带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按照学校“盯、抓、管、查”的带生方法(盯到每个学生、抓住不良言行、管到每件小事、查验训练效果),他们必须24小时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同练,基本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非常辛苦。但孩子们向记者揭发了一大堆管带的共同缺点:随便打人、训练粗暴、经常说脏话……“以前有管带私自截下家长寄来的东西,他们晚上等大家睡觉后喝酒、吃烤鸭。”“打骂是经常的,只要动作稍稍有点不到位,就会遭打。现在我们都害怕。”另一个学生说,“一次被子放反了却没有人承认,管带叫大家列队,然后挨个给耳光,打了5轮。”“管带指使其他孩子把我逼到厕所,然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现在还疼。”……关于管带打人如何恐怖的故事,在采访中听到不止几十次。记者还了解到,师生关系也因打骂变得微妙:不少学生怕被打,在管带面前非常顺从,但从心里不服。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家长抱怨费用太贵,说徐向洋借此发了财。按照入学规定,基本建校费3000元/人,训练费2000元/月(含住宿、伙食),被褥费300元,空调费300元,保险费40元,押金1000元;而且“训练为期一年,半年内非我方原因退出训练者,所交费用(包括押金)概不退还。第一次交费一次性4640元+半年12000元=16640元”。徐向洋对此的解释是:“我们学校是淮安市教育主管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由我独资兴办。我们的学费核定都是经过物价局的,而且收这么多的钱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开销很大,每个孩子都要拉出去训练,还包括吃住等等方面,所以才定了这么一个标准。工作室目前最多只收150个孩子。一次性收半年的钱,就是为了迫使孩子完成必要时间的培训,这样才能起到效果。如果谁中途离开,我宁可把钱捐给希望工程也坚决不退!”记者在淮安市教育局获知,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是在2000年左右以民办培训机构的性质办学的。在采访中,记者看到他的经营、办学许可证高高地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其办公室负责人也一再表明:“如果我们不是合法办学,怎么会有那么多家长把孩子送过来呢?”而淮安市物价局负责民办学校工作的王主任对记者说:“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在两年前就收费标准备过案的,包括:择差教育费、代办费和住宿费,每个季度共计6000元整。”他还表示:“社会力量办学有些收费是比较机动的。” 专家:教育方式要变革 “为什么说来他这里受训的孩子就是差生?称之为‘择差教育’本身就存在对孩子不客观的评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薛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孩子本质上不应该有“优、差”之评价。因为每一个人的优势智力区域和劣势智力区域是不一样的,即发展的性向是有差异的。所谓“差生”,也只是在进行某一方面的评价时,这个孩子相对较弱。薛凯说:“虽然徐向洋也说他眼中无差生,但是他对外宣称他办的是一所‘择差教育’学校,那么这个进校的‘门槛’究竟是什么?人为地给孩子贴上‘差生’的标签,给他们归类分成三六九等,这对他们内心是有伤害的,会让他们得到不良的心理暗示,产生自卑心理而更降低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他还认为,这些来学校的孩子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对家庭和学校给予的教育内容、形式缺乏共鸣,导致教育信息传递无法完成。“其实这种方法是从德育角度尝试的一种教育方式。因为构成品德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种成分中,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品德培养的开端。徐向洋尝试的就是从意志力培养着手,这跟学校搞军训的意义是一样的。”“据了解,‘行走学校’的管理中也存在着学生受体罚的现象,对于这一点徐向洋本人也未否认。这种教育管理即使学生接受家长许可也是不合理的,毕竟孩子不是家庭私有财产,教育管理也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并不是说孩子挨打后“变好”了这种教育方式就值得肯定,“即使动机是好的,方式也必须合理合法。教育是显性、隐性同时发生的过程,在用这种‘暴力方式’教育一个孩子的同时其他孩子都看在眼里,他们会学习到什么呢?为了达到一个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孩子的模仿性很强,以后他们也有可能采用这个经验来处理所遇到的问题。”“‘徐向洋行走学校’给家长和学校提了个醒,教育应该是完整的。”薛凯认为,“行走学校”至少给了家长和学校启示:对于家庭来讲,孩子的今天,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而是不正确家庭教育造成的后果。教育不应当是偏颇的爱和简单的重复要求,“孩子是跟随成人的行为和情绪学习的,学习不是指令,独生子女家庭里要重创规则。而对于学校的启示是,教育的方法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要关注到青少年喜动、喜异的特征;教育的途径要拓宽,经验是可贵的,但要伴随社会的变革而发展;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学习风格,包容他们在适合自己的方法下学习。” 本报特约记者 裴增雨 本报记者 陈璐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教育新闻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