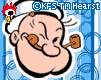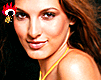| 艾滋病人手术难问题京穗调查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1日02:29 新京报 |
|
在艾滋病人们为一个小手术求医无门的同时,医生们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他们缺乏艾滋病人的手术经验,也缺乏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在传染病医院,荣仔每天吃着昂贵的抗病毒药,期待着血液中的HIV病毒降下来,去另一家曾给他承诺的医院做血管瘤手术,但那家医院的医生已肯定地说,他不可能回来,除非病毒已没有传染性。北京佑安医院成功地为托马斯实施了腰大肌脓肿引流手术,但他的病根没有消除,没有骨科专家愿意为他做骨结核切除手术。王女士在临产手术前验出HIV阳性,她随即受到“特殊”护理,没有人愿意为她的女儿打预防针,因为新生儿HIV检测也呈阳性。 “他们说,如果我的病毒降到没有危险性的程度就可以给我动手术。” 荣仔(化名)的左腹股沟动脉长了一个拳头大的血管瘤,随时可能破裂。在动手术的前两天,他被检测出HIV抗体呈阳性,随后,广东省某医院将他转到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广州市第八医院。 在该医院,荣仔已经住了20多天。每天他都要吃昂贵的抗艾滋病毒的药,以降低血液中的HIV病毒含量。广州市第八医院的条件不足以处理血管瘤,荣仔仍然希望尽快回广东省某医院动手术。 “他的血液里基本已经测不到HIV病毒了”。11月24日,广州市八医院艾滋病科主任医师蔡卫平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病毒,荣身体内96%-97%的病毒已经被杀掉了,“HIV不在血液里,动手术时,医护人员受感染的机会就小得多。” “但是,广东省某医院给不给他动手术,还是个问题。”蔡卫平已经不是第一次遇上类似情况。荣仔的血管瘤 能否考虑出诊呢?该医生坦言:“我自己还没有说服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问题———风险太大了。如果你们实在没办法,而我到时候又说服了自己的话,我可以考虑出诊。” “这个病人是被别的医院骗过来的。”今年11月18日,广东省人大代表到广州市第八医院视察时,一位医生指着荣仔说。 这句话让荣仔一夜失眠,“如果抗完病毒他们还不给我动手术,干吗还要让我花这么多钱来吃这么贵的抗病毒药?这个药一吃就得终生吃下去的。”他现在一个月要吃掉1000多元的抗病毒药。 荣仔11月2日住进广东省某医院。此前,他曾经往左腹股沟的静脉上注射毒品,9月份,发现这个部位长了一个拇指大小的肿块。入院时,他“左下肢肿胀、乏力、无法行走”,检查之后确诊为动脉瘤,被要求立即住院,准备11月7日动手术。3万元的手术费,当时就交了。 11月5日,主刀医生告诉荣仔:经过查验,医院不能确定荣仔是否患有艾滋病,必须转到广州市第八医院检查,“等没有了病毒再帮你动手术。”手术费也退了回来。 荣仔的母亲说,医生当时的态度非常和善,还专门给他们开了一份《住院病案出院记录》,记录了荣仔住院医疗及出院时的状况。 该《记录》上写明:“了解患者病情,查HIV试验呈阳性”;“与医院及家属商量后,转送传染病院进一步治疗,已报告医院,已填传染卡,请示上级医司,予以转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左股动脉动脉瘤”,出院情况为“神清、精神好”。 荣仔的母亲当时曾询问主管医生:“是不是病毒没了该院就可以接受荣仔动手术?”对方的回答是,可以接受,只要广州市第八医院能够开张证明,证明没有病毒。 11月25日,荣仔的主管医师———广东省某医院外科黄医生承认,当时确实对病人家属有过承诺,但前提并非“病毒降低到没有危险性”,而是“没有传染性才能够做”。 事实上,HIV病毒在目前是不可能完全消灭的,传染性也是肯定存在的,因此黄医生说:“荣仔不可能再回到本院动手术。” 蔡卫平曾提议:实在不行的话,市第八医院可以提供手术室,只要医生同意过来出诊就行了。 对此,黄医生则表示:“没有必要,广州有专门的肿瘤医院的医生。” 同一天,记者以艾滋病患者朋友的身份,向广东另一家省级医院肝胆外科的一位医生求询。这位医生说,这只是一个小手术,但由于涉及到艾滋病问题比较复杂,必须各个部门都问一下。 半个小时后,这位医生回复:一方面是医院本身科室的消毒室不行,一方面护士长和领导都认为这个手术牵涉到太多问题,不能接受,“手术肯定要见血,普通医院都害怕。” 能否考虑出诊呢?该医生坦言:“我自己还没有说服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问题———风险太大了。如果你们实在没办法,而我到时候又说服了自己的话,我可以考虑出诊。” 说起儿子,荣仔的母亲声泪俱下:“血管瘤随时会爆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等死啊。钱不是问题,我们只想求医……为什么不能给我儿子一条生路?” “我确实见过更悲惨的案例。”蔡卫平回忆,两年前,广州市第八医院收治了一名30多岁的艾滋病男患者,“与荣仔一样,也是腹股沟血管瘤。” 蔡卫平介绍,住院之前病人已求诊了几家医院,住院的几个星期里,他也帮着四处联系医院,但没有一家愿意接受。“直到有一天,病人血管瘤破裂,血喷涌而出。由于破裂范围比较大,怎么也压不住,半个小时后,血喷完了,病人就死了。” “本来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动手术的。”蔡卫平说,艾滋病科只能处理内科问题,广州市第八医院的外科医生也只是普通的外科医生,动脉瘤破裂出血等外科情况超出了他们的处理能力。佑安医院的四例手术 “由于免疫系统的问题,艾滋病患者感染合并症的几率比正常人高得多,其后果往往是致命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手术在一些非常有名的大医院之间踢来踢去。” 今年9月11日下午,北京佑安医院,来自广州的艾滋病患者托马斯(化名)完成了他的腰大肌脓肿引流手术。 “手术很成功。”主刀医生林栋栋说,“但托马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出现脓肿是由于一个骨结核病灶在托马斯的腰椎里不断扩大。今年3月开始,他的腰部每天剧痛3个小时,下午到晚上定时发烧六七个小时,体重骤减10公斤。在广州市第八医院,托马斯打了两星期的抗生素,烧退了,身体也基本稳定下来,但在背部肿起了一个拳头大小的脓肿,CT检查结果是骨结核。 当时,专家小组的意见是应该及时进行手术治疗,但和荣仔的情况类似,广州八院无法施行骨科手术,除此之外,托马斯找不到愿意为他开刀的医生和医院。一位网友曾为他找过一个骨科医生,得知真情后,这名医生跳起来说:“你想害死我!”今年6月,黑龙江一位医生曾表示愿意为托马斯动手术,但医生所属的医院则坚决拒绝。 “医院对艾滋病人的拒绝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艺术。”托马斯说,北京某大医院给他的答复是:“我们除了结核病,什么都收。”而另一位医生则建议,他根本没必要做这个手术。 事实上,在佑安医院为托马斯完成脓肿引流手术之后,他还需要进行第二步手术———骨结核病灶切除,但佑安医院没有骨科。 “跟很多专家都谈过了,一听说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死活不愿意来。”11月25日,佑安医院外科主任徐光勋说,两个多月了,尽管他们已努力多次,愿意做这个手术的外科医生依然没有找到。 从2001年到今年9月,佑安医院外科共收治了4位艾滋病患者,其中3例都是徐光勋亲自主刀。 “由于免疫系统的问题,艾滋病患者感染合并症的几率比正常人高得多,其后果往往是致命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手术在一些非常有名的大医院之间踢来踢去。” 徐光勋举例说,佑安医院收治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郑某来自马来西亚。“就是脸上一个小粉瘤,一个赤脚医生都能解决的手术,跑遍了马来西亚、泰国各大医院,没有一个医师敢治。”来佑安医院之前,郑某曾向北京一家赫赫有名的综合性医院求治,但很快被赶了出来。艾滋病产妇问题 目前预防母婴传播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在产妇分娩之前以及婴儿出生后及时服用AZT或者奈韦拉平,这可以大大降低婴儿感染率。没有吃这两种药的话,母婴感染的几率是30%左右,而通过吃药加上剖腹产以及不用母乳喂养,一般可以降低到10%以下。 2002年11月,30多岁的大龄产妇王女士到华东某大城市一家大医院剖腹产。王女士说,从进入产房到女儿出生,整个过程都很顺利,医生护士都很客气。 然而,第二天开始,王女士就觉得一切都变得异常起来。当天早上,一位医院护工穿着消毒衣带着手套进病房给她的婴儿喂奶。过了一会儿,同房的病人神色怪异地搬走了。每天例行的测体温医院单独给王女士发了一个温度计;王的衣服全部被消毒过…… 经过一番追问,医生告诉王的姐姐,医院在进行剖腹产前对王进行了血液检测,第二天出来的结果显示:王是HIV病毒携带者,而且已经过防疫站确诊了。 “当时整个医院妇产科连清洁工都知道了,就我自己不知道。医院太不尊重病人了,这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王女士说,她此前并不知道自己携带HIV,“我又没有输血,又不吸毒,怎么可能?”接下来的一切让王女士无法再平静:医生和她接触戴着手套,医院本来每天都要抱婴儿去洗澡的,她的女儿却被“遗忘”了。连正常新生婴儿都要打的预防针,医院都不愿意打,“说是我们小孩不适合打。”孩子后来是在其他医院打的针。第三天,王女士出院了,而一般产妇剖腹产后至少要住院一周。 王的女儿HIV检测也呈阳性。“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要等小孩18个月后长出她自身的抗体才能够确认是否受了感染。”王女士说“要是女儿以后查出来是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 在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中,母婴传播占有一定的比例。而通过一定的产前产后干预,可以大大降低婴儿传染的几率。然而由于普遍存在的歧视,女艾滋病患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咨询和指导。蔡卫平认为这是一个急需引起社会关注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位女患者在广州市第八医院艾滋病科进行分娩,每次都是到临产的时候由该院联系广州市妇婴医院派医生过来。 “这对产妇很不公平,她们没法享受到正常人都有的产后护理服务。”蔡卫平说,还有一些孕妇患者,最后只能偷偷跑到乡下去分娩,而那里的医务人员几乎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生,“这样其实无论对医务人员的保护还是对产妇婴儿都不利。” 蔡卫平介绍,目前预防母婴传播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在产妇分娩之前以及婴儿出生后及时服用AZT或者奈韦拉平,可以大大降低婴儿感染率。没有吃这两种药的话,母婴感染的几率是30%左右,而通过吃药加上剖腹产以及不用母乳喂养,一般可以降低到10%以下,发达国家这个几率甚至可以降低到3%以下。艾滋病人的孤岛 “一般因为性传播途径和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患者比较正常,也积极配合治疗,希望早日康复。而很多吸毒的艾滋病患者,‘自己都放弃了自己’,比较难管理。” 在艾滋病科当了10多年的医生,蔡卫平对许多艾滋病人受到的医疗歧视深表无奈。“很多病其实是小手术,但人家就是不愿意给他们做,主要是心理压力。” 蔡卫平说,他所在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对于许多艾滋病人来说,已经成了他们在海洋中的孤岛。” 一旦发现艾滋病患者有什么小毛病,无论是外科或内科都送到该院艾滋病科。交叉学科处理的情况经常发生,比如病人生小孩、新生儿的观察护理、合并肿瘤病人的处理等等,而车祸、外伤、动脉瘤破裂出血等也往这里送。 目前,广州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对病人实行的比较宽松的管理方式,“像普通病人一样,”病人出入自由,对病人的探访也是自由的,除了极个别病人患有开放性结核病的,医生会提醒家属或者探病者,而一般医务人员查房等都没有戴口罩或者手套。 与其他科不同的是,感染一科(也即艾滋病科)对病人的分泌物、用过的注射器、标本等的处理要严格得多。注射器每次用完之后都要先用消毒剂浸泡之后再做处理,粪便、血液等标本的处理更谨慎,病人所有的污物都要经过消毒剂浸泡并且分开放。为减少院内的感染,病房每天都要进行一次消毒。感染一科的床单、病服基本上都是专用的,每次都是用消毒剂浸泡过之后单独洗涤,以避免与其他科的病房混淆。“这些东西经过浸泡之后就不会有任何传染性了。” 艾滋病科的病房由一条通道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左边病房的病人经常互相串门,聚在一起抽烟聊天;右边的病房静悄悄,病人们大都不愿意面对镜头。左边的是吸毒感染的,右边的则是因为性传播途径和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患者。11月24日,市八院艾滋病科住院16名艾滋病人中,有2/3是吸毒感染的。 蔡卫平介绍,在去年年中以前,艾滋病科并没有这样的“泾渭分明”,不同渠道感染的病人都是混住的。但是,由于吸毒感染者即使住院以后还经常在卫生间吸毒,或者聚在一起吵闹,毒瘾一发作起来性格都会扭曲,没有吸毒的感染者受到的威胁很大。因此,在感染一科(艾滋病科)成立半年之后,医院对病人实行了分开管理。 “一般因为性传播途径和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患者比较正常,也积极配合治疗,希望早日康复。而很多吸毒的艾滋病患者,‘自己都放弃了自己’,比较难管理。”艾滋病科的一位护士说。医护人员的恐惧和防护 “一旦出现意外暴露,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要第一时间去验血。其实,有没有被感染,要几个月后才能检验出来,但是,这管血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以后证明你‘清白’的铁证。” 在蔡卫平看来,为艾滋病患者做手术有一定风险,但只要做好防护自己小心就不会被感染,而且艾滋病毒很脆弱,一般的消毒剂就可以将之杀灭。 佑安医院感染科医师张彤也有类似看法,“医护人员之所以对艾滋病患者敬而远之,缘于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认知不足。” 但另一个事实是,托马斯的主刀医生林栋栋做完手术后,心里并不踏实。他说,自己一直瞒着同在佑安医院做护士的妻子,直到好久没什么事了才轻描淡写地说出来。 林栋栋今年32岁,医学博士,他坦言:“那天正好徐光勋主任有会,就让我主刀。这是我第一次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心里直犯嘀咕:万一感染了怎么办?考虑到是科里安排的任务,也只能干。” 护士江永丽在佑安医院外科手术室做了14年的护士,参与了医院所有4例艾滋病患者手术的护理。她回忆自己第一次参与艾滋病人手术时的心情说,“当时心里直嘀咕:真倒霉,孩子这么小就碰到这事!”“回去跟家里一说,爱人从此就不让再干一点家务活:怕我碰破了留下创面。” 外科病房年轻护士刘婕也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护理刚做完手术的艾滋病患者的情形:“引流管里体液好多,我脑子里只想着:千万别碰上体液。” 徐光勋说,从2001年开始给艾滋病做手术至今,他一直瞒着家人:“不能告诉他们,会担心死的。”2002年,徐光勋在给一位艾滋病患者做阑尾周围脓肿切开引流手术时,手指被手术刀划破,心里一直非常恐惧:万一感染了怎么办?人家会不会往歪处想?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事了心里才踏实。 在佑安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新秋的工作手册上,详细地记载着工作人员手术误伤的情况,外科主任徐光勋受伤最多,被扎伤、割伤达4次。“平时好多次他们都不说,也没记。” “正是因为对艾滋病认知不足,医护人员缺乏相应的防护知识。”徐光勋说出了问题的另一面,目前国内尚缺乏一套艾滋病手术的防护规范,“我们是按照病毒的防护知识准备的。” 江永丽介绍说,目前他们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时的防护用品已实现了全部一次性,医护人员一律戴两副一次性橡胶手套,平时只有一副;身穿的防护服为一次性防水无菌手术衣,平时为消毒后反复使用的棉布防护服;要戴上一次性防护眼镜,平时一般不戴。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作用,就像SARS肆虐期间,有的医护人员穿6层防护服还是提心吊胆一样。两副手套也一样可以被割破。”徐光勋说,“目前没有更具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广州第八人民医院,蔡卫平介绍,感染一科医务人员流动性相当大,全科22人,除了4名主要医生固定外,其他的医务人员都是轮换的。至今,今医院已经有15名医护人员(2名医生13名护士)在操作过程中,发生被艾滋病人血液污染的针头误伤。 13名护士都已经离开了感染科,感染科的护士长说,“虽然发生误伤后,我们会做一年的跟踪,目前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没有被感染的现象,但毕竟心理上有阴影。” “宁肯感染SARS,也不愿意感染AIDS。”这是SARS之后感染一科曾经流行的一句话。“在这里工作,最大还是可能会受感染的压力,”一名护士说,“一旦感染了AIDS,人们往往把你和不良行为挂钩,才不管你是因为职业原因以外感染的呢。” 蔡卫平说:“我们院长经常告诫我们,一旦出现意外暴露,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要第一时间去验血。其实,有没有被感染,要几个月后才能检验出来,但是,这管血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以后证明你‘清白’的铁证。”两种恶性循环 “国内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医护人员越是怕做艾滋病手术,就越是无法认知艾滋病,越是不了解艾滋病,就越是怕做艾滋病手术。” “正是通过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医护人员才最后认识到其实艾滋病远没有想像得那么可怕。”11月25日,徐光勋说。 徐介绍,当初在给托马斯做腰大肌脓肿引流手术时,曾试着查找一些参照资料,结果发现国内没有任何相关资料论题,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网站上却发现有3000多篇与手术有关的学术文章,其中关于艾滋病合并结核的文章就有100多篇,艾滋病患者做心脏搭桥、肝移植手术的都不少。 “国内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医护人员越是怕做艾滋病手术,就越是无法认知艾滋病,越是不了解艾滋病,就越是怕做艾滋病手术。”徐光勋说。 另一种恶性循环是关于歧视。蔡卫平说:“医务人员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实际上是最需要纠正过来的,因为他们的态度反过来会影响到其他市民。与此同时,社会人群对艾滋病的认识不足,也反过来令医院害怕影响到其他病源。” 要改变这种状况,蔡卫平提出,首先要让普通市民知道这种病的传播途径,说明艾滋病不会通过空气传播,从而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制度,比如对拒绝艾滋病人的医院或者医生进行惩罚,导致艾滋病人因延误治疗而致残或死亡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等等,甚至可以参考目前普遍实施的“受诊医生负责制”,第一个接触病人的医生要负责到底,而不是一推了事。 同时,蔡卫平认为,还应该加强医务人员保障机制。他建议由政府拨专款对从事艾滋病工作的医护人员给予补贴及购买专门的保险,一旦因工作意外感染HIV,要为他们日后的生活提供足够的保障,免除这些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稳定防治艾滋病的治疗队伍。同时在经济分配上,向从事艾滋病的医护人员倾斜,使他们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来源:新京报) 相关专题:新京报-核心报道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京报-核心报道专题 > 正文 |
|
| |||||||||||||||||||||||||||||
|